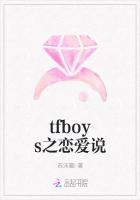一九八三年的六月八日,东浦镇车水马龙之下,是一片欢声笑语的惊天呼声。此时许多的年轻人正在热烈组织庆祝我国加入了南极条约,是继一九七九年的又一件举国同庆的大事,为了国家地位的不断上升,为了百姓的骄傲,镇里彻夜通明。
而在一个长街尾对面不起眼的破旧不堪的裁缝铺里,一位白头老人正带着眼镜,似乎在四处寻找什么。她苍老的手已不再如年轻时那么灵活,但没有人比得了她做的衣服。
不过在以前确实有很多人关顾她的旗袍,但如今的大势是追赶时尚,老百姓倒是忘了还有这样的一位好手。
今日我作为《民众日报》的记者受命而来采访的便是这位老人,她名叫余阿九,是一位世纪老人,一生勤勤恳恳,很受当地人的尊敬。
不过她自己不以为意,笑说就因为年岁大罢了,谁的一生不是这么过来的。
当再次打开那些散落在历史尘埃里的陈旧书箱时,她告诉我,自己从没想过已经是一百零一岁的高龄。满头白发的她却仍旧坚毅如初,时光荏苒后,苍老的痕迹依旧是当初的无奈时代。
里头保存起来的全部东西都是她舍不得扔掉的往事,那些隐藏在时空深处的故事,又将何处去寻?她淡然地抽出那张报纸,我仔细阅览,上面的时间清楚地写着一九二一年五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是鲁迅先生发表的的故乡一文。
长达六十年了,这份报纸终于重见天日,可她却忍不住悲哀起来,我怎么劝也劝不住,只得认真地听她讲起当初的故事,这也就是我采访她的原因。
了解时代的苦难,让被遮盖的历史重见天日。
但是时间把她抛弃了很远,她再也走不回当初的路,找不到当初的人。在无尽的回想中,她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个老朋友,因为她的过去,也与他密不可分。
她的那个朋友是一个真正拥有民族魂的人,可惜天妒英才,在民国二十六年就已去世。余阿九也去瞻仰了他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
不过她不敌那些热血的学生,一个一个自动组合成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
她只是默默地点上香烛,娓娓道来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友人,其中在提到阿水一人时她怔了良久。阿水此人不但是他们共同的朋友,还是她一生都未曾忘记的朱砂痣。
那次丧礼的场面很宏大,是上海滩从未有过,全中国都从未有过了的。她的这个朋友确实乃世间罕有的文学之才,但余阿九的心里只有从前的回忆与悲戚。
想到这些深埋心底的往昔,她苍老的手逐渐落地,眼睛竟已缓缓合上。
她在踟躇,长达一世纪,他还能认出自己吗?身边的哀恸声长啸,可是她却飘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记忆里想要与一个少年永远生活的海边,或许她终于可以了却了那个梦。
一旁悼念的我并没有哭,因为我知道,她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了,而她的故事我更要一字不落地告诉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