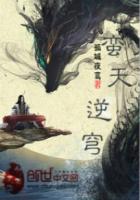拂云叟道:“岁寒虚度有千秋,老景潇然清更幽。不杂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自风流。七贤作侣同谈道,六逸为朋共唱酬。戛玉敲金非琐琐,天然情性与仙游。”
只是,从前与我相伴的人到哪里去了?而今只剩下鸟,剩下风月。
月光下竹影来回,轻轻擦拭着竹子下一方石刻的棋盘。
女子问:“你一路走来,何止行了千里万里,偏这点路就腿软?”
三藏说:“不敢欺心,贫僧这一路都是骑马。”
“那就说说你的马罢。”
“那才是‘真的畜生’。”三藏没好气地说。
“什么叫做‘真的畜生’?”女子继续走路。
三藏没奈何,只得跟上道:“这畜生本是海里的神龙,却畏死贪生,偏化作了白马,屁颠屁颠地跑来做老和尚的脚力。他还偏有几分做脚力的天分,一路上但食草饮水,不仅绝少与我降妖除魔,遇见了妖魔,反而比老和尚还逃得快呢。难道不是‘真的畜生’?”
“他就无甚好处?”
“骑着还算舒服。”
女子‘咯咯’地笑了一声。“怎么,你总是这般健谈?”
三藏愣一下,遂也跟着笑了。“不消说,常时总是跟畜生说话,哪有跟女菩萨说话快活?”
“然而,”女子说,“若是有人陪伴,便是畜生也是好的,不是么?”
三藏自然说是。又道:“其实也是个爱好。从前在金山寺里无聊,不是与人吵架,就是聊天。”
女子惊奇:“你还会吵架?”
“哪有什么会不会的?”三藏也不遮掩,“无非是吵他娘罢了。怎么,女菩萨也要听吗?”
“你说就是。”
“那就坐下来罢。”三藏其实有些疲惫,毕竟在小白的悲伤趴了一天一夜呢。“你看这株翠柏,非有两个人合抱不可,咱们若拉起手来,便能测出他的腰围,若在树干上凿个树洞,还能对他说些知心话儿。”
女子问:“怎么,你也要跟他聊天么?”
“不可以吗?”三藏说。
孤直公道:“我岁今经千岁古,撑天叶茂四时春。香枝郁郁龙蛇状,碎影重重霜雪身。自幼坚刚能耐老,从今正直喜修真。乌栖凤宿非凡辈,落落森森远俗尘。”
只是,从前与我相伴的凤凰到哪里去了?而今只剩下鸟,剩下风月。
三藏说:“我听说柏树质坚,咱们与他说些悄悄话儿,或可忏悔今生的罪孽,或可吐露心底的秘密,他必不与外人说去。”
女子笑笑,举步便走。又问:“你却有什么罪孽不能与外人讲呢?”
三藏追逐她的影子,问道:“谁又没有罪孽呢?”
“又是什么罪孽?”
三藏道:“不可说,不可说。”
“可你心有滞碍哪能修行?”
三藏反问:“若心无滞碍,又何必修行呢?”
“你修的什么?”
“自然是解脱。”
“解脱个什么?”
“自然是滞碍。”
女子道:“如此,才是滞碍。”
三藏说:“如此,才是修行。”
“如此,便快些跟上来罢。”
“奈何我这老寒腿呢?女菩萨,且怜惜则个,须知老和尚年迈体衰呀。”此时,三藏的说话几乎是一种呻吟。“或者,要是骑着马来就好了。”
女子问:“你又老了?那也不急在这一时。”
三藏颓然道:“怕只怕‘量变引起质变’,哪天走不动了,才悔之晚了。”一时又欢喜起来,笑道:“话说女菩萨,你看这株苍松枝叶何其茂盛,咱们爬到树上去听听松涛,便如泛舟大海。人也道‘松者,寿也’,也不知它经历了多少岁月,咱们何妨去侧耳倾听,听他讲讲那过去的故事?”
女子却问道:“何谓‘量变引起质变’呢?”
劲节公道:“我亦千年约有余,苍然贞秀自如如。堪怜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机。万壑风烟惟我盛,四时洒落让吾疏。盖张翠影留仙客,博弈调琴讲道书。”
只是,从前与我相伴的仙人到哪里去了?而今只剩下鸟,剩下风月。
三藏道:“也是那猴子说的。”
“猴子怎么说的?”
“猴子说,也许他今天不知道怎么让天与地相见,但是时时想着,常常念着,总有一天会想明白。”
“他倒耐心。”
“其实有个说法呢。”
“什么说法?”
“不怕贼偷,就怕贼想念。”
女子恍然道:“这猴子原是个偷东西的惯犯。”
“他是有些心得。”三藏说。
“也是你教的好徒弟。”
“天地良心,老和尚哪敢教他?”三藏却有了新的发现,又兴冲冲地说道:“话说女菩萨,你看那里有棵枫树,此时虽然不是秋天,但是红叶嫣然,咱们快去摘些叶子,便如摘下星星一般。”
女子问:“却不腿软了?”
三藏傲然道:“硬得很,硬得很。”
二人走到近前,只见那一树叶子在月下风中舞动,恰如一树的火焰在欢呼,在雀跃。三藏轻轻地摘下一片。
“得罪,得罪。”三藏合掌说。
独角便笑笑。
女子问:“得罪怎地?”
“他好生长着,却不想被我摘了。”
“风也吹落些。”
“和尚却不是风。”
“雨也打落些。”
“和尚也不是雨。”
“那和尚是什么?”
“还是什么?不过是罪孽。”
那女子便痴痴地看着他,问:“到底有什么罪孽?”
三藏一笑:“这便是了。”
三藏把那枚叶子轻轻地簪在她的发间。
“如此便不像了。”三藏说。
“不像什么?”女子已然羞红了脸。
“鬼。”
“什么鬼!”
三藏连忙致歉道:“我初时见你面色苍白,发丝且在风里凌乱,还以为是‘传奇’里的鬼魂呢。”
女子才不恼了,问:“什么‘传奇’?”
“乃是我天朝的文化瑰宝。”说起传奇,三藏总是兴致勃勃,喜道:“怎么,女菩萨也要听吗?若是咱们坐下来,我能给你讲上一千零一夜。”
“你说真的?”
“怎么不真?”三藏自信满满的样子。“出家人不打诳语。”
莫说一千零一夜,便是一千零二夜,那些故事也讲不完呢。
女子便盯着三藏的眼睛说:“那你可记住了。”
“放心,”三藏又信誓旦旦地说。“老和尚一辈子念经,腰也不好,腿也不好,唯有记性好得很呢。”
何况有些故事还是亲身经历,又哪里需要去记忆呢?
女子转身又走,同时有些挑衅似地问道:“你就不怕我真的是个鬼么?”
三藏赶上几步,却道:“便是鬼也是好的。”
“怎么好?”
“你不嫌我粗鄙,愿意陪我。”
“那也不算什么。”
“也不嫌我絮叨,愿意听我。”
“也是无可奈何。”
“明知我是唐僧,也不吃我。”
那女子便停下了脚步。
“可见你必不是鬼。”三藏翻翻眼皮,想了想又说。
“莫非只有吃你的才是鬼么?”
“况且,即便你真的是鬼,也是个女鬼。”
“女鬼便怎地?”女子正色道:“怎么,你敢轻视我么?”
三藏摇摇头说:“但只亲切些,女鬼总是好的。”
“怎么‘亲切’呢?”
“看脸。”
女子又笑出声来。
“怎么,你是在奉承我吗?”女子问。
“出家人不打诳语,正是。”
“你却不知道‘红粉骷髅’么?”
“自然是知道的,不过贫僧也知道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贫僧也是个骷髅。”
女子一怔。
三藏却笑道:“话说女菩萨,你不会真的是鬼吧?”
“你看呢?”女子再次拂去额前的乱发。
三藏翻翻眼皮,又想了想,才道:“还是别说这件事了。话说女菩萨,你看这里有一株丹桂,一株腊梅,梅枝上还零星挂着几瓣花呢。咱们不妨去问问她们:春天已经到来,冬天还会远吗?或者也摘下一瓣来,我与你簪在耳边,也与那片枫叶相映成趣也。”
“怎么‘相映成趣’呢?”
那一男一女两个小童相视一笑。
三藏道:“便是‘星星相映’。”
女子又红了脸颊。只是在三藏看来,为何她的眼睛里像是有些悲伤?而在女子的心里,在三藏看不见的地方,怎么又会有些失落呢?
“可是长老呀,还是别说梅花了,”像是不经意地,女子的手在眼前划了一下,才问道,“你看那棵又是什么树呢?”
三藏说:“呀,此刻就在眼前,我还以为是一座山呢。”
“是树。也不知他经历了多少岁月,又经历过多少风雨,才至于今日这般盛大,一树便是一世界也。”
三藏合掌道:“善哉,善哉。”
女子说:“那里还有一个树洞,洞口则尤其宽大,咱们何妨钻进去瞧瞧,也好看看那树中的世界呢?”
“宽大是宽大,却只怕进去容易出来难。”对此,三藏却是实难从命的。
“却有何难呢?”
“你不知道,”三藏忧虑道,“其实贫僧这一路行来,最怕的就是洞了。想那洞中不知深浅,也不知有没有什么妖怪。”
“能有什么妖怪?”
“自然,但只要吃我的就是妖怪了。”
女子莞尔:“你还真是明白。”
三藏倒也谦虚:“无他,唯手熟尔。”
“何谓‘手熟’呢?”
“手被抓得多了,也就熟了。”
女子已然抓紧了三藏的手。
“可是长老,你看那边洞里似乎亮着灯火,莫非其间别有洞天?”
“还是个会点灯的妖怪?”
“人家还未吃你呢。”
“这倒是。”
“可是长老,你看那灯火越来越亮,分明是越来越近啦。”
“不仅如此,随之还走出几个人来,那为首的一个可不就提着灯吗?”
女子道:“不消说,必是来接长老的。”
“你怎知道?”
“因为小女子跟他们是一伙儿的。”
“这便是你说的地方?”
“可不就是?”
“贫僧其实怕生,不如回去罢。”三藏转身便走。
女子却哪肯放他,笑问道:“圣僧岂不知‘既来之,则安之’吗?”
“我看那几人形容古怪,远不如女菩萨来得亲切。”三藏说。
“圣僧又不闻‘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吗?”
“甚么‘子羽’,不要也罢。”
二人拉拉扯扯,不觉双方已到眼前,三藏勉强看去,却是四位长者。
那四老者更是将三藏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那眼光三藏分明是熟悉的,也就免不了毛骨悚然。
这情景,三藏心下暗叹,果然还是要吃我呀。
别吃我,别吃我。
却听那执灯的一人当先揖道:“这便是唐朝来的圣僧吗?我等久候多时矣,真是幸甚一遇!”
女子说:“长老,这位便是劲节公了。”
三藏道:“惭愧,惭愧。‘僧’是真的,‘圣’却是假的。”
三藏偷眼去看,这劲节公人如其名,果然一脸坚毅的颜色。
一人道:“老朽号曰‘孤直’,却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女子说:“这位便是孤直公了。”
三藏道:“‘老’必是真的,‘朽’却是假的。”
三藏小心打量,孤直公同样人如其名,形容方正。
几人大笑。一人道:“向闻唐僧之名,今日一见,果然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更胜闻名。果然是个得道的高僧。”
女子说:“这位便是凌空子了。”
三藏说:“若真得道,便‘凌空’去也,又何必还要留在这里受苦?”
凌空子似乎多一些冷峻,使人不得轻易亲近。
一人道:“便凌空又能如何,还真能飞上天去?那时候进退不得,也只得‘拂云’罢了。”
女子说:“这位便是拂云叟了。”
三藏问:“怎么头发是绿色的?”
拂云叟道:“天生的。”
三藏说:“我还以为是顶帽子。”
拂云叟却多一些不羁,有些浪子的神气。
这四个都是衰老的形容,眉宇之间却有无限森然的气象。
女子说:“长老却不问奴家的姓名么?”
三藏忙道:“但只亲切些,总是好的——”
那女子噗嗤一笑。遂又掩了口,欠身说道:“小女子小字‘故人兮’,人前叫做‘杏仙’的便是了。”
三藏赞叹:“真是个亲切的仙子。”
杏仙道:“贫嘴!”
孤直公道:“‘杏’是真的,‘仙’却是假的。”
劲节公道:“孤直慎言。”又说:“至于你身后的那个,小字‘赤枫鬼’的,大号乃是‘独角’。”
三藏一回头,只见得身后立着一个青面獠牙的人形怪物,长头发殷红如火,名副其实,额头上果然长着一根油亮如漆的独角。
遂躲在杏仙的背后,三藏尖叫一声:“仙子救我。”
杏仙笑:“救你怎地?”
劲节公说:“圣僧莫怕,这怪物丑是丑些,其实心地良善,也是我辈中人。”
独角便笑笑。
三藏问:“何以见得?”
杏仙道:“人摘了他的叶子,他也不恼。”
独角便笑笑。
劲节公道:“这独角心拙,尚且算个蒙童。”
三藏问:“却有多大年岁?”
劲节公道:“若是比之于人,不过是七八岁吧。”
“七八岁便长这般大了?果然是个怪物。”
独角便笑笑。
三藏这才走出了杏仙的影子,又问:“不知杏仙又芳龄几何呢?”
杏仙说:“独角若是七八岁,故人兮便是二八年华。”
三藏说:“真好年华也。”
杏仙道:“又贫嘴!”
三藏又问:“也不知四翁寿数几何?”
劲节公说:“有诗为证。”
三藏问:“劲节公也作诗吗?”
杏仙回答:“又何止劲节公呢?长老不知,四老其实皆长此道,便是故人兮也略作得。”
劲节公说:“敢启圣僧,我等原非歹人,今日特请你来,正为论道会诗也。且入陋舍一叙,我等也好供奉些斋素。”
三藏轻叹道:“却是可惜,可惜。”
杏仙问:“长老何言可惜?”
三藏说:“可惜没带那呆子来,料来他必饿得紧了。”
凌空子问:“圣僧说的可是天蓬元帅?”
三藏说:“那呆子神通广大,尤其能吃。”
拂云叟道:“他若来了,我等便没得吃了。”
三藏道:“便让他来?”
众人大笑,不允。三藏又叹道:“可惜,可惜。”
杏仙嗔道:“你又可惜个什么?”
“可惜没带那猴子来。”
凌空子问:“圣僧说的可是齐天大圣?”
拂云叟说:“他若来了,我等也不成事了。”
三藏笑问:“什么事呢?”
拂云叟道:“自然是作诗。”
三藏又叹道:“果然可惜。却不知诸位可曾到过长安么?”
孤直公道:“听便听过,却从未去过。说来惭愧,我等困此久矣,却苦不得脱也。”
劲节公道:“正是。”
三藏说:“若未去过长安,便不知那些月下的诗会,只有长安最美。猴子也曾去过一次,便是会诗去了。”
孤直公问:“圣僧说的也是齐天大圣?”
三藏道:“那猴子尤其神通广大,有一样本事唤做‘筋斗云’的,一去十万八千里,长安虽远,与他却近。”
“他却悠闲。”拂云叟说。
三藏道:“也不尽然。那猴子其实是个天生的劳碌命,却少有些空闲。”
劲节公道:“修道原本艰难。”
三藏道:“命运原来乖张,想得的得不到,得到的又变了样。那猴子是个天生的诗人,奈何宿业太重,一辈子放不下刀枪。这一路上为保贫僧取经,也不知又犯下了多少杀孽。”
拂云叟说:“果然可惜。”
劲节公问:“却不知大圣何在呢?”
三藏大喜:“想来不远。”
杏仙道:“不曾见过。”
劲节公道:“如此,便随缘罢了。”
凌空子道:“那便人庐舍一叙,如何?”
劲节公当先便行,请三藏在后,三老随之跟上。三藏无可奈何,也只得踉踉跄、战兢兢,携着杏仙的小手走进那树洞之中。
好软。
凌空子道:“吾年千载傲风霜,高干灵枝力自刚。夜静有声如雨滴,秋晴荫影似云张。盘根已得长生诀,受命尤宜不老方,留鹤化龙非俗辈,苍苍爽爽近仙乡。”
凌空子抬起头来,看一眼自己硕大无朋的本来面目,眼睛里闪烁的却是刻骨的绝望与悲凉。
在那洞中左转右转,直把三藏转得惊心动魄,眼中才出现了那树中的世界。
终于走出了树洞。
三藏见得前方似有一面石壁,壁下有一草亭,亭子边上有一棵杏树。那杏树兀自在月下招摇,树叶子晶莹剔透,似乎每一片都透过月光。
树下还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童,见得众人到了,乃相视一笑。
只是呀,从前与我相伴的神龙到哪里去了?而今只剩下鸟,剩下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