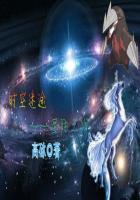两天以来,岳尊一直在竭尽全力的施展《火云腾》术法。灵力耗尽了再充满,充满了又耗尽。在这种灵力潮汐的激荡下,他的经脉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变得通畅而坚韧。同样的,他的气海也在灵力潮汐的一呼一吸之间变得比以前更加充盈起来。
带着笨重的龙默琴,岳尊腾云驾雾时的灵力消耗异常快速,几乎是每隔半个时辰,他就要找个地方降下云头休息,通过盘膝打坐恢复气海中几近枯竭的火灵力,这大大降低了岳尊的前进速度。
浔陶古镇外的官道上,这边担柴的樵夫腰间别着斧头,那边种菜的农夫颤起挑子来赶路。刚刚跑过去两个你追我赶的懵懂少年,后面跟过来一位颤颤巍巍的卖鸡老妇。小纨绔策马,瘴气乌烟。老把式挥鞭,车轮辘辘。
待拉货的马车进了城,只见远方一位身材魁梧的青衣文士,带着一名红裳侍女徐徐而来。
那青衣文士手中摇着一把纸扇,颌下飘洒着一部长须。别看他浓眉小眼,大鼻厚唇,面相忠厚愚钝,他的步履之间却隐隐之中透露出一种骁勇雄姿。
那红裳侍女秀发如云,面似桃花;柳眉捧莲,星眸溢彩;鼻梁纤巧,耳婉润玉;肤如凝脂,唇若樱桃。婀娜细柳扶风,款款灵蛇游水。形容妖冶多姿,顾盼妩媚勾魂。
红裳侍女身后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她一边亦步亦趋的跟在青年文士身边,一边好奇地东张西望。
青衣文士带着红裳侍女徜徉在浔陶古镇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尽情欣赏着花花世界,肆意浏览着人间百态。
就在岳尊目不暇接的时候,前方迎面走来一位白衣秀士,秀士抱拳施礼道:“朝见晴川蕴紫气,午来闹市迎高朋。这位兄台器宇非凡,必是饱学雅士,小弟南鸣徽这厢有礼了。”
岳尊站住身形,定睛一看,面前恭恭敬敬的站着一位白衣秀士,那秀士沈腰潘鬓,潇洒俊逸,手中握着一把檀木扇,抱拳拱手,正面带微笑的施礼问好。
白衣秀士的身后,跟着一双蓝衣侍女,她俩一个抱着瑶琴,一个带着玉箫,两女花开并蒂,大乔小乔一般俊俏,若是跟龙默琴比较起来,倒是逊色了三分妩媚,黯淡了七分勾魂。
岳尊赶紧还礼:“阁下谬赞!岳尊徒增年齿,或可忝称兄台,怎敢混珠器宇雅士,钓誉沽名呢。南贤弟出口成章,才气纵横,岳某敬佩之至。”
南鸣徽一拍手中折扇:“好!听君一语,如饮琼浆。岳兄若是不嫌南某才疏学浅,见识浅陋,能否赏脸让小弟做个东道,醉仙舫中,听琴赏花,以诗佐酒,畅谈天下,岂不快哉?”
岳尊到浔陶来,原本是替夏语沫送家书的,本想找人打听一下其父夏亦樵家住在何处,这个南鸣徽看来是个游手好闲的主儿,想来对这浔陶古镇应该了若指掌,不若就应了他的约,顺便打听一下好了。
岳尊想到这里,就抱拳笑道:“多谢贤弟盛情,愚兄就厚颜赴会了。”
南鸣徽展臂虚引:“岳兄请!”
醉仙舫!
南鸣徽和岳尊在一张临窗的桌前对面而坐,双方侍女各列两厢。
酒菜流水而上,南鸣徽替岳尊斟上一杯酒赞道:“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你我能在闹市相遇,必是前生有缘。满饮这一杯,祝你我友谊地久天长。”
“多谢贤弟盛情!”岳尊举杯一饮而尽。
两人饮过几杯过后,南鸣徽问:“岳兄!我见你风尘仆仆,想必也是赶了远路来的,不知道你来浔陶是寻亲呢还是办事儿,小弟愚陋不才,家父却有几分浅薄人脉,或许可以帮衬一二。”
岳尊先抱拳致谢,随后道:“岳某此次千里游学,只为增长些阅历见闻,倒也无甚要事。只是途中顺便帮朋友捎封家书,却是要送给夏亦樵老爷家的,不知贤弟可知晓夏家府宅何处?”
南鸣徽闻言,面色一变:“夏家?”
岳尊见他神色大变,心中一惊,他不动声色的道:“对!就是夏家!”
南鸣徽一愣神儿,随即恢复了笑吟吟的模样:“啊!失态!失态!岳兄见笑了。来!来!喝酒!喝酒!”
南鸣徽把杯中水酒一饮而尽,然后道:“夏家本是镇中贫户,三代都以卖豆腐勉强为生。夏家发迹于三十年前,首昌家道的是夏启璋老翰林。夏翰林官至户部尚书,十五年前,以至花甲之年的夏翰林卒在云州任上,留下渔樵耕读焕五子,琴棋书画凤凰六女。”
南鸣徽稍稍整理思路道:“夏翰林作古后,五子各承家业,星散在燕山各处。这夏亦樵就继承了老翰林在浔陶古镇的一份产业——浔陶豆酱坊。
夏亦樵的夫人林氏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唤作夏可文,女儿唤作夏语沫……”
南鸣徽讲到此处,竟然不由自主的怅然失神起来,岳尊见他怅惘若失的神态,就不难猜出他对那夏语沫,恐怕也是情根深种。
片刻之后,南鸣徽突然警醒过来,南鸣徽嫩脸一红:“岳兄见笑了!”
岳尊淡淡一笑:“南贤弟是性情中人,何来见笑之言,那夏家后来怎样?”
南鸣徽叹了一口气道:“六年前的九月初五,浔陶镇来了一位神秘的女神医,那神医听说夏夫人被儿子气出了怪症,浔陶的名医各个束手无策,她就主动去夏家登门拜访,替夏夫人医治怪症,女神医果然妙手回春,仅仅一剂汤药就治好了夏夫人的胀气怪症。”
岳尊奇道:“这不是挺好吗?贤弟又是因何唉声叹气?”
南鸣徽道:“那女神医在夏家见到了夏语沫姑娘,说她具有什么上品人魂的资质,是修仙的绝好材料,露了几手仙术之后,就把夏姑娘给带走了。可怜那夏夫人思女心切,终日以泪洗面,日渐憔悴,前年秋天九月初五……就已经撒手人寰,香消玉殒了。”
岳尊:“啊?”
南鸣徽叹了一口气道:“那夏可文是个嗜赌如命的家伙,夏夫人的亡故,其中大半罪责,却是该由这个逆子承担的。他今天在赌场输了田契,明天输了酱坊,后天又输了府宅,最后连妻妾也尽数赔了进去……要是老娘能卖钱,他定能将老娘也输了出去。
先是因夏可文输了田契,夏亦樵老爷一股急火攻心已经卧病在床,那赌鬼一心想着捞本翻身,又以酱坊为注,结果又把酱坊给输了,夏亦樵的病情是雪上加霜。抵押府宅,质押妻妾,一心捞本的夏可文因为输红了眼睛,越陷越深。那夏老爷在屡次三番的打击之下,终于承受不住,于去年冬天一命呜呼驾鹤西去了。
现如今,夏亦樵老爷家这一支,已经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除了那个终日苟且偷生的夏可文,连个喘气的小家雀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