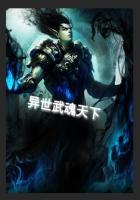“阿姜,已经洗了两遍了。你也去洗漱一下。”熊俊君拉住左姜的手。
“你知道他最怕脏了。在你营里时,每次你都骂他浪费水。”左姜平静地说。又去擦着首阳的身子。
“阿姜。”熊俊君心疼地看着左姜,无言相劝。只好看着左姜又再擦首阳的尸首。
“谭老将军!”熊俊君看见谭葭进来,行礼。
“父亲。”左姜看见谭葭,也轻声叫着,然后又继续擦着首阳。
谭葭看看熊俊君,熊俊君心痛地说:
“已经第三遍了。”
“来人!”谭葭叫着,进来一个侍卫:“抬走尸体,穿衣冠帽入棺。按照谭家一等奴役入殓。”
左姜抬起头,恶狠狠地看着谭葭,推开抬尸的侍卫。
谭葭走过去,“啪”打了左姜一个耳光。
“老将军!”熊俊君走过去,一把把左姜拉到身后:“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她也是一个血肉之躯。”
“抬走!”谭葭继续命令着。左姜倒是安静地站着,看见首阳被抬走。
熊俊君拉拉左姜的胳膊:
“阿姜,你还好吗?”
左姜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抱着脸,一点点红色的泪水滴在地上。她寂静无声地哭着。熊俊君的眼中溢满泪水。
谭葭走过来,抱住左姜的头:
“姜儿,孩子啊!”
“父亲,姜儿有罪!杀死母亲,又杀死首阳。”左姜压抑地哭着。
“孩子,战争本就是死人的游戏。谁死都正常,怎么死都是意料之中,死在哪里都是他们的命。和你无关。”谭葭沉痛地说。
左姜慢慢平静,谭葭安排侍女伺候她洗漱干净。熊俊君一直在外面守着,他有点不安心。自从他们入了谭家军,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左姜如此失态。即使谭硕当年被杀死,左姜只是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一觉未睡,却未掉一滴眼泪、未曾一句失常。
“熊俊君!”左姜穿着干净的衣服出来,看见熊俊君。
“老将军还在等我们。”熊俊君淡淡地说着,眼睛却无尽询问和担心。
“我已经平静。”左姜试图微笑一笑,却没有成功。
“父亲。”左姜走进屋,看见谭葭坐在灰暗的灯光下:“让父亲担心。”
谭葭点点头,示意他们二人坐下:
“武侯已押在大牢。下一步行动要如何?申国可有安排?”谭葭说着,语气却很焦虑。
“我已派人报告申浚王胜利之事。同时让申浚王派人送谭佑公归国。明日再派人将武侯押至申国。”左姜将后续安排告诉谭葭。
“姜儿,朝廷之上不可一日无君。”谭葭看着左姜。
“谭佑公明日启程,后天就进入谭国国境。所以明天休朝一天,行吗?”左姜询问谭葭。
“你确认明日谭佑公能够启程?”谭葭担忧地问。
“当日申浚王承诺与我,一旦胜利立刻让谭佑公启程。”左姜回忆着:“父亲,担心什么?”
“万事皆有可能。明日再看看。我会让武侯君签署昭曰:明日休朝。”谭葭说。
“父亲,通知一下内务府,告诉大臣们就可以了。怎么还让武侯君出面?”左姜困惑地问。
“姜儿,糊涂。谭葭只是一介臣子,怎能做王之事?那谭葭岂不成了里外勾结、篡权夺位的忤逆之臣了?”谭葭生气地说。
左姜一惊,猛然站起:
“父亲,我连夜回申国,亲迎谭佑公归国。”
谭葭和熊俊君也站起来,吃惊地看着她:
“为何?”
左姜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谭葭:
“父亲,申浚王恐有变。”
谭葭读罢信,坐回椅子上:
“姜儿,武侯君果真按照信中所说交战时方拿给你?”
“是的,父亲。”左姜说。
“此信确为申浚王所写?”谭葭又问。
“是的,父亲。有他的玉玺印章。”左姜又答。
“那你为何没按照信里所写去做?”谭葭盯着左姜问。
“父亲,若是你,会这么做吗?”左姜问谭葭。
“兵列阵前,不得不发。”谭葭沉着声音说:“申浚王知道你肯定会开战。所以这是计。”
“信中说什么?”熊俊君看着他俩越来越消沉。
“申浚王给武侯来信:我会兑现当初承诺,让你为王。阿姜将军此番进攻谭国,只是做给天下人看。等你们在都城之外见面,将此信交给阿姜将军,阿姜将军自会懂王的安排。谭佑公之事,勿忧!”左姜缓慢复述着,申浚王的布局也慢慢清晰。
“武侯相信了申浚王,所以带了很少兵去应战。”熊俊君担忧地说。
“父亲,我现在连夜赶回申国,亲自去接谭佑公回国。”左姜站起来说。
“姜儿,将受王控,抗令违令者,斩!此为军律第一条。而且你一走,申国士兵对谭国的举措将很难预料。”谭葭提醒左姜。
“父亲,明知有诈,不能坐视不管。”左姜慷慨而言。
“姜儿,或许等待是现在最后的方法。申浚王的答案可能已经在路上。”谭葭忧伤地看着左姜。
“父亲……”左姜看着谭葭的眼神,有点手足无措。她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把所有的事情回忆了一遍。
左姜慢慢睁开眼睛,脸上浮现一丝嘲讽的笑容,对谭葭说:
“父亲,姜儿鲁莽了。过高估量了自己的能力。”
谭葭点点头,过了一会儿说:
“姜儿,打算如何应对?一步错,万民疡。”
“父亲刚教孩儿:等待。”左姜笑笑说:“再难的日子也会有结束的时候。”
“顺势而为。”谭葭再交待着。
“阿姜,何不退出?隐姓埋名,安稳度日。”熊俊君忧心忡忡地劝着。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天下纷争,何处安宁?”左姜反驳熊俊君,沉思一会儿说:
“慢慢等。父亲、熊君去歇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