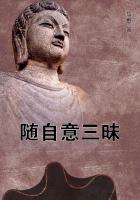兴许突然想到了有什么可以凭恃的,姬文光跳下了龙座扶手,双脚仍然立在龙座软垫上,脸现得意之色,指着太屋内众人“嘿嘿”笑道:“你们宦官不行,你史官也不行。嘿嘿嘿!他康王庄王泰王更不行,百官们都对朕俯首称臣。”末尾,他洋洋自得宣称,“朕的龙椅稳若泰山,朕的江山固若金汤,朕的天下九州兆民沃野千里,哈哈哈哈!”
皇帝疯狂,龙光四散,满室斛簌。
张靖走到业已气馁的姬文光面前道:“皇上圣主,您多虑了。方今天下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四夷臣服敌顽授首,大臣戮力百姓同心,天下人感恩戴德,正是盛世欢歌之际,没有人会想要对大周不利更没有人想要害您。”
“呸呸呸!你个阉货!肮脏的东西,这个时候拍朕的马屁,真不是东西!”姬文光厉然变色,不仅对着张靖拳打脚踢,还疯狂地吐了几口浓痰,吐在其脸上。
帝心如铁,臣心如水。众人看到扬名第一的内侍张靖受此大辱,有替张靖忿忿不平,有怕皇帝震怒殃及自身的,也有表面紧张暗地里却大是快意的。不论如何,这情景下无疑所有人都将头压得更低了。唯有张靖顶着一头浓痰如顶佛光安之若素,颇有点唾面自干的气概。
兴许是宣泄累了,姬文光突然坐回御座,歪着脑袋倚在靠背上眯着眼睛盯着太屋屋顶,看得出神。
张靖向趴在地上的一个小内侍使了个眼色,小内侍悄悄然爬起来退出去。不久,两名抬着装热水和冷水的木桶以及盆瓢等用具的内侍掀帘而入,将木盆等放在姬文光的脚边。
张靖不动声色地蹲下,给木盆里一瓢半瓢地添水,试了试木盆里的水温刚好,亲自替姬文光脱下了靴袜,又将他的脚面慢慢地引导放到木盆里。姬文光舒服地哼了一声,慢慢地舒展了紧张僵硬的筋骨。
姬文光一声不吭,张靖也一声不吭极为认真地替他清洗着白皙但青筋冒露却少有血色的脚面。脚底下跪着的一片人影都在偷偷观望。许久,姬文光恢复神态,口气温和地对张靖道:“刚刚苦了你们了,大家受委屈了,都起身吧。”
众人舒了口气,却大气都不敢喘。跪在那里互相观望。直到张靖率先道:“皇上都说了,都起来了吧。”众人才依依战战,狐疑十分地倒退到角落才站立起来。
张靖面色如常道:“雷霆雨露,均是天恩。圣上金主之所以如此待我,均是引我等为亲信之举,怎敢说苦呢?况且圣上一言警醒犹如棒喝,实是解了我等逆行倒悬之厄,从长时间看等于是普施恩惠于我等,奴才等谢恩都来不及呢,又怎能说委屈?”
“嗯。”姬文光安心地享受着张靖的捏脚,“张靖。之前卫盐推荐的那个刘世让你觉得怎么样?”
张靖搜索脑海道:“刘世让,这个人履历没有问题,带兵有一手,只不过听说人品方面有些微瑕。”
“对!”姬文光一合掌道:“此人为人确实有一些毛病,不过只要他能够治军取胜为朕讨伐戎贼,朕容许他有些瑕疵也无妨。毕竟他是卫盐推荐的人,所以才放心用他。朕现在把整个雍州和西京的安危还有朕的五万精兵都交给了他,五万边军也给他随意调动。要兵给兵,要饷给饷,已是最优条件了。只盼他能早奏凯歌,只是他却太令朕失望了。这一年多他一直按兵不动,劳师糜饷,一日糜废半京师,一年糜废半江南。他明知道大军一日不动朕就一日不得轻松,朕的整个朝廷犹如戴了嚼头的牛马,进退不得,可是他依旧如此。”顿了顿,当着张靖的脸,姬文光道:“雍州刺史赵广汉上奏书弹劾刘世让打了败仗,损兵数千人,却隐瞒不报,应当押解至有司量刑处置。朕聆此讯寝食难安,已经下旨让刘世让自己进京述职了,这次一定要当面让他知道,朕不在乎损失多几千兵,朕在乎的是朝廷已经支撑了两个三年,再也支撑不下去另一个三年了。他干的了就干,干不了就下台换人!百姓困苦朕也无时无刻不烦忧,他这个雍州将军兼西京招讨使就是来替朕分忧的,不能替朕和百姓分忧,他早该下台了。”姬文光缓和了下语气,“估计不出十日他就会到京城了。结合张甲的汇报,朕要好好跟刘世让谈一谈,相谈促战。”
“是啊。”张靖点点头,“纸上笺牍终究不如面对面详谈清楚。张甲刚好要从雍州回来,比刘世让还快一点,最快要一两日就到京了。到时候先让他把雍州的情况再将刘世让的动向亲自汇报一下。”
“哦!”姬文光闻言有些意外和不悦,但他还是暂时按住了。“卫盐的身体怎么样了?”
张靖道:“看样子了。年纪大了,肠胃不好,牙口也不行,走路都要人扶着。”
姬文光闻言感慨系之道:“时光荏苒啊!朕还记得当年朕小的时候卫盐每天背着朕从东宫到父皇寝宫请安,风雨无阻,又常陪着朕读书到深夜。想想那时虽辛苦却充实,家国大事都在父皇一人肩上担着。父皇宴驾,比朕现在还少几岁。朕十四岁登基,风中雨中没想到一晃十八载了!”
姬文光陷入了沉思,又突然一愣回醒了过来。“你明天抽个空去看看卫盐,有什么需要跟朕提。别看现在宫里困难就不敢提,该紧衣缩食的自然要紧衣缩食支援军国大事,但宫里老人的保养也要提上,不能让别人以为朕亏待了老人。”
“是。”张靖道,“老师一直想过来看圣上的,问了我几次了。我把情况一说,他就一直顾虑圣上的忧虑,所以没来成。”
“哦?”姬文光振奋道,“卫盐也想朕,太好了。让他有空就过来,朕好久没有听他的卜筮,让他过来给朕卜筮国运。”
“好,我会把圣上的意思传达给他。”
“对了。”姬文光又想起来,“张甲不是宫里派去做监军的么?还不到三个月怎么又回来了?”
张靖停顿了一下,“内朝把他从监军的位置上调回来了。”
姬文光默然半晌道:“朕知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死人盈野是家常便饭。朕也知道张甲是你亲弟,你有意维护才把他从险境处调回来,但他是宫里的代表,代表的是朕的权威和耳目,他一回来朕就如同少了一双耳目了。西边的事情也要有人跟着。”
“奴才知道兹事体大,内朝已经让参议大夫葛良前去接替他。”
“哦,葛良?可靠么?”
“内朝复议的人选,十五岁以神童闻名京师,才学过人,获三公举荐,今年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有多谋善断的名声,家世也清白,一直以侍中的参议大夫散着。所以内朝同意了。”
“十五岁闻名京师获得举荐三十岁才供职,这么说朕甫一登基他就入朝了?朕侍中的参议大夫都散着?那侍郎呢?郎官们呢?内朝没有事情做么?”姬文光不满地瞪了张靖一眼,“你们內监不要什么事都把持着,要让侍中的文官多管管事。他们都是各地举荐的人才,不能埋没了。要让朕的内朝活起来!”
“是,奴才明白了。”
“明白就好!”
张靖又解释道:“圣上,张甲不成器,入军之后地方人颇有怨言。这一点不因为他是舍弟我就替他掩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人打仗最重要是随机应变,善择良机,宜攻取则击敌破壁,宜守御则凭坚据守。与其坐看舍弟将来贻误军机被军法从事,坏了皇上和宫里的名声,不如早早换人派遣个多谋善断的谋臣与协助猛将。葛良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才派了他过去替换张甲。期望谋臣猛将能勠力同心,这一点请圣上拭目以待。”
“老成谋国之言。”姬文光感叹道,“若朝中大臣都如你一般,朕何愁西戎不灭!”
张靖谦虚道:“圣上过奖了。像卢九蕴,周密,羊柯他们之才德我就难以企及。”
“哼!”姬文光道,“他们什么都好就是气量狭小!整天逮着诸位鸡毛蒜皮的事都不放过。真应该让他们来听听,枉他们还整天在朕面前诋毁爱卿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张靖淡然一笑道:“圣上何必多虑,诸位国老他们也是拳拳忠君心切罢了。”
“还是你懂事理,知分寸。”姬文光愤愤不平,“他们都是太倚老卖老之辈,太不知进退。要么都是弄臣,油嘴滑舌沽名钓誉。一代新人换旧人,以后朝堂之事再敢多嘴就让他们统统回乡里种田去!”
“那他们可要感谢陛下了。”张靖一笑道:“圣上,若几位国老都回乡种田去了您只怕就太孤独了,没人闹事,说不定您又得下旨令请他们回来。”
姬文光“嗤”地一笑,心情放松。“还是你知心解意。这些个老头儿!这么有力气跟朕争,他们要有你一半知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