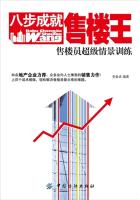我手上脚上都裹着白纱被安置在榻上,瞧着琅篁在书桌旁奋笔疾书。
“不许动!”我身子甫一微微抬起,他的声音便到了跟前。明明,明明他眼也未抬手也未停。
我诞笑着道:“我看你也挺忙的,我还是换个地方躺着罢。”
他挑眉,侧过头来看我,“怎么,这张床榻长了刺,让你浑身不自在?”
“不是床榻的问题……”我嗫嚅。
“那你是花脚猫么?”
“啊?”
“听闻人间的话本里将此物形容那些在一个地方坐不住的人,我看,挺适合你的。”
我干巴巴笑了两声,道:“您太抬举我了!我们犬科跟猫科还是有点区别的。”
琅篁不应,复又低下头去。我正酝酿下次逃离他眼皮底下的机会,他忽地将笔一扔,起身,到了近前,又俯身,呼吸都扑在我脸上,依旧问:“还想跑?”
我心有不甘,扭头望了望窗台露出了两个脑袋,他们在那里等了半天了也没见我逃出去。“我看你写奏折写的挺欢的,也没我什么事儿,我出去换换气还不行么?”
“换换气?换换气的时间你把灵元丢在了锦官城,换换气的时间被繁芜伤成这样,若若,你把每一次换换气的时间都变成了生离死别……”他顿顿,眸子里的悲伤又添了一重,“赌你的命?若若,不过是一个繁芜而已,不过是一份繁芜和贺兰的爱情而已,你为什么要拿你的命做赌注?”
我一怔,多少年来他对我的做法不置一词,我说了做了他不说一句好与歹,只将最后的结局看在眼里。到如今,他终于说了吗?
他的脸一点点离开,眼眸里的感情也都跟着遥远起来。我笑笑,道:“可是,你还是会帮我的,不是吗?”
他苦笑起来,半晌点点头:“是啊,我会帮你。只要你愿意,我都会帮你。我会启奏帝君,说贺兰娶了悍妇,求他销了繁芜的仙籍。你的赌注下的这么大,我又岂能不添把大火。”
“不,还不够。”我笑起来,身子又抬起来,他离我将远不远,我用裹着白纱的手腕将大半个身子撑起来,又快又准的在他唇上啄了一下,“看,这样就够了。”
“登徒子,啊,不,登徒女……”如歌的声音最终被祝余掩了下去,随即窗外发出慌乱急促的脚步声。我趁着某人发愣之际,终于从书房逃了出来。真是不容易。
是夜,我在若木那里碰到了祝余,他就着月色正给若木浇水。松软的土地又形成了小小的漩涡,那里便也多了一个月亮。
“浇得太勤快也不大好罢?”我走近了说。话音刚落,祝余手里的那一瓢水又倒了下去。我叹了一口气。
“若若……”我眼睁睁瞧着祝余又舀了一瓢水,所幸他唤着我名字的时候手顿在半空并没有动作。“我们都瞧见你亲琅篁了。”
“然后呢?”我盯着地上的那个月亮看。
“原本你的事儿轮不到我来说三道四,但若若,我们一起在招摇山长大的,我不希望你迷路。倘若你不喜欢他,就不要因为感激他而跟他在一起。我知道,你喜欢凌空,喜欢了许多年。”
我静静等他说完。
“我也知道琅篁喜欢你,喜欢了许多年。所以你不能因为凌空死了,你就转而投入琅篁的怀抱。你是因为空虚还是因为感激,若若,你想清楚了么?”
我的脸僵得很厉害。
“若若,原本我自己就是个移情别恋的坏人,更加没有资格说你。但,但,我不想你将来后悔,也不想琅篁委屈。”
“你喜欢我么?”待他说完,我问了一句。
小祝余错愕,立在那里不知如何作答。我欺近一步,作势要亲他,他惊慌失措,往后退去,被身侧的木桶绊倒,跌在地上,半桶水都浇在身上。风起,若木的叶子发出欢快的声音。我笑起来,却异常严肃得道:“你看,你不会亲一个不喜欢的人。倘若你是个例,那么若是琅篁站在这里,大约你也不会亲他。我们都是有感情洁癖的人,若心里没有这个人,面上也做不出来亲近。方才你问我是空虚还是因为感激,我可以告诉你,都不是。我是因为喜欢。”
“明明……明明你那么喜欢凌空……”
“他是画里的人物,我再喜欢都握不到。这个道理,一千年前我就懂了。所以你看我,在他身边那么多年,他身边也没别的姑娘,我都没有坦白心思。”
“那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琅篁的呢?”
我抬头,又开始盯着天上的那轮月亮,喃喃:“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约是锦官城的那场大火里吧……我闻到了中药味,终于明白多年来我太过执着别人对我的坏,虽口口声声说念着某些人的好,却从未参透其中的深意。失了灵元反倒清醒不少,那时候我多后悔自己将要死去,再也不能站在他面前同他笑着唤他的名字说出自己的心意。即便,即便最后死在他怀里,我也不能原谅自己先前这么愚笨。
“那那那琅篁知道你的心意了么?”祝余终于爬起来,结结巴巴问道。
“大约只当那是我为了逃跑使出来的计策吧。”我苦笑一声应道。
一千年过去了,他遇着的姑娘可比当年招摇山的小师妹多多了,我不信没有入他法眼的,我不信他还如当初那样喜欢我。时过境迁这句话,我比谁体会的都深。知道了会怎样,不知道又会怎样,终有一日,我会带着如歌从乐游山灰溜溜走掉。这个准备我早已做好。
---
琅篁奏折终究呈到了帝君那里,因为亲的那一口,他回头又补了一句,说繁芜伤得不仅是他招摇山的同门,还是心爱的女子。不知这消息传到贺兰那里,他要怎么说我们狼狈为奸害苦他。
贺兰的消息果然灵通,琅篁前脚回了乐游山,他后脚便到,一巴掌拍在琅篁肩上,苦笑道:“老弟,你又何苦凑这个热闹,还嫌我不够乱么?”
我瘸着腿脚走近,打趣道:“果真乱了么?也没见你怎么憔悴啊。”
贺兰偏过头来看我,道:“噢,若若,你手上脚上的伤好些了么?我给你带了药来。”
说罢就往怀里掏。不枉多年的兄弟,我们逼他到这个份上,他还要慰问我。
我接了药,并不说谢谢,反正前几日已经说过不喜欢这样的他了。今日我又添油加醋说道:“只有药么?是不是该带着你家那位登门负荆请罪啊?”
“若若,你就别跟着起哄了。眼看着帝君马上就要顺了你们心意销了她的仙籍,我却连她人影都没见着。”
“这算是畏罪潜逃么?”我惊问一句。
看样子贺兰是顾不上我了,只追着琅篁问:“一定要这样做么?你原本也知道她是无心,女人大抵都是这样爱吃醋。日后你遇见了别的姑娘,若若也将是这个样子。你将心比心,撤了那份奏折,跟帝君说是一场误会罢。她一个人修了五百年前的仙,只有一把琵琶陪着,其中的辛酸我们这些人尚且不能体会,好日子还没过多久就断了后路,你让她怎能不伤心?”
他絮絮叨叨说了一通,将我也拉扯进去,换来的不过是琅篁一句:“我做的怕远比不上你做的让她伤心罢。”
我从未见过如此低声下气又如此落魄不堪的贺兰振彦,他踉跄数步,神情在我的视线里模糊起来。只听他凄惨惨笑了两声,道:“兄弟么,真的是兄弟么?你见不得若若受伤,我也见不到她受伤啊!”
琅篁一直不松口,他终究无功而返,落拓般离了乐游山。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贺兰,早点看清自己的心罢!”琅篁对着那背影轻声道。
我睨了身旁的人一眼,道:“戏演的不错,这些年人间的话本没少看罢?”
~~~
亲上了,终于亲上了,真是不容易啊。
大家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