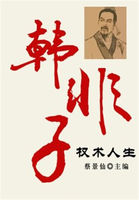先父去世后,家里就母亲一个劳力,爷爷也跟着我们吃饭,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没见过他干活。
那一年夏天,都需要浇地,妈妈就请隔壁的邻居帮忙,第一次还好,邻居是个好青年;第二次母亲请他帮忙时,邻居的老父亲在家哭闹着,不让儿子帮我们,避我们如蛇蝎,谁让我们是孤儿寡母呢。到卖桃的时候,妈妈要带我们一块去,对门的邻居先我们碍事,脸色难看至极,只去了一次;第二次,那个邻居就不跟我们一块儿卖桃了,谁让妈妈带着我这个累赘呢。
我还有个大伯,他家有两个儿子。有一天,跟着他们一块儿玩,到了一块花红园外,那个大儿子就伙同其他几个欺负我跟哥哥;我赶紧呼叫,妈妈很快赶来,教训了那个大哥;结果婶子闻讯赶来,又跟我母亲吵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那婶子,自打记事儿起,就对我很冷淡,是因为我没爹了吧。记得,还有一个姑姑,先父去世前,去他家还有笑脸;先父去世后,那种亲切就没了,也许他们家确实也困难吧。
小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会发烧;有天夜里,我又发烧了,妈妈去叫爷爷,爷爷根本不搭理我们;外边下着雨,妈妈背着我,哥哥在后边给我们打着伞,去村里的卫生所,给我打针、拿药。等到地方,妈妈身上湿透了,有淋的雨,更多的是出的汗;至今想来,老头的所作所为令人心寒。本来我们家还有一屋子木头,但是老头背着我们给全卖了,这事儿把母亲气坏了;于是,母亲四处请人评理,少有同情,更多的是冷眼。
村里,有个叫罗豆儿的,喜欢我母亲,愿意照顾我们。别人问我,愿意他做我爸爸不;我都会说,愿意;因为,我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好人。现在想来,母亲应该是替他着想,怕我们孤儿寡母拖累他吧。高中毕业后,我被母亲赶出来打工,在工地上遇到了罗豆儿,好像还是单身,很邋遢;看得出来,他过的并不好,那时候母亲做过肿瘤手术后,在家休养,过的也不好。这世间,人与人的关系就是那么奇妙和无奈。
曾经有一次,村里有一家买橘子,妈妈骑着三轮车带我去了。我喊着:“来一袋!来一袋!”母亲跑去跟物主说了句什么,现在想来应该是家里没余钱,准备赊一袋。但是,那个男人勃然变色,对着我们说:“滚出去!”我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的尊严被踏的粉碎,母亲瞬间苍白如纸的脸。不管何时,只要那个男人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把他的头卸下来,一定!
母亲曾经想把我过继给本家一个在北京做军官的亲戚做孙子,本来把我哄得很好;但第二天那个舅爷来时,我还是支支吾吾地不愿意,事后我对母亲说:“就是一块儿喝西北风,我也跟你一块儿过”;也许就是因为这句话,母亲再也没离开我。现在想来,当初如果我答应过继给人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起码,母亲能少受点苦。
有一天落黑儿,舅舅来我家了,很是严肃;给我跟哥哥几块钱,让我们出来玩儿;那一天,我们来到代销点儿,很奢侈地一人买了一块儿鞋底儿巧克力;那一刻,应该是我在桃庄记忆里最幸福的时刻了。等回到家,家里的物件儿都收拾到架子车上了;趁着夜色,我们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妈妈,我们还回来吗?”
“你想回来吗?”
“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