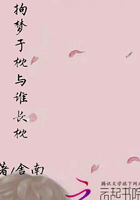叶求知瞧跳出之人乃是个和尚,出手姿势不凡,怕他伤了马儿,当下挥掌迎去。但觉对方真力绵软浑厚,他那一掌便如泥牛入海,非但没有激起浪花,连丝涟漪都不起。马儿四蹄生风,一头撞进去,恰似撞进了一团棉团里,顿人立嘶叫了起来。叶求知纵跃下马,一把牵住它,任它挣扎也无济于事,向那和尚看去,见他年纪甚轻,也只比自己略长而已,又敬又佩道:“多谢师父出手,才拦住了这匹惊马。”
那和尚道:“施主好神力,倒是小僧冒昧多事了。”
叶求知道:“师父说哪里话。”心意一动,问道:“师父可是前往南山寺?”
那和尚异道:“施主怎么知道?”随即省悟此去城外只有一家寺庙,我这个和尚不是去南山寺,又去哪里。
叶求知道:“我昨晚听到有人说起师父。”当下将昨晚酒楼一事说了出来,最后道:“这几人说要在路上会一会你,师父法力高强,但不免势单力孤,不如避他们一避。”
那和尚笑道:“不碍事,我也正要会一会他们。”
叶求知道:“他们含忿在心,恐怕不是那般易与。”
那和尚看了叶求知一眼,笑道:“多谢施主好心相劝,非是小僧争强好胜,而是这几人实与我佛大有渊源,其门派是我教下的旁门分支。不过他们的道统已失,目前只剩下他们这凋零几个人,我若再不出面,过得几年,六识门想必就要不复存在了。”
叶求知心想:“原来还有这么一番缘故。”天下门派大多出自道佛两家,六识门源自佛教也不足为奇。叶求知说道:“听他们言来,并不知自己出身贵教,师父的好意他们未必会领情。”
那和尚道:“那也无法,总不能眼看他们衰亡。”
叶求知不以为然,心道:“兴衰存亡自有命数,这六人的修为固不甚高,其门派也衰微至极,但未始就这么一直一蹶不振,哪天会重新崛起也说不定。”
那和尚观他面色,猜出他所想,说道:“你道他们其中三个为什么一直都戴着斗篷不脱下?”
叶求知心中也是奇怪,问道:“为什么?”
那和尚道:“只因他们长相太过奇特,怕拿下来吓着别人。”
叶求知道:“那有什么,相貌乃是天生,又有什么可耻之处,何需遮掩?”
那和尚摇头道:“他们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练功所至。”
叶求知惊道:“他……他们是妖宗邪修?”所谓妖宗邪修,是指取法妖族,练那邪术的。此二者练之越久,身体就会出现异状。
那和尚仍旧摇头,道:“那倒不是,他们是练不得法。六识门的功法早已失传,十不留一,久练无益,遗患无穷。”
叶求知恍悟,他们边说边走,已来至南山脚下,那和尚道:“今日得遇施主,也算有缘,便此一别,望施主多自珍重。
叶求知道:“在下也正要上南山寺随喜一番,正好与师父一路。”
那和尚道:“那六人正在前面等我,你与我同去,不免会被他们误会,施主还是自去吧。”
叶求知道:“不要紧,我看那六人也不像蛮不讲理之人,就算误会我与你一伙,那就算是就是了。”
那和尚如何还不懂他的心思,看了他一眼,心道:“我只不过替他拦了惊马而已,其实以他之力,就算我不出手,也不会撞上路人,算不得什么恩情。但他明知前路有险,还坚要陪我,足见是个热心好义之人。”好在那六人是他故意相诱,早已有备,不虞有危险发生,但仍嘱咐道:“我若能好言劝得他们皈依我佛最好,但万一说僵了动手,施主还是暂作壁上观为好,我实在不支,你再助我不迟。”
叶求知答应一声,心道:“看来他还是怕我人小力弱,帮不上什么忙。”其实他出门之前,到门里兑了一些符篆在身,临敌之际大有用处。当下也不声张,只待觑准时机再作打算。
两人在路上互通了姓名,原来那和尚叫弘致。他们上得山来,走到山腰,忽听到石后有人道:“来了。”六个人打从山石后转了出来。那三师兄瓮声瓮气的道:“咦,怎么多了一个,这人的味道好熟悉?”
大师姐冷冷道:“此人昨晚在那酒楼上。”她眼力非凡,过目不忘。
五师弟叫道:“好啊,原来这和尚派人盯着咱们。”
这六人中,排行前三者都头戴斗篷,叶求知之所以能分出他们来,全凭体型和声音。这时四师弟一指弘致,道:“叽里咕噜。”
三师兄问道:“二师兄,老四说什么?”
二师兄道:“他说正主儿已现身,动手吧。”
三师兄道:“好。”提棍就打,只听呼的一声,此棍从左至右横扫过来,棍风激荡,山石滚动,草木倒伏。
弘致不想他们说打便打,话尚不及说,当下一撤身,让过棍子,掌力轻吐,将叶求知送出圈外,道:“来得好。”见三师兄堪堪扫到右端,又要反手回来时,立纵上前,在他棍端一拨。那三师兄此时恰旧力已尽,新力未生之际,被弘致顺着惯性往右一拨,身不由己地向后面的同门扫去。他高叫一声:“大家快躲。”
众同门齐齐一矮身,从棍下躲过。棍风过处,顿将大师姐和二师兄的斗篷卷落,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叶求知望去,只见大师姐容貌清秀,一双眼睛却大得出奇,几占了脸的三分之一。而那二师兄两耳犹在摆动,仿似一对兔耳一般,果如弘致所讲,生具异相,想必那三师兄也好不到哪里去。却见那三师兄犹如陀螺一般急急而旋,向斜刺里冲出,弘致的一拨之力,再加上他本人的一轮之功,那惯性何等之大,他又舍不得丢下那棍子,直被带得越转越远。
二师兄跌足道:“唉,那是老四说的话,我又没叫动手。”
大师姐被吹落了斗篷,露出真颜,羞恼道:“还说什么,这就真打。”
众人一听,齐齐上前,那二师兄回头冲三师兄喊道:“往石头树上砸,一砸就停下来了。”
那三师兄一听有理,转着圈儿往山石处旋去,但听乒乒乓乓一阵响,棍子如风轮般不停地砸在石头上,直打得石屑纷飞。
这边也已动上了手,二师兄使开双刀,如泼风一般,一刀紧似一刀砍向弘致。弘致倒纵前跃,身形不定,在众人之间穿插来去。五师弟咚咚咚跟在他身后,空有一身横练功夫,却追不上他。四师弟见弘致身法太快,众人一拥而上反易误伤自己人,便站立不动,一见弘致过来挺剑就刺。而大师姐则站在圈外,手持长鞭,她眼神锐利,弘致身形再快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弘致到哪儿长鞭就跟到哪儿,如影随形。在她真力催使之下,长鞭直如灵蛇蛟龙一般,或刺,或抽,或缠,有诸般变化,要论众人中最难对付的非她莫属。而唯一不动的,除了叶求知外,就是那个自始至终一直发呆的六师弟。叶求知暗扣数张符篆,一俟弘致不敌,就撒将出去。
双方缠斗一阵,弘致忽右手一扬,一团烟花射向大师姐。这烟花五彩缤纷,绚烂至极。大师姐猝不及防,眼前大亮,无数流光在眼里闪耀,忙闭上双眼,但瞳孔之中犹残留无数的金星在飞舞,不由得流下泪来。她是练眼之人,对光尤为敏感,烟花一出,无异废了她的绝招,使她再也无法看清眼前的战况。
弘致破了大师姐的神目,运力于喉,拢音成束,向二师兄狮吼一声。外人看来,弘致只张了一下嘴,二师兄听来却无异是深山滚石,空谷传响,震耳欲聋。他掩耳急退,耳鼓似要被刺穿了一样。他平日旦有风吹草动,飞花落地,无不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却恨不得耳朵聋了才好。
五师弟见异变突生,大师姐和二师兄一下子都相继受了伤,怒吼一声,挥拳直捣。他这时候含怒出手,铁拳捣出,狂风大作,大有崩山于拳下之慨。弘致不再避闪,转身面对五师弟,伸出一指对准来拳,摇头道:“你这一拳空有威势,却虚而不实。”
叶求知见这两人,一个静如处子,一个势如猛虎,一个斯文消瘦,一个孔武魁伟,一个纤纤一指,一个是砂钵大得拳头,其间的优劣高下分明显见,可偏偏弘致一副淡然自若,成竹在胸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