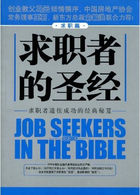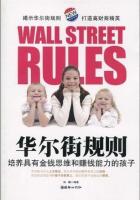陈姨娘惊得只说,你这孩子也忒是大胆了。
林珆漫不经心地说:“比不得姨娘的胆子。我本也没想着害人,这四丫头经了这一劫,想必跟咱们没甚妨害了。倒是姨娘别再弄神弄鬼的了,大伯母便是那会再不能生育了,她难道不会从三房过继?三弟跟二弟不也只差了一个来月?”
陈姨娘略有赧色,“为娘那会也是一念之差,我跟大太太孕期也不过差两个月,我不过是想抢在她头前生下长子。”
林珆禁不住鼻子里嗤一声:“长子又如何,那也是庶长子,能讨到什么好?何况我爹并非老太太亲生,以后分家析产,老太太的陪嫁也不会往咱们房贴补。”
娘俩正说着话呢,院子里有人扬声问:“敢问三姑娘在么?”
林珆听出是服侍父亲的大丫鬟雨霏的声音,忙开了门,把人往屋里让:“雨霏姐姐今儿怎么有空到姨娘这边来,赶紧进来坐,姨娘刚沏的竹叶青,我尝着味道很是清香,这秋高气燥的,正合适姐姐润润喉。”
雨霏赶紧道个万福:“给姑娘请安,多谢姑娘赐茶。奴婢不敢叨扰姑娘,专为给老爷传个话的。老爷叫奴婢来问问看:姑娘可记着老太太的话,去给四姑娘赔了不是了?”
林珆一激灵,猛可地想起这档子事,这一下午光顾着发脾气和跟姨娘摆龙门阵去了,赔不是这种事或许潜意识里就本能排斥的,忙陪着笑说:“劳姐姐跑一趟了,我本就是要去四妹妹那的,这不姨娘有点不舒服,老太太不是也说孝悌最重吗,姨娘怎么说也是我亲娘,为人子女的自是要过来看一眼才能放心的。”
雨霏斜了陈姨娘一眼,仿佛这会才看到姨娘,略福一福:“姨娘这会可好些了?”
陈姨娘的一双手都在袖子里握成了拳,面上却是满脸堆笑:“好多了。雨霏姑娘辛苦了。”
雨霏只略点点头,冲林珆说声:“姑娘赶紧去吧,奴婢这就给老爷回话去。”
林珆貌似不经心地问了句:“雨霏姐姐多会来的呀?站了这半天了连口茶都没喝上,倒叫我过意不去。”
雨霏本已走到院子里,闻言脚步不由得一滞,微笑着说:“姑娘不必介怀,奴婢也是刚到。”
陈姨娘耳听得脚步声渐渐远去,咬牙切齿地说:“这蹄子仗着老爷宠爱,连我都不放在眼里,多咱让她知道老娘的厉害。”
林珆不屑地说:“我劝姨娘还是省省吧,雨霏是老太太赐下来的人,连爹都不敢对她不敬的。何况她服侍了老太太几年,能识文断字的,老爷把她放在书房里侍候笔墨呢。”
陈姨娘不觉嗤笑说:“你爹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他要是能的话,不早科举出仕了?他也就比我强点,能写几句打油诗罢了,文章是断断比不上你大伯父的,就是诗歌我看也不如你三叔。还不是老太太出钱给他捐了个七品闲职,他也不用去点卯,不过在这府里料理点庶务罢了。”
林珆不觉在心里腹诽说,那你那会还要死要活地要跟着他?
陈姨娘叹气说:“好在这府里家底厚实,虽说地都由大太太集中操持,老太太却也先给了咱们这房好几间铺面,倒也不在这俸禄上打算。只是这雨霏迟早是个隐患,我看老爷书房里小厮伺候着也就罢了。“
“哼,”林珆轻轻嗤一声,“姨娘自以为未雨绸缪,那有什么用。爹要收用她,岂是姨娘能管得了的?爹娶赵姨娘孙姨娘那会,姨娘哭也哭了,闹也闹了,又有何用?”
陈姨娘也不觉暗自叹口气,年轻时贪图富贵,且也爱着林钊风流倜傥,谁晓得坏也坏在这风流倜傥上。跟自己好的蜜里调油的时候,山盟海誓,情深款款。岂知是深情而不长情,多情而不专情。
林珆见陈姨娘黯然,心里倒有点不落忍,低声说了句:“娘我先去了,你也别想太多,爹对你还是很好的。何况你有我和二弟呢,不比那赵姨娘孙姨娘强上何止百倍?”
陈姨娘目送着女儿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女儿太笨叫人担心,女儿太聪明了也叫人担心,这孩子才多大点啊,就能有这般心思,也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向晚斋里,老太太躺在一张红木的马架子★上,半寐半醒,碧沅轻手轻脚走过来,给老太太盖上张薄被子,老太太却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双目炯炯。
碧沅忙着告罪,老太太摆摆手,只看着刘妈妈:“妈妈我寻思了半响,三丫头虽然可恶,她最后那番话倒是有几分道理。”
刘妈妈以为老太太给气胡涂了,忙宽慰说:“老太太,三姑娘被二老爷娇宠了些,有时说话口无遮拦的,您别跟她计较,气坏了身子。”
老太太摇摇头,“四丫头从小多病多灾的,偏又才气甚高,我着实偏疼她些,晨昏定省都给她免了,走几步路也怕她累着了,连大门都难得出一次,反倒给她养成了个病西施。咱家里假山就那么点高,换了别人顶破天了也不过摔折个腿,她就能给摔迷糊喽。。。”凝思了一瞬,“碧沅回头跟四丫头说说,从明儿起,每日卯时中,上我屋练功。”
刘妈妈着实吃了一惊:“老太太,您这岁数,这身子骨。。。”
老太太不满地说:“我这身子骨结实着呢。”
碧沅紫菱吓得跪下:“老太太。。。”
老太太狡黠地一笑:“瞧把你们给吓的。都起来吧,我自有主张。碧沅替我修书给我那大弟妹,问问她府里的女教习黄大娘可还得用,甭管她现在还使着没,先借我几年,她那一房就一个孙女,那云丫头本就野,再习武几年怕是不要上房揭瓦了。”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刘妈妈笑着说:“真真这云姑娘是个男儿脾性,比咱们四姑娘还大着一岁呢,可比四姑娘淘气多了。早些年咱们跟着大老爷在京里的时候,那会子二老爷也跟着在京城里呢是吧。云姑娘有次来府里玩,把那马蜂窝都捅了,她和三姑娘四姑娘都被叮了好些包,三姑娘哭了好半天呢。”
老太太想起这档子事也不觉失笑:“那云儿也真是淘的可以。怨不得我疼四丫头,身子骨弱点,性情却是疏阔,自己满脸的包混忘了,看着云丫头脸上的包还只笑,三丫头可是足足哭了一个时辰,把云儿骂了一个时辰。”
林玚突然打了个喷嚏,嘴里嘟囔着:“谁在背后念叨我?”
却听一声娇笑传来:“四妹妹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呢?”
林玚眼见得一个华服少女款款进来,不由得眼前一亮:只见那林珆长了张小巴掌脸,下巴尖尖,水汪汪的一对大眼睛仿佛会说话,嘴巴却仿佛比那樱桃还小点,肌肤白里透红,吹弹得破。时令已入秋,她上身穿件银合色的银丝掐边的比甲,底下仍是穿着件淡黄色的百蝶穿花的真丝百褶裙,上边的蝴蝶和花朵竟是用蜀绣织法,活灵活现。林玚暗想:我要是个男人指不定也喜欢这个调调。
忙叫侍墨看茶看座。
林珆却是郑重其事地作了个揖,口里说着:“四妹妹,我这厢给你赔礼了!昨儿在假山那,为着点琐事争执,我失手碰到你了,害你立足不稳摔了下去。是姐姐的错,四妹妹大人大量,宽恕则个。”
林玚心里暗暗喝彩:这台词真是滴水不漏,好一个“失手”,好一个“碰”,这人不去做律师可惜了!
林玚只揉着脑袋说“摔迷糊了,记不太清了。姐姐既不是故意的,也不必在意。说什么宽恕不宽恕的”
林珆一时有点琢磨不透林玚这话的意思,只好含糊笑着点头。
姐妹俩喝着茶,说着些诗词针线的闲话,消磨了一个下午。
掌灯时分,林府华灯结彩,正厅里林府家宴。由于姑娘少爷们还小,也不特意分开男女,只略略摆了两桌,那林琇更是在席间穿梭打闹。
林钊心里暗暗叫苦,也不敢大声呵斥,只得叫自己媳妇管管。谁晓得这二爷自小跟着陈姨娘,兼之父亲溺爱,并不服气,哭着只说要吃这个够不着那个,叫自己亲娘夹菜。陈姨娘同着几个姨娘侍立在旁布菜,这会偷瞧老太太冰霜一样的脸,一眼斜过去又正好见着赵姨娘孙姨娘互相递着幸灾乐祸的眼色,也不觉大为尴尬。欲待呵斥,又恐平日里一向温言细语,这会子突然发狠,这孩子闹将起来越发不可收拾,只得低声哄劝说:“琇儿听话,安安静静的,晚间姨娘给你吃果子。”
老太太突然发话说,“这琇哥儿十足十的六岁了,只识得几个字,许多规矩还不甚明了,委实不像个大家公子,又一味的娇嗔使性子,惯得不像个爷们。我听说在家学里就不好生学习。我看明儿起,别跟着姨娘了,二太太偏劳多费点神,好生带着琇哥儿,”二太太忙站起来唯唯应声,只说必当尽心竭力。
老太太接着说,“原先几个姑娘是跟着吕先生学功课,吕先生过年前要回老家去,咱们也不用讲究那些个迂腐规矩,凡上了五岁的,无论男女,都一块上家学学去。我听说荣安侯家的家学不光自己家的孩子在里边读书,还对外招收学生呢。他们家的公子小姐知书识礼极讲礼数的。咱们虽比不得人家,也不能做了这益州城的笑柄。”
★马架子:四川地区一种实木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