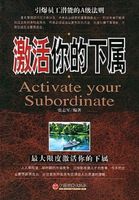这事过了没多久,任大胆一个人可以大胆地踏上那木楼梯。一天,从县城方向来了个自称是商雨轩女儿的二十来岁的姑娘。不,应该说是位少妇,困为他分明看到她是提着皮箱挺着个凸起的大肚子进的楼门。
她说她叫商紫霄,说着从脚下皮箱里拿出一支竹箫给他辨认。
任大胆不识字,但他是认得老先生的箫的,上面的字他的儿子任洪福还是认得的。任洪福把箫递还给他爹说:“爹,是商伯伯的箫。”
任大胆连忙提起箱子领商紫霄进楼:“小姐,请!”任大胆叨唠说小姐呀,你可回来了,我都急坏了,这兵荒马乱的,老爷也不回来。
任大胆问紫霄要哪间房,紫霄抬起她那紧蹙的眉开口说:“随便吧。”
这是任大胆听到的她说的第一句话,此后再也无话,只是点头还是用眼光应答。任大胆领她进了二楼靠东边窗子的一间房,另两间是老爷和女先生的。任大胆不敢把楼里发生的事说出来,硬着头皮全家人再搬回廊下。
商紫霄终日闭门不出,坐在楼上房间里凝望大海默默地想,或者说是看。她是回这儿生产的?为什么要来?是个谜。有时任大胆竟忘记了她的存在,脚步声惊醒她回眸凝望。看到她的目光,让人觉得似是有无限的心事像海深。才觉得她是活的,悄无声息地存在着。
商紫霄拿着一幅画下楼,手指客厅正堂。任大胆问:“小姐,你是要我给贴上去?”紫霄微微一笑,稍纵即逝。“好嘞!”任大胆把那画挂上去,取下原来的牡丹图。紫霄站在那儿静静地注视。
任大胆看那画,画上是个年轻的女人,他端详画上女人再看紫霄,很相象,分明是一个人。他问:“小姐,这画是您啊?”紫霄不出声,神情好似入了画,她盯着画上的女人,那女人目视着她和客厅里的一切。
商紫霄着一身的素白衣裙看画,画上的女人也是一身的素白。任大胆觉得似有一股的冷气从她们脚下冒出,冷得人心冰凉,他连忙出去。
当任大胆招呼小姐吃饭踏进她房间时,却看见紫霄的身子直溜溜地挂在房梁上,吊着脖子的床单还在晃悠。任大胆顾不得多想,冲上去解那绳索:“小姐,小姐,你咋想不开啊?”放倒在地上,体温还热,但没了呼吸。任大胆要哭:“小姐呀,你咋想不开呀?老爷回来我咋向他们交代?”
蹊跷事发生了,紫霄突然间睁开眼睛直直地望着他,欲说不能。手指向自己的肚子,任大胆这时吓得尿流在了裤里,他以为是诈尸,撇下她,倒头就逃。“回来啊!”一声哞叫,像鬼嚎。他头皮发炸,魂出了体人怔在那儿。他害怕她会跳起来追赶他。
“哇—”一声婴儿啼哭,任大胆灵醒过来。她生了?孩子哭声真切,大白天哪来的鬼?他折回来,—一个肉红的小生命降生,踢蹬。“是个男孩子。”任大胆咧嘴笑,对紫霄说。他抱起她的小孩,找一件她的衣服包裹着凑到她面前叫她看。紫霄的脸色不再那么苍白,有一丝的气息,露出一丝微笑,手指前方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封信,竹萧,还有一块玉。
任大胆问:“给他的?”
他感觉到她在点头,对孩子说:“你妈给你的,多好!”孩子似乎是听明白了咧嘴笑,任大胆说:“小姐,你看,他笑了。”
她已经没了气息。他这才想明白小姐是遇到为难事了,想不开才上吊,连孩子也不想要了,偏在咽气的时候孩子要生,憋了最后的一口气等他来。
这也是有缘分。任大胆想这楼是不能再住了,老死人,得敢紧收拾了搬回去。信是写给一个人的,任大胆不识字,收拾了小姐的遗物装进小皮箱,抱起孩子回家。
任大胆给孩子取名为:任洪祥。
时光荏苒,城市在发生着变化。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外在表象就是:城区在扩张,一座座的高楼耸起,以钢筋水泥混凝土建筑物吞噬着周边村庄。当初那个小县城也成为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一座新兴城市,—日照。河山村被城市吞并,成了新城市中的一区,它也在扩张变化,大有衔接鬼楼之趋势。约有二百米的待开发耕地隔开了小村与鬼楼的亲近。
鬼楼还是孤独地伫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