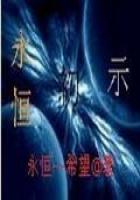(一)
入夜已深,阿婆见余念迟迟不归,已然十分焦急,直到余念进门才放下心来。余念对一路上的际遇绝口不提。只将包着银子的手帕交给阿婆。阿婆小心翼翼从枕下取出一个钱袋,说道:“这是这几年攒下来的,足有八两,待小念出嫁,好为小念置办嫁妆。”
余念得知自己是异类,婚姻嫁娶已不做多想。但阿婆善待令她动容,抱住阿婆道:“小念不嫁,阿婆,我只是个弃婴,你却待我如此好。”
阿婆将她拉至桌子边:“傻孩子,饿坏了吧。快坐,我给你留了饭。”
余念喝着粥,边问道:“阿婆,你当年捡到我时是怎么样的场景?”
阿婆道:“那年隆冬,奇冷无比,那时你叔叔婶婶还住这里。一日清晨,我起来烧火做饭,忽听井边传来婴儿啼哭,我跑过去,见你小脸都冻成紫色,便抱了你回来。襁褓中,你身上只一只绿色坠子,我们都不识字,找了教书先生才知坠子上写的是‘心有余思,念念不忘’,我便给你取名余念,不知你生身父母姓名,也只好让你先跟着我姓沈,等将来打听到父母下落,就把姓改回去吧。”
余念闻言:“那叔叔婶婶为何搬走?是因为我的缘故么?”
阿婆道:“那些年,家里没有余粮,生活吃紧,你叔叔婶婶想将你送走,见我执意不肯,他们便在村里另起了宅院。每次回来,不是跟我要粮食,就是要银子……唉……”
余念见勾起婆婆伤心事,不再言语,想到自己身世还是毫无头绪,当即不再多问。
(二)
不夜城,一处阴暗宅院内,傲因赤裸上身,小心处理左臂内侧的伤口。幽暗光线中房间墙上挂着一副画像,画中少女五官精致,笑容甜美,却身着男装。
看着画中人一脸明媚,傲因愈发恼怒,努力回想……她怀里的小兽当时叫她……小念……
“小念……”傲因喃喃自语,伸出利爪,画像瞬间粉碎。
午夜的长安街,敛了日间繁华,四处漆黑,安静冷清,傲因缓缓走在空旷的街道,腹中渐渐升腾出对食物的浓烈渴望。正自踌躇间,忽听远处传来更夫敲竹梆子的声音。傲因面色一喜,循声而去。
更夫是个瘦小的中年男子,乏了便坐在街边檐下打起盹来。此时傲因靠近,更夫察觉,迷蒙中抬眼望去,只见傲因伸了长舌利爪向自己扑来,更夫大惊失色,口中失声大叫:“妖怪啊!!”
随即跌落在地,连滚带爬,躲过傲因攻击,挣扎起身,开始在无止境的夜色中拼命狂奔。
不敢回头,跑了半晌,更夫浑身湿透,已然精疲力竭。此时已跑至自家门口,更夫进院插上大门,跑进屋内插上房门,又用桌子将门堵上,这才长舒了口气。
却听见身后传来“呵呵呵呵”地笑声,更夫冷汗直下,稍安的心脏又开始狂跳。缓缓扭过头,只扭到一半,只觉头顶剧痛,似要炸裂般,有股大力挤压将脑袋分成两瓣,更夫嘶声惨叫,杀猪一般,已不辨人声。悚然的惨叫也只两声便再无声息。
他的脑壳已被傲因撕开,连着皮肉的发丝间,清晰露出脑浆,片刻间便被傲因连同体内血液吸食干净。更夫的身体迅速干瘪了下去。
傲因心满意足的舔着嘴,丢掉手上只剩皮和骨的尸体。重新走在长安街道。
只见街头一个身穿白衣的身影,走出城门,一路向南,口中一直反复念叨:“小念……小念……”
(三)
春寒料峭,阿婆偶染风寒,房间不时传出几声轻咳,余念抓了药,轻执小扇,于柴房小火煎熬。
入夜,家家户户房门紧闭,万物俱静。此时乡间小路上缓缓走来一个白衣男子,不断耸动鼻翼,喃喃道:“好香,好香……”循着香气一路行至小院外。
余念端了药碗,从柴房出来,扭脸便看见满面笑容的傲因:“小念,原来你在这里,我找你找的好苦。”
余念一脸惶恐,下意识后退:“你要怎样?”
傲因已伸出利爪和舌头:“你好香,我要吃了你。”
余念一个猝不及防,被傲因的利爪掐住了脖子,便觉呼吸困难,双手一松,药碗落地“啪”一声脆响,瞬间四分五裂。
阿婆听到声响,唤道:“小念?”不等回应披了衣服出来,看到眼前一幕大惊失色:“放开……放开小念……”抄起门边扫帚向傲因打去,一下正中面门,傲因恼怒,另一只利爪掐住阿婆脖子,将她提起,又用力甩出去,阿婆脑袋撞在墙上,血溅当场。
余念大叫:“阿婆!”发出的声音却是:“啊~啊~”眼睛瞟向灶台,熬药时将火折子放在那里……
忽想起夜寒给她的铃铛,一直坠在腰上,摸索着一把拔掉木塞,那铃铛是空心,却听“叮铃”脆响,幽远空灵。
傲因听到铃声,手上力道竟松了不少:“这声音……有些耳熟……”片刻,望向余念腰间,疑惑道:“寒大人的‘幻音’因何会在你身上?”
只听身后一个极清冷的声音:“因为,那是我给她的。”
听见夜寒声音,傲因顿时呆住,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慌由心底蔓延开来,气势一泄,松开了余念。不敢抬头,转身对着夜寒躬身道:“寒大人~”
夜寒不做声,只冷眼看着跌落在地的余念,只见她大吸几口气,便立即爬起跑向阿婆,阿婆年事已高,被傲因一撞头骨裂开,脑后开了个洞,鲜血泊泊外涌。
余念忍着泪托起阿婆的头,阿婆气若游丝,双眼空洞,眼神涣散,已是弥留之际。余念唤道:“阿婆,阿婆……”只觉托着阿婆的手,指尖粘稠,轻轻抽出,见自己手掌袖口都已被鲜血染红,瞬间再收不住眼泪,视线模糊:“阿婆,阿婆你怎么样?”
阿婆双唇微动,却发不出声音。
余念抬眼望向夜寒,任凭泪水淌了一脸,哀求道:“救救我阿婆,求你,我求求你,救救她,不管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承担……求你,求求你……”
夜寒望向眼前的泪人,反复呢喃哀求,像只无助的小兽,单薄脆弱。依旧不做声,却还是上前搭住了阿婆的脉搏,双眉轻皱,又查看她后脑伤口,终于对着余念缓缓摇了摇头。
前所未有的不安演变成巨大的惶恐笼罩了她,余念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一时间,悲伤汹涌而至,又化作眼泪肆意泛滥。她的手开始发抖,模糊视线中,慌乱捂住阿婆后脑,想阻止外涌的血液,却是徒劳,只听她从喉管挤出的声音,发出悲鸣:“不要……不要……阿婆不要离开我……”
夜寒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倒出一颗药丸,给阿婆服下,对余念道:“这颗药可缓解她的痛楚,你跟她好好道个别吧。”
此时,阿婆涣散的目光聚在余念脸上,慈爱如初:“小念,阿婆要先走一步了。”
余念忍着心痛道:“阿婆,你不要说话,我去找郎中来救你。”
阿婆拉住她的手,断断续续道:“小念,阿婆岁数大了……迟早要有这么一天,你听我……说,我枕头下面有些银子和这房子的地契,你一定要收好……万不可落入你叔叔婶婶之手……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余念眼泪始终在涌,看不清阿婆的脸,她慌乱摇着头,声音有些嘶哑:“不要……不要……我只要阿婆,阿婆不要离开我……”
阿婆微笑,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望向余念的眼光无限怜爱与不舍:“小……小念……我……从未……后悔……当初留下你……”说完双眼轻阖,撒手人寰。
余念绷在心里的那根弦瞬间断裂,她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终于离她而去,只觉整颗心痛到抽离,嘶声喊道:“阿婆……”
再也承担不了,她死死抱着阿婆的尸体,在院子里……悸哭……
(四)
夜寒起身,到傲因面前,负手而立,寒声道:“傲因,你入我不夜城,可知我城中规矩?”
傲因抖如筛糠:“城主大人乃妖界神医,且法力高强,所创不夜城,收留过往流离妖怪,所定城规,凡以人类精气血液为食者,需适可而止,不得枉杀性命。”
夜寒俊脸不怒自威:“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了断?”
傲因双腿再无力支撑身体,跪地道:“我一时失了手,才触犯城规,请寒大人……”
夜寒眼中寒意更深:“哦?那长安城的更夫,你作何解释?”
傲因闻言脸色灰败,瘫坐在地:“寒大人,我一时糊涂……”
却被夜寒打断:“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了断?”
傲因半晌才道:“不敢劳烦寒大人,我自己动手。”说完伸出利爪,这双爪曾撕开过无数人的脑颅,帮助他吸食无数甜美脑浆与鲜血。而今却要用它了结自己,傲因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与暴戾。
伸出利爪击向夜寒面门,他这一下出其不意,动作极快,夜寒却是更快,早有防备般,轻巧避过,另一只利爪又到面门,接连快速攻击,直指要害,不给夜寒喘息机会。夜寒自如闪躲,身法行云流水,潇洒俊逸,傲因疯狂攻击竟连对方发梢都没沾上。手臂指尖同时暴长,左右向夜寒夹击,夜寒顿住,口中念念,指尖划出几道白刃,有如削泥一般,将傲因手臂利爪削为几段,残肢散落一地,傲因伤口鲜血狂喷,跌倒在地。
夜寒缓步踱到他面前,傲因面色极其惊恐,不顾疼痛,拼命向后退缩:“寒大人,我一时糊涂,寒大人饶我性命……”
夜寒自怀中取出一朱红瓷瓶,倒出一赤色药丸,轻声道:“傲因者,以人类脑浆亦或血液为食,生性嗜杀,刀剑伤之,不日便可自愈,若要绝以后患,当用火攻。这颗火珠,我便赏你。”
傲因惊恐中透出绝望,口中喃喃:“不……不……”
夜寒不由分说,将火珠弹进傲因口中。顷刻,便如同引燃的稻草,由体内起火,傲因痛苦嘶喊,原地翻滚,渐渐化为灰烬,不留一丝痕迹。
余念对眼前一切视若无睹,依旧抱着阿婆尸体流泪,在暗夜里犹如一朵苍白的小花。
夜寒不擅劝慰,在她身旁静立许久,才道:“逝者已矣还请节哀。若有一日,你在人界无处立足,可来不夜城寻我。”
余念自顾流泪,待她抬起头时,已不见夜寒踪影……
(五)
沈婆婆离世的消息,在小村里不胫而走,她那儿子儿媳便在脸上捂了帕子,一路嚎啕至余念的小院。
早有邻居帮余念敛了婆婆尸身,设了灵堂。两人跪在灵前哭丧,嘴里嘶喊:“我地那个老母亲……我还没尽孝……怎么说没就没了……”两人干嚎半晌,只闻其声,不见落泪。
周围邻居劝慰:“人死不能复生,别哭坏了身体。”两人才渐渐止了哭声。
入夜,夫妻二人与余念一同守灵。叔叔问道:“大侄女,我母亲是怎么没的?听说是招惹了妖怪?”
余念闻言泪眼婆娑,只是不语。
叔叔又问:“那母亲临终可有遗言?”
余念想到银子与地契,轻轻摇了摇头。
“那这房子的地契……啊哟……”叔叔话到一半,便觉耳朵剧痛,被婶婶揪起,将他拉至院外小声道:“你个蠢货,此刻跟她要哪门子地契?”
叔叔委屈道:“不是你说要地契么?”
婶婶道:“你这般要,那丫头铁定不给,反倒让她有了防备。”
叔叔问:“那以你之见呢?”
婶婶冷笑:“明的不行来暗的,我自有安排,你切莫鲁莽。”
余念自小便能暗夜中视物,百米内的声响亦听得清楚。二人谈话轻细入耳,眼睛望向阿婆卧房,心知叔叔婶婶只为阿婆枕下之物,不由悄悄叹口气,叹在心底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