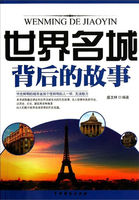早晨的雾霭将整个村子都拥抱在怀,紧紧的,让人几乎透不过气来,睁不开眼来。风这个时候也为这怀抱让了步,不再来打扰。唯有寒气还像往常一样,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你,以刀刻地方式。
碗里的热气不断地蒸腾起来,给张松的眉间眼角带来了一丝温温的湿意,入鼻后却是一股苦苦的味道。张松手捧着碗里的药,不仅嘴里是苦的,就连眼眉都是苦的。犹豫再三,张松屏气凝息,闭着眼张大嘴巴一口气就将药灌了下去,然后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张松生病了,昨日一天的劳累与担惊受怕,极大地损耗了他的精气神,给了病魔以可乘之机,出汗后没有及时更衣,更是病魔的引路人。
昨天晚上张松是睡在了自己的床上,想来是母亲将他抱上了床,只是不知道母亲是几时回来,将他抱上床的,但想来应该是很晚,他睡得极熟的时候,要不然以他的警醒,肯定是能够觉察得到的。
今天早晨母亲叫醒后,张松觉得自己的眼皮像是被胶水粘住了,怎么也睁不开,头颅似有千斤重,怎么都抬不起来。张松母亲摸了摸张松的头后,让他继续卧床休息,就出了山洞。张松点了点头,就倒下又睡着了。
再次被母亲叫醒时,那股药的苦味就一直围绕着张松,母亲也没有多加劝说,只是将药给了张松,让他趁热喝了。“良药苦口利于病”这道理张松母亲已经教过了张松,张松也是懂的,所以不用母亲多说。
喝完药后,张松默默地坐在洞口。洞外雾气很浓,就是山洞门口的那棵大树也只是显示了一点轮廓,连树叶也看不清。厨房里母亲只见一点依稀的影子,那影子正在忙前忙后地准备着朝食。
朝食过后,母亲就走了,张松还是感到特别的疲累,就上床睡了。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晚上,起床后在刺骨的寒冷的围绕下,张松全身打起了哆嗦。
也许是同样刺骨的寒冷让张松想起了前天晚上的梦,梦里最让张松印象深刻的,除了那刺骨的寒冷与全身的伤痛外,就是那声震颤灵魂的枪响了。
比那声震颤灵魂的枪响更让张松震惊的是,前天他还觉得出生至今绝没有听过这枪响,而现在他就有些恍惚,觉得这很可能就是真真切切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这一变化让张松心里充满了惊疑。
“小松,来吃饭了。”母亲将饭食端入了山洞。
“母亲,梦里的东西是不是一定都是真实的呢?”张松往嘴里扒了一点麦饭,下定决心向母亲求教。
“梦啊,一般来说都是真实的,人们不是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母亲快速地往嘴里扒着麦饭,一边得空含糊地跟张松说道。
“母亲,前天晚上我也做了个梦。”在心里思量再三,张松决定把梦里的事情告诉母亲,母亲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他很想从母亲这里寻求帮助。
母亲听完张松的话后,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梦境中的一切事物,如工厂、手枪、铁制椅子、电灯、清晰无比的镜子等,她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见过了。她以为这是张松在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做,闲着胡思乱想出来的。
于是母亲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张松的头,以劝慰的语气对张松说:“松儿,你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了对身体不好。快点吃饭吧。”
张松愣了一下,母亲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让自己快点吃饭?但很快,张松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母亲不相信自己真的做了这么个梦。
张松有点急了,他又把自己做的那个梦详细地向母亲描述了一遍,说:“我是真的做了这么个梦,要不然我哪里能像你描述得这么清楚啊。我现在想请你告诉我,这梦里的一切是不是真的?”
母亲听完,略加思索,抬起头准备跟张松说些什么。
“砰”,随着一声巨响,家门被人猛地一脚踢开,一股气流掀起地上的灰尘扑面而来,碗里的干净的饭食上很快就覆盖了一层灰尘。
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嚣张地闯进了张松母子俩住的山洞,为首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虬须大汉,紧跟着的是王狼、小六子,还有王玄、王宝、韩龙与其他一些张松不认识的人。
浓眉大眼的虬须大汉是村里的大村老,他与王狼还有另一个没出现的张让是村里的三个村老。
“小杂种,昨晚是不是你放走了小五子,我昨晚只看见你从那里经过了,一定是你放走了他。他妈的,晚上走路像个鬼一样,想吓死人哪。”小六子一见张松就有几分恼羞成怒的喝问道,似乎对昨晚给张松让路有点耿耿于怀。另一边,几个人举着火把朝山洞深处走去,满山洞的搜寻。
张松心里一惊,原来小五子让自己捡石头是要逃跑,并不是要防什么野兽。正当张松在想找个理由辩解时,母亲已经开了口,“不可能的,我儿昨天生病了,那有力气去放小五子。再说,小五子与我儿又没有什么交往,我儿怎么可能想到去放了他。最重要的是,我昨晚回来的时候,小五子还在那里。”
“现在是问你生的那个小杂种,而不是问你,你多什么嘴?怎么,昨晚服侍得你不够舒服?”王狼的语气一开始还是阴测测的,后面又变得轻佻起来。
一听这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哄笑起来,其中以王玄、王宝、韩龙笑得尤为刺耳。
听了这话,母亲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全身发抖,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张松两眼圆睁,怒气迸发,大喊一声“你这个狗杂种,欺负我母亲,我打死你!”
母亲大惊失色,只来得及喊一声“不要”,就见张松朝王狼冲了过去。
其他人也没有想到张松居然敢冲过来打王狼,来不及反应,王狼一时也没有防备,就这样,张松冲到王狼面前,两只拳头狠狠地打在王狼胸口的护甲上。王狼胸口传来一阵疼痛,他后退了几步。
就在张松要打第二拳时,小六子抽出长刀迅速地架在了张松的脖子上,目光冷峻,两眼像眼镜蛇一样盯住张松,只要张松敢出拳,他将毫不犹豫地将张松的头颅砍下来。
“不要啊,松儿!”母亲再次喊道。
张松脖子上已经有鲜血流出,他身子一僵,便停住了手。
这时,王狼已经反应过来了,他飞起一脚,朝张松踢了过去,这一脚正中右肩,张松倒飞出七八丈远。王狼还不想罢休,他一把夺过小六子的长刀,挥刀就要朝张松砍去。
这时,大村老制止了王狼,说道:“哎,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嘛。再说也要给四娘几分薄面啊,四娘可是知书识礼的人,不要在四娘面前打打杀杀的。”
王狼气恨恨地说:“好,看在大村老的面子上,今天就放过你一回。”
这时,前往山洞深处搜寻的几人出来了,对大村老说:“禀大村老,仔细搜过了,洞里没有人。”
“四娘,如果你见到了小五子,一定记得要向我们报告!如果是隐瞒不报,后果自负!好了,我们走吧。小五子这混蛋,跑了就跑了,还偏偏还要弄点事出来,不找到他,誓不为人。”说完,大村老也不管张松母子俩的反应,率领众人出了山洞。
四娘垂着泪将张松扶了起来,解开了张松的衣服,察看伤势。王狼这一脚踢得真狠,只是幸好踢中的部位是肩部,要是在其他部位肯定要骨折,即使这样,张松肩部也是一大块乌青,并且肿了起来。昨天的伤也受牵连而又更加疼痛起来。
四娘年龄其实并不算大,只是这几年在村里过得很苦,眼角眉梢已有皱纹,鬓角已有几丝白发,坚毅的脸庞含着化不开的忧愁。虽然常年的辛劳让四娘从外形上显得有点苍老,但从气质上来说,四娘跟村里所有人都不一样。
看着四娘垂泪的样子,张松心里一痛,轻声安慰道:“母亲,没事的,你不用担心,我没事。”
“松儿,你别动。母亲给你揉揉才好得快。”四娘已抹去了眼泪,同样轻声的说道,同时轻轻地为张松揉了起来。
“吱呀”山洞门口传来了关门声,一道人影偷偷地溜了进来,关上了洞门。四娘惊得跳起来,颤着声音问道:“谁?”
“是我。”入耳的是一个熟悉的低沉的声音,声音故意压低了。
来人走到跟前,果然是老铁匠,张松高兴地叫了声“铁匠叔。”
老铁匠同样高兴地用手拍了拍张松,说道:“我都看见了,你是好样的!”张松偏了偏脑袋,老铁匠的衣袖上传来一股熟悉的怪味。
“昨天晚上你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你知道有多危险吗?后来你又到哪去了?”四娘关切地低声问道。
“我不放心你,想着照顾你一点。那群畜牲,这段时间越发地不像样了。”老铁匠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脸色阴沉,“总得让他们付出点代价才行。”
“大村老夫人去世了,他就少了许多约束,做事也少了许多顾忌。你我在这里势单力孤,没法跟他们斗,最重要的是松儿还小,先要保住平安才好。”四娘平静地说道。
老铁匠与四娘无语对视了一眼,叹了口气后,就略弯了弯腰,告辞而去。临别时又用手拍了拍张松的头,那股熟悉的怪味再次扑鼻而来。
老铁匠走后不久,张松与四娘也睡了。刚刚发生了那种事,张松已没有心情再去问四娘关于梦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