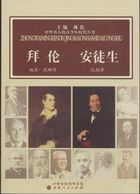宝蝉这么一承认,沈氏和陈子义都松了口气,但陈南乔的心却很是紧了一下。
这簪子明明是刚才他听父亲胡说什么在亭子里找到了个簪子,所以趁着沈氏不备,偷偷从她头上取下来的,他一个暗鬼护队的精英,投点东西对他来说,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了。
从一开始看到宝蝉那个样子,就知道宝蝉一定会替沈氏顶罪的,自己这么做,并不是要证明什么,只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沈氏的表情和反应。而刚才,沈氏那个紧张的样子,便完全可以看出,她昨晚定然是出了门,因为只有出了门才有丢失簪子的可能性,所以她才会紧张,那么这样说来凤兰应该是她杀的,那么既然杀了凤兰的人是她,就说明,沈氏,才真的是去年那场火的真正凶手!!
而宝蝉,应该只是一心护主罢了。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既然她是真凶,就应该看看沈氏手上有没有荧光粉罢?
荧光粉,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不管谁是真凶,一开始就应该看看她们手上的荧光粉的啊?!
对了两位,不知可否将二位双手伸出来,我们需要查看一下二位的双手。”
”宝蝉冷笑一声,“看看我们手中有没有血吗?”
我们只是看一看。
此刻大家心中已经很清楚陈南乔想干什么了,但是因为昨天晚上宝蝉已经出去给沈氏买了硫磺,所以宝蝉和沈氏心中都没有多大的波澜。
“怎么了东家?”陈南乔一双鹰一样的眼睛,略带着微妙的嘲讽味道看了看沈氏,复又转头看了看宝蝉,道,“宝蝉?你们该不会不愿意罢?难不成,还要我爹把你们带去县衙么?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沈氏终于忍不住开口道,“不就是看个手么?两位爷虽然不说是为了什么,但是料想也该是正事了,你们放心,我是不会乱往外说的。”
言及此处蝉扑哧一笑,也开口道,“是啊,我也不会乱说的。”
陈子义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两个女人在说什么,于是便开口问道,“什么不会乱说?乱说什么?”
“我说陈大人,您虽然说是锦衣卫,还有腰牌为证,但是您说您此刻并不是在县衙,也不是在什么公共地方,也不告诉我,看手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您既然是不说,那么就是可能和公事案子有关,也可能不和案子有关,对罢?”沈氏冲着陈子义嫣然一笑,然后妩媚的白了他一眼,继续道,“那么如果有可能不和案子有关,而您们父子二人便是如此进入我的房间,还要看咱们主仆俩人的手……”
沈氏用很微妙的语气说着笑了笑,继续道,“二位爷,虽然说是男女授受不亲,可陈大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做出这样的要求,咱们主仆两人只是寻常的良家女子,胆小怕事,你说咱们哪敢拒绝呢?所以这若是传了出去,必定会是有人说二位爷的闲话儿的。”
陈子义父子一动不动的看着沈氏,心下都在想,这婆娘真是太厉害了。
而宝蝉站在一旁,觉得东家沈氏这话说的简直太有水平了,于是也笑着开口道,“大家伙儿或许会说,两位爷利用公职,进入女子……”
言及此处,宝蝉意味深长的笑了笑,不再说话了。
沈氏见宝蝉如此知道自己心事,心下里又觉得这次自己说的这些话,可一定会让陈子义和陈南乔尴尬不已的,即便是知道他们不会就因为她们这两句话就不看自己的手,但可以让他们难堪一下,沈氏心中也觉得开心。
毕竟,再怎么说,他们两个也是陈子澄的族亲,对于沈氏来说,他们都一样那么令人讨厌!!
然而沈氏万万没有想到,陈南乔竟突然十分严肃的走到沈氏宝蝉面前,开口道,“宝蝉姑娘,我且问你,你究竟可知道锦衣卫这个机构?”
宝蝉被陈南乔这突然而来的严肃弄的有点不明所以,再加上陈南乔此刻眼神凶狠,恰似可以射出毒箭一般,完全不似平日里那副纨绔子弟的模样,所以宝蝉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她拿不准这陈南乔想干什么,于是只能无辜而胆怯的摇了摇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知道?”陈南乔冷笑一声,嘲讽的昵了宝蝉一眼。
宝蝉觉得,此刻的陈南乔根本就不像他本人,她从来没见过在陈南乔的脸上出现过这样奇怪的、认真的、严肃的、难以言说的表情。
“既然你不知道,那就不要乱说话了,“锦衣卫直属当今圣上管,只听命于圣上,说的那些皇亲国戚咱们都可以直接抓人,更不必公开审讯!!你听明白了吗?!”
沈氏听到陈南乔这么说话,心下里的气势即刻是没有了,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反应,只是愣愣的看着陈南乔。
只间陈南乔表情十分严肃,眼神之中带着让人心害怕的光芒,他继续说道,“沈氏!宝蝉!我们并没有强行将你们带走审问,并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此次是在我大伯法事大典之前,我不想这期间发生什么事情耽误了大典,这是对先人不敬。所以才对你们一味忍让。可是你们两个妇人,非但不明事理,刚才还口出妄言,胡言乱语,什么闯入女宅看女子双手?你们这是在辱没朝廷命官!”
虽然陈南乔这突然之间的气势吓到了宝蝉,沈氏也有些害怕,但到底沈氏不是那么简单的女人,总不能几句话就被唬住了,“陈公子,您也消消气儿,咱们可没有辱没朝廷命官的意思,这个罪,奴家哪受得起,只是陈公子,我要是没记错儿,陈大人的确是锦衣卫,可是您……奴家似乎还没见过腰牌!
这臭婆娘还真是伶牙俐齿。
但她说的也很是在理的,当日里,爹偷偷用了杨嬷嬷的腰牌冒充锦衣卫,而他们暗鬼护队的腰牌为红色,和锦衣卫的黑色腰牌全然不同,这个时候的确是不能拿出来自己也冒充锦衣卫的。
正在思忖着该怎么回应的时候,“南乔不是锦衣卫。”
陈南乔心下当即一沉,想着爹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一向是包庇这沈氏的,该不会此刻也借着机会让自己别再插手管沈氏了罢?
而沈氏和宝蝉的脸上即刻就露出不屑而讥诮的表情看陈南乔。
然而未见,陈子义又开口道,“可我是!”
陈子义看了看儿子,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然后看着这沈氏和宝蝉两个女人,双手背后,缓缓踱步道,“刚才南乔已经说了,我作为锦衣卫,抓人不必申报,审讯不必公开,在此地审问你们两个,倒也不算什么大问题罢?而你们两个,居然胆大包天的在朝廷命官面前说我们的审讯是轻薄?这已经是辱没朝廷命官了,所以!”
话锋至此,陈子义即刻转变了一个十分严厉肃穆的态度,眼睛直直的看着沈氏道,“犯妇沈氏!”
沈氏顿时吓了一跳,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即刻低头,不敢说话。
见沈氏如此,陈子义又转头看了看宝蝉,吼道,“犯妇宝蝉!”
宝蝉更是吓得腿都软了,低着头,和沈氏一样不敢说话了。
“你们两个犯妇可曾知罪?!
此刻屋内的气氛十分凝重,窗外是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停歇的风雪,无声无息的雪和疯狂大作的风交缠在一起,形成一副独特而绚丽的窗外风景。
而陈子义的声音,就像是来自遥远的天际,那么肃穆有力,那么掷地有声。
沈氏和宝蝉当即下跪,连声道,“民女不敢,大人扰民……”
陈南乔在一旁看着心下里十分烦躁,其实不过就是看她们的手罢了,如果她们两个不是心虚,干嘛要说这么多?逼着我们翻脸。
正想着,便听到陈子义叫了自己一声,道,“陈南乔!”
“在。
“你去拿一截蜡烛来。
陈南乔摸了摸腰间,取出一支白色的蜡烛,道,“孩儿身上一直带着。”
“点燃。
说着,陈南乔便是点燃了蜡烛。
小小蜡烛在这苍白的白天里,看起来那么苍白无力,并不显得温暖,陈南乔举着蜡烛,心下道,刚才说那么多,还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这下要看出了荧光粉,看你们怎么狡辩!
你去看看她们两个犯妇的手掌手背,是否有银蓝色粉末。“注意,必须用东西挡住光芒,然后用蜡烛仔细奎照。”
爹。说着,陈南乔从茶案上拿起一个摆放格式茶盏的盘子,挡住白天的光亮,另一只手小心翼翼的将蜡烛对准沈氏的手。
当蜡烛的光芒缓缓的笼罩住沈氏的手掌时,陈南乔心底便是一沉。
没有!
是的,沈氏手掌干干净净,并没有什么银蓝色粉末。
怎么会这样?陈南乔心下大惊,然后回头看了看陈子义,但见陈子义和自己一样,脸上全是吃惊的神色。
难道真的不是沈氏?陈南乔在心中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