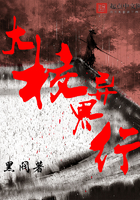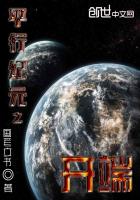夕阳西下,空中繁星渐显,山路两侧灯台中摇曳的火光同天上的点点星光遥遥相对,老神木下人头攒动,空气中弥漫着名为期待的躁动。
众人围绕着一个环形高台,高台的中心生长着一棵生死难断的树,树干之粗壮足足需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树冠上没有一片叶子,形似鬼爪。这就是桃源村的老神木,据传是一棵能通灵的树,除非重大事宜,否则村民们是不会靠近这棵树的,只是在山下的桃仙庙上香参拜,祈福求愿。老人都说这是一棵桃树,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棵树开花结果,但人们从不怀疑这棵树还活着,因为这棵树会流血!
高台的侧面镌刻着样式古朴、繁复的纹路,一些了解阵式的贤者认出那些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阵式。阵式是专属于贤者的语言,其本质是零子级的算法,是贤者与零子沟通的语言,也是贤者对零子运行的理解。尽管这些贤者自诩见多识广却没有一个能够辨析出这个阵式的实际用途。最不可思议的是,高台台面边沿镶嵌着的那一圈零石。零石是零子的结晶,是夏什最近才兴起的机械能源,这一圈零石发动并维持一个高级防御阵式数年之久也是绰绰有余,目前连凤笯的工事都不敢如此奢侈,在这样一个偏居一隅、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却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在场的贤者的态度,不得不说,确实算是见识不薄。
此时,高台上站了七八个孩子,意得站在最左边,是所有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最小的还不足月。意得仿佛处在一种梦游的状态之中,因为并没有人告诉过他择星仪式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还有不同的笔试题!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内侄男,一个外甥女,一个舅父,一个姑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表兄,一个表妹。你会说:“这家一共有十二人。”但事实上只有四人。请做出合理判断。意得默默地在题目下面写到:另外八个都诈尸了……
小明和弟弟步行到学校,弟弟需要四十分钟,小明需要三十分钟,如果弟弟比小明早五分钟离家,学校离家七公里,问小明能追上弟弟吗?那肯定追不上!因为小明还在上一个题里和小红放学呢,有小红了谁还要弟弟啊!
四名行人正常经过北方牧场时跌入废料池,一人获救三人死亡。据查,当地牧民为养草放牧,储存牛羊排泄物用于施肥,一家牧场往往挖有三四个废料池,深者达三四米,之前也发生过同类事故。问牧场管理人是否应对事故负责?……什么人看见地上那么大的坑就直直往里跳啊?!
……
这时,一个身材高挑、曲线曼妙的美丽女子走上高台,意得看见她如遭天雷灌顶,全身一阵酥麻,他从没见过这般美丽的女子,比容伯家的秀秀姐还好看。荣伯是村里唯一的大夫,村里人有个痛疼脑热都来找他,虽然荣伯不收诊费,但村里人无论有了什么,也无论贵贱,都会给他家带一份以表示感谢,所以秀秀姐从小就不用像村里其他孩子为了生计干粗重的农活,在意得的记忆里,秀秀姐总是捧着医书,阳光打在她的脸上,光影里她纤长的睫毛上下翻飞,像一只小蝴蝶飞进他心里使个劲的扑腾,呼扇呼扇的翅膀挠得他心里痒痒。小时候秀秀姐握着他的手教他写字,那少女细腻的皮肤让他觉得叫花子喝多了吹牛提到的锦缎也不过如此,所以在意得的心中一直坚定地认为,天上的仙女也不过就是比秀秀姐会飞而已。他一直没有告诉秀秀姐他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决定了将来要娶她,而此时他居然有些庆幸他没把他这点小心思告诉任何人,他忽然觉得叫花子也许是对的,离开桃源村也许没他想象中那么糟。意得的内心深处爆发出一种强劲而原始的动力!
意得目不转睛的盯着面前的女人,她肤白胜雪,唇似樱红,一双蓝眸好似内蕴璀璨星河,一袭白色长裙,素腰一束,盈盈不堪一握,裙侧可见她修长紧实的双腿,金色的长发柔顺的垂在腰系在火光的照耀下泛着金色的光芒,她身上没有任何一件配饰,却贵气逼人,年轻的面容遮掩不住举手投足间成熟女人才有的优雅,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感让人在她面前除了跪地臣服不做他想。然而台下的贤者在看到这位美女时却齐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小声地叫出了这位的名号:“盲女·月十三”。
听见台下有人称呼这位美人“盲女”,意得大吃一惊,因为女人的步伐轻快而坚定,单从他的行动上意得捕获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以证明她其实是个瞎子。女人没有理会围观群众的骚动,径直走到意得面前,抬头看向天空,意得随着她的目光也看向了天空。一轮满月挂在天空之中。意得知道,择星仪式马上要开始了。忽然,他觉得被人拍了一下后脑勺,他猛地低下头发现月十三美丽的面庞就在他面前足以让他感到面红耳赤的距离,而他的脸不知何时已被人捧在了手里,还没来得及不好意思,意得便听见女人轻声说:“头别乱动。”
她的声音不似少女那般如山涧清泉明亮清脆,而是比较低沉,带着强烈神圣、庄严的气息。意得下意识的看向她的眼睛,刹那间如坠星海。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好像与繁星融为了一体,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袭来。然而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意得就觉得自己落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随之而来的还有寒冷,他不知道自己是梦是醒,因为他觉得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背影。他站在一旁,眼睁睁的看着一条拇指粗细的白蛇钻入他的嘴中,经由食道,进入他的胃,化成了无数细小的白色长虫钻进他的血管游走于四肢百骸。他想吐,那条蛇却不断前进卡在他的喉咙深处,他甚至能感受到那条蛇的鳞片在他食道肌肉上的摩擦;他想咽,那条蛇却像变戏法的从帽子里抽出的旗子一样无穷无尽,阻止着他喉部肌肉的收缩;他惊异的发现自己连一根手指头都调动不起来,冷汗从每一个毛孔渗出;他默默祈祷这种酷刑赶紧结束,但似乎接受他祈祷的用户此时并不在服务区。一种寒意从他的身体内泛出,他快要冻僵了,越来越困……他突然感受到一丝温暖,好像被裹进了柔软的皮毛之中,这不是他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
有一年冬天特别的冷,很多人都病倒了,身子骨本就不好的锦娘自然没能逃脱,连荣伯都断药了。为了采药,意得一个人进了山,药是采到了,大雪也把山封了,到处白茫茫的一片。他不知道自己被困了多久,依稀记得,老巴南和叫花子找到他的时候他除了困之外他居然感觉到一丝温暖,老巴南背着他不停地叫他的名字跟他说话,叫他再困也不要睡,说锦娘还在家等他呢,桃花糕都做好了,就等他回家了……后来他才听老巴南说,他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脱衣服,真个人都凉透了!老巴南给他身上裹衣服的时候他还一个劲地挣扎,死命的喊“热”,要是再晚一会,可能就没救了!
想到这些,意得突然特别想哭,他还没有告诉老巴南他的胡子是他烧的,和虎子没关系;也没有告诉叫花子他往他的酒葫芦里撒尿的事;更没有告诉锦娘她最喜欢的盘子没有丢,是他不小心给打了,尸首就埋在他经常躺着晒太阳的石头旁......他还没娶媳妇,还有很多事没做,可是他没机会了,他实在太困了,眼皮越来越沉,意识也越来越涣散......突然,他眼前浮现出“盲女”的脸,还是那么美丽,却让他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感,就好像这并不是一张脸,而是以一张被用来当做面具的皮,她微微一笑,意得便堕入了彻底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