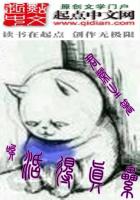昨日我并没有和叔带谈论下去,在他一声长叹后,我也想到了,太宰虢季是西虢的国君,太傅姬友是郑国的国君,太师尹吉甫是尹国的国君,只有太保张仲、太史伯阳父、大司马叔带才是无封之臣,其余众臣父王不能以心托付。
张仲今年七十多岁,让他来做傧相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伯阳父虽然五十余岁还算硬朗,但他是太史,每日的朝堂之事还需他来记录,跟我去申国亲迎那也不合适。所以到头来父王放心的也只有叔带一人而已。
去申的路途倒不必日夜兼程,第一日我们会在同关落脚。
同关是宗周北面的门户,也被称为同官,由于在铜水之川,后人改此地名为铜川。
同关不大,却是北面横岭群山入周原的必经之处,为了防御犬戎的进攻,此地驻扎着常武一军万余人的兵力。此地的守将名叫张宜,小司马位中大夫爵,今年三十余岁,是太保张仲的次子。张仲有象宜二子,长子张象虽是文臣但却贵为大司寇,掌宗周刑狱。
亲迎人马于酉时天黑后到了同关,但此时的同关却是灯火通明。
张宜早就得了父王和上司叔带的命令在此迎接,他命了三个师近七千余人军士手持火炬夹道立于两侧,自己则领着两个副将站在道上静静等候。
见到我和叔带纷纷先后下车朝他走来,张宜及其副将快步走到我面前单膝拜倒:“末将率同关守军恭迎殿下、恭迎大司马。”
“吾等常武军士恭迎殿下,恭迎大司马。”持火炬的军士也一同单膝跪地。
“张将军及两位将军快快请起,张将军如此兴师动众,真是让孤不知所措啊。”我笑着扶起张宜,继续说道:“孤这是亲迎仪仗,又不是去打仗,当不得千军之迎啊。张将军还是让众将士们早些回去歇息吧。”
张宜起身对我笑道:“殿下有所不知,在征国人未婚者不能娶妻,好多人还指望着摘了那匹夫的头衔呢!这军士们一听说殿下亲迎队伍路过,争着抢着要过来迎接沾沾喜气,若不是还有守御之责,那驻扎在此的常武一军可就全来啦。”
匹夫匹妇是国人中对未婚男女的一种贬称,张宜倒不是在羞辱自己的部下,军旅之人心直口快而已。
“哈哈哈哈!”张宜倒是把众人都逗乐了,连我也无奈地边笑边摇头。
叔带在旁笑骂道:“张宜,你小子也是饱汉不知饿汉子饥,还敢开殿下的玩笑?还不快迎殿下进去,想让殿下在这道上喝风不成?”
张宜“哈哈”一笑,连忙把我等迎近了关内。
这一夜倒是平常,亲迎虽在婚娶六礼之末,但为了表示对女方的敬重,我也是不能饮酒的。张宜是同关守将,也不能纵酒,所以我安稳地在他营帐休息了一夜,第二日便早早离开了。
再往北跨过横岭,就是申国都城雒川所在,中间也没有关隘可供我休息。这段路我们行了三日,这三日每日都有快马往申国报信,以便申侯能够及时迎接。
三日后,车内。
我整理了一下玄服,叔带检查着冰函里的奠雁。
“赵大夫,还有两个时辰才能到雒川,想必申侯迎接的使臣也快到了。”我停了整理衣裳的手对叔带说道。
叔带也合上冰函,对我说道:“殿下此时心绪如何?”
“安然。”我说了两个字。
“如此便好,微臣也就放心了。其实到那申国也无多礼仪,殿下只管把夫人哄上车就是了。”叔带笑着说道。
“呵呵,赵大夫到时可不要看孤的笑话才是。”我也笑着说道。
“微臣哪敢看殿下的笑话。不过殿下这几日只谈了这横岭山水如何峻奇,却没说出那日心中疑惑,倒是让微臣讶异许多。”叔带转了话锋。
我对叔带说道:“也许是孤近两日看了那山高水远之景,心中开阔了许多。孤想着太傅毕竟是姬氏族人,私心有之,公心亦有之,公心还是大于私心的。不知赵大夫以为然否?”
“殿下所言极是,郑国、晋国、燕国等诸侯国自是和宗周同气连枝。不过,“叔带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只是人心似水如浪,这一浪是公心高于私心,那下一浪或许便是私心压过公心了。”
叔带说话总是喜欢藏掖,虽是为臣之道,倒也令我头痛。
“赵大夫还是明说吧,莫要再口含玄机而隐忍待发了。”我苦笑着对他说道。、
“呵呵,愿知者才知之。既然殿下愿知,微臣便明说好了,”叔带顿了顿继续说道:“太傅姬友乃我宗周社稷之栋梁,自是无私于宗周。但他有一子名为掘突,殿下可知否?”
“掘突啊,孤当然认识。他长孤两岁,幼时还在一起玩耍过,后来太傅受封郑国他便去了封地,这些年倒是少了来往。赵大夫既然提到他,可是他那里有什么新的消息不成?”我喝了一口茶,漫不经心地说道。
“殿下既然和掘突幼时相熟,可知其为人?”叔带问道。
“幼时怎能知老?他幼时倒是喜欢与我比拼饭量。”我笑着说道。
不过叔带可没笑,而是认真说道:“观其幼或可知其老。这掘突幼时无君臣之分,与殿下玩耍也无需礼让,如今他久在封国,心中对殿下之忆仍是幼时之况,必难有敬畏之心。他日殿下即位,掘突将如何自处?”
“哦?日后他还能携郑国叛出宗周不成?”我一脸不信地反问道。
“这倒是不会。不过掘突如今颇受郑国官员拥戴,太傅不在郑国时事务也交其打理。这两年郑国的国力增长了许多,其中大部分功劳都是这掘突立下的。”叔带解释道。
“此是好事,那又如何?”我又问道。
“虽是好事,也只是郑国一家的好事。现今郑国国人心中只有郑却没有宗周,这便是宗周的坏事了。”叔带脸色有些失落地回道。
我深深地看了叔带一眼,缓缓说道:“赵大夫其实是想说,如今各诸侯国的国人心中也只有本国无宗周吧。”
“呵呵。”叔带脸色有些不自然。
我不作任何表情地看着叔带慢慢说道:“这一点孤也是明白,不过此刻还未到最坏的时候。那些诸侯国君私心虽重但仍不敢过于表现出来,那说明宗周的礼法还能束缚他们。赵大夫警示孤的这番话,孤记住了,连同日前的那些话,孤也记住了。但孤也另有一言想问赵大夫。”
“殿下请问。”叔带说道。
“赵大夫是不是也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裂地封国呢?”我淡淡一问。
“微臣不敢。”叔带眼神一惊连忙跪着说道。
我摆了摆手对他说道:“孤此问并不是在责怪赵大夫。而是念在赵大夫对父王对宗周如此忠心的份上,孤日后会想办法给你一个封国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自己了。”
“微臣惶恐!”叔带仍是跪地不起颤声说道。
我看他不信,笑着过去把他扶起来,说道:“孤的傧相大人快起来吧,都听见申国人的马蹄声了!”
叔带见我并没责怪,又听见远处的人喊马嘶之声,也是微微一笑起身,又把发冠扶正了些。
“申侯长子姜献,奉父侯命前来迎接殿下!”一个大喊声从远方人马中传来。
我命人停了车,等姜献一行人到了仪仗前面才缓缓从车内出来。
“姜献参见殿下!”姜献下马走到我身边拜道。
“姜世子请起,有劳姜世子前方引路了!”我等姜献回了礼便又上了车。
约莫一个时辰后,我和我的亲迎队伍终于赶在天黑前到了雒川城下。
此时的雒川城很是安静,城门口也只有寥寥百余人。这并非申侯姜胡的不重视,只是礼的一部分,所以说这昏礼对于嫁女一方并非吉事。
我在叔带的搀扶下下了车,奠雁在叔带的手中执着。
刚下车我便听到了申国夫人和其他女眷痛哭的声音,定睛望去被她们包围在中间的申姜也是哭得泣不成声。
待叔带把贽礼交给申侯,申侯也只是嘱托了几句便摆手让姜诚送我和申姜回返了。
不论我之前对申侯和申国怎么看,自今起也便是一家人了。想到此处我不禁看向申姜,她今日之妆容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从此她便是我的妻了!”心里如此想着的我慢慢朝她走去。其他女眷见我走来纷纷让出了道路,申姜也抬起头看向我。四目相对时,她那略有期许又羞涩的眼神让我心中一颤!
我上前牵起她的衣袖把她带到申侯与申国夫人面前双双跪下稽首,然后便又在众女眷的哭声中把申姜扶往专门为她准备的墨车。
我把墨车上的引手递到申姜的手中助她上车,待申姜进入车内,我坐到车前拿起缰绳赶着墨车在原地转了三圈。这一个古老的礼节,既是夫家对妇家的歉然与谢意,同时也表示嫁妇对亲族的不舍。
之后我把缰绳交给车夫,回到前面我的车上,在傧相叔带的命令声中,仪仗开始回返。
没有什么分别之语,也没有夸张的哭天抢地。
亲迎之礼便在这么一个安静的黄昏中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