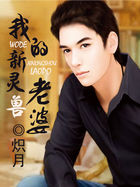七夫人脸色并不好看,鸳鸯又受她冷眼一扫,吓得一个冷颤,嘴里也不太利索:“奴婢鸳鸯见过夫人,见过五夫人。”
七夫人点了点头,五夫人则双眼一寒,陡然凌厉的瞧着鸳鸯喝道:“你就是鸳鸯?就是你这个贱婢唆使十四欺负我家良儿的?”
鸳鸯还没说话,七夫人就不满的道:“五姐这话好没道理?你家小十是个什么人,我家十四又是个什么人。他俩年纪可差了三四岁呢,指不定谁欺负着谁来。”
这话听得五夫人火冒三丈,她护短是素来出名的,平日里在几个如夫人中谁也怕她三分。今日却没曾想会受到这个平日里她最瞧不起的七夫人呛白,立时叫道:“我家小十可还在床上躺着生死不知,你说谁欺负谁来?”
七夫人听了不以为然:“我家十四不也还躺在床上生死不知么?”
五夫人听了咬牙切齿道:“谁晓得是不是见我来了吓得在床上装死?巧儿,你去瞧瞧去。”
她也是带了仆婢来的,巧儿便是她从娘家带来的贴身丫头。
巧儿二十来岁,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子,个子比五夫人略矮一些。听了自家主子的话为难的看了七夫人一眼,终究还是马上做出了抉择。大步朝着秦从文躺着的床头而去,用手去探秦从文的额头和脉搏。
鸳鸯见自家七夫人不拦着巧儿,她只好站在一旁局促的不知该如何是好。眼瞧着巧儿用手在摸自家少爷,动作虽然轻柔但哪里有下人随意去摸主子的道理?
五夫人却不耐烦巧儿的动作太温柔,她大步上前推开了巧儿道:“似你这般如何能探得人的虚实?”
挽起右手的袖子就去掐秦从文的手腕,料想秦从文如果是装昏一定会吃痛的尖叫。她出手可不留情,只一下秦从文的手腕上就起了青紫,瞧得鸳鸯一阵心惊肉跳。
旁边七夫人也觉得五夫人未免太不将她放在眼里了,脸色不愉高声道:“老五,你这是做什么?欺负一个病包儿么?你来我这儿到底想怎么着,直接拿出个章法来吧。”
五夫人见掐秦从文不动,只好收了手。一双眼睛望着鸳鸯,又狠狠的瞪了一眼床上的秦从文,而后跟七夫人道:“你须应我三件事,否则咱们就去王后那儿走上一遭。”
一说去王后那儿,七夫人心里就有些怯了。他可是听七夫人说过,秦从良就算是醒了以后也不能再练武了。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可以目不识丁但一定得有武艺傍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哪怕是王爷府的公子,一辈子也只能活在痛苦之中。
正因为知道后果严重,所以她才不肯替秦从文认罪。她素来喜欢以己之心度人,觉得五夫人是必定要敲诈她一笔的,所以便打算赖账。
果然,五夫人道:“第一,这个贱婢挑唆主子弑兄,其罪当诛,不杀她不足以平我心头怨愤。”
五夫人抬手一指鸳鸯,说出的话和眼神中饱含的恶毒让鸳鸯脸色瞬间煞白。亏得她已倚住了墙,否则非得直接瘫倒。
鸳鸯用哀求的目光瞧着七夫人,只盼七夫人念着她待十四爷的好救她一回。但七夫人才不会管顾她的死活,听了五夫人的要求后不怒反喜,心里竟然侥幸的想着如果这样就能够平息五夫人的怒火,那便宜可赚大发了。一个婢子的死并不可惜,她并不放在心上。
“第二···”五夫人一指床上的秦从文,道:“我要他也自废武功,替我儿作伴。”
这话说出来,七夫人脸上就是一怒,只觉得五夫人实在没给她面子。但眼见五夫人眼神坚决的望着自己,七夫人犹豫了起来。
“五姐,孩子还太小了些,这样做未免太伤天和。不若,等十四醒来后我教他去给小十那孩子道个歉吧?”七夫人扯起嘴角笑着道。
“笑话,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老七,你当这是做你的生意,能讨价还价来的?”五夫人直接戳破了七夫人的心思,她语气坚决的道:“我儿秦从良天赋异禀,眼看着年后就要开灵进入定武境界了。我好容易去老祖宗那儿求得让良儿进祖庙开灵的机会,哪料到···总之,如果秦从文不自废经脉,我们便去找老祖宗评理。”
这一句话出,七夫人脸色勃然大变。相比较怕王后,她更惧老祖宗。老祖宗乃是老王后,是整个秦家一言九鼎的人物。当初她有幸嫁入秦家本就是高攀了太多太多,老王后不喜她的出身太过卑微本就对她横眉冷目,如果这事儿闹到老王后那里去,天知道老王后会如何待她?
“怎么能因为这点儿小事儿打扰老祖宗呢?那太罪过,太罪过了。”七夫人险些跳脚,强颜欢笑,果决的点了点头说:“好罢,这条件我也依了你了。”
五夫人满意的点了点头,而旁边鸳鸯险些没直接昏死过去。她万念俱灰,本还想着求七夫人的情救救她,此刻见七夫人连十四爷都放弃了,便知道自己在七夫人眼里更不算什么了。
“第三···”五夫人又道。
听她还有条件,七夫人眉头忍不住跳了跳,一股子怒火没来由的从心里生出。
她小门小户出身,又素来爱妆点打扮,所以进了王府后也让下人和娘家的人帮她做生意。平日里做的就是斤斤计较的事儿,没想到今儿给人如此斤斤计较了一回。强忍着怒意,七夫人闷声听五夫人又待如何。
却见五夫人将修长的第三根无名指竖起,说道:“我儿受伤太重,必定是需要药补的。你得给我五千金币,这事儿才能算了。”
她一句话出,却没想戳中了七夫人的痛处,就听七夫人失声尖叫道:“什么?五千金币?你这可是往我心窝子里剜肉呢,休想。”
五夫人听了怒道:“你连儿子都舍了出去,还惦记着五千金币么?你若不答应我,咱们去找老祖宗理论去。”
七夫人此刻听了五夫人的话再没了怯意,如同被挑衅的母鸡一般战意昂扬的用丝毫不低于五夫人的声音道:“理论就理论,我倒要瞧瞧,这天下间还有个讲道理的去处没有。”
说话时,两人起身出了屋子,让一众人面面相觑。就在所有人都要忘记鸳鸯时,七夫人忽然回头冲着鸳鸯道:“你这惹祸的贱婢,杵在这儿做什么?随我一起走,咱们这儿也只有你最了解武堂到底发生的什么事儿了。”
听了七夫人的话,鸳鸯回头望了一眼仍然在昏迷中的秦从文。流了些泪,终究只能失魂落魄的跟着去了。
而起初人满为患的小屋此刻瞬间变得冷冷清清,打起的帘子也没有人记得放下。寒风从屋外刮了进来,让整个屋子都冷飕飕的。
躺在床上的秦从文脸颊和身子越发的滚烫,他眉头紧蹙,在睡梦中似乎在沉思着什么又似乎在忍受着什么。干涸的嘴唇起了死皮,一如在沙漠中缺了好几日水的行者。
“水···”他如是说。
耳畔完全能够听得到姨娘和五夫人的争吵,甚至瞧见了鸳鸯的失魂落魄。但也仅此而已,他无法做出回应甚至连多想也不能,直到所有的人都走掉,整个屋子安静下来。
“水···”
秦从文只觉得脑浆在热水里沸煮一样的疼痛,思维混乱而又迷糊,嘴里嚷着要喝水。然而此刻谁理他来?外间的风雪倒是还刮着,但屋子里却清冷的可以。
他几乎以为自己要死了,迷迷糊糊的开始做起了梦魇。
梦里有他用寒冰掌击伤秦从良,也有死去的方远和方文方武。他们想要拿自己的性命,而自己却似乎无力阻止。入眼处时一片黑暗,这黑暗的所在没有他可以逃离的去路。
他终于被方远和方文方武抓住,这三个新死的野鬼冷笑着来撕他的肉。秦从文正疑惑为什么这死去的鬼里没有秦从良的存在?但不等他多想,他的头皮就被方远用冰锥子剥开,而方武则用拳头将他的头骨砸破。头颅里滚烫的脑浆给方远拿了出来放在手心里捧着,眼看着那不断跳动的脑浆要给他们分食。猛然,那漆黑的天空中一道流星划落。
不知何时,天空中多了许多星辰。星辰在漆黑的夜空中散发出点点微光,可以预见到它们所在之处必定离大地太远太远。那颗从天而坠的流星也必定离大地太远,但它却比其它的星辰更加明亮。
那是一颗已极快的速度划落的流星,拖起长长的光影,在星空中穿行。它所过之处众星纷纷躲避,而躲避不及的也给它强横的撞开。但它似乎也并非是无所不能,在无数次与其它星辰碰撞后终于化成了火花,只余下一个不再散光的陨石落下。
那陨石坠落的方向正好是秦从文所在之处,笔直的朝着秦从文和三鬼砸落而下。那陨石坠落的速度十分迅速,只是眨眼之间就出现在了秦从文和三鬼跟前。
三道凄厉的惨叫声音响起,就见捧着自己脑浆的方文当先痛苦的嘶鸣,而于方文争夺脑浆的方武和方远也紧随其后痛呼了起来。
‘轰’的一声,陨石重重的砸在了它们的身上,而后重重的坠入了地面。
三鬼瞬间被打的魂飞魄散,化作道道黑烟被陨石吸收。而秦从文的脑浆则也不见,但秦从文的一具完整肉身却又重新闪现出来。
三鬼不在了,秦从文却仍然活着。他毫发无损,似乎头皮和头骨从没被撕裂敲烂过。错非眼前的所谓陨石还在,秦从文一定怀疑三鬼到底来没来过。
所谓陨石,其实是个体型颇大如鼎的香炉。三足两耳,古朴沉重,秦从文发现无论如何使力也无法推动它分毫。
香炉材质似铁非铁,其内除了布满的粉尘外别无一物。炉身上无字画,也无铭纹,普通平常。但看似普通平常,却给了秦从文一种重若泰山之感。他走到极远处远远的望着这香炉,不敢靠近。
因他发现这香炉似在抖动,果不其然,当秦从文离它三丈开外后,这香炉猛然拔地而起一飞冲天而去再不见了踪影。这香炉一去,天地间的星辰也瞬间消隐不见,似乎先前秦从文所看到的一切都无非是幻象而已。
秦从文不知道的是,就在幻象陡生之前,王府内院的别庭院里一个正坐在炕上捧书茗茶的妇人抬起了头蹙了蹙眉。
茶杯里香气缭绕,这长的颇为靓丽的美妇却混不在意。只是皱着眉头喃喃道:“府上似乎多了什么赃物?不知是谁敢来王府如此作怪。”
她正要唤人去查,一个婢子忽然在外间轻声道:“王后,听涛院的五夫人和柳院儿的七夫人一起来了,她们正在茶厅求见您呢。”
美妇听了愣了愣,便道:“这两位倒是稀客的,她们来这儿做什么。倒不必让她们在茶厅里候着,直接将她们带我这儿来罢。”
因五夫人和七夫人贸然造访打岔,她索性将那‘赃物入府’的小事儿给抛到了脑后,忘的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