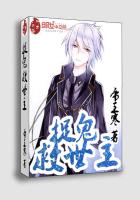余下的几人可没有鲁岩这般伸手,相互帮衬着才爬了过去。二院的围墙里很是荒芜,岩缝里偶尔钻出来几束野草,枯黄的叶面上偶尔漏出一丝丝绿。
白歌最后一个越过墙头,刚刚跳下来,就被眼前这座通体刷白的建筑吸引。这是一座仅有三层高的筒子楼,楼房正面是整整齐齐的墙面,每隔一段出现的窗户,也被老式钢条横竖隔离开,如若不是通体被刷为白色,恐怕说是监狱更加贴切一些。
“里边黑乎乎的,没有照明灯光吗?”白歌趴在一楼的窗子上,抹开玻璃上的灰尘。
“整个基地,就这个地方我最不熟悉,但理应是有照明设备的,基地为了方便检修、巡查,所有电路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只要找到总闸开关就可以了。”鲁岩绕到二院的正门口,一边说一边仔细寻找。
正门是一个六七十年代最常见的构造,一扇木门上镶嵌着两块不大的磨砂玻璃,斜拉下来的金属把手被一条厚厚的铁链牢牢拴在一起。
“怎么一个医院需要上这么多道锁?”林边圆很是好奇。
白歌心中略感不安,就连一向泰然自若的鲁岩,也焦躁的来回踱步。
鲁岩用匕首插进铁把手的连接处,用力撬开了一个缝隙。“我数三下,咱们一起撞过去!三、二、一!”
哐当一声,两扇门应声而开,铁锁联同把手被硬生生从木门上扯了下来,吊在半空中左右晃荡。声音回荡在山洞里,逐渐减小,直到消失。
“咳咳咳!好大的灰尘,也不知多久都没有人进来过。”林边圆用力太猛,差点闪倒在地,冷不丁吸了一口凉气,却被飞起的灰尘呛个正着。
苏心蹑手蹑脚的跟了进来,环视四周,除了岁月留下了痕迹之外,和十几年前并无两样。门口的大厅中,两边墙上写着那个年代专属的标语,正面是一组楼梯,直通楼上。“你们看墙上那些黑手印,好吓人!”
子琪忽闪一下躲在苏心身后,头都不敢露出来。
两侧的白墙上,清清楚楚的印着一排黑手印,有些五指清晰可辨,有些则被长长拖曳,留下四道指痕。
鲁岩下意识的猫着腰、侧着身子挪到墙边,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墙壁上的黑手印。“是干了的血渍!”
借助着洞外照进来的光,勉强能够看到大厅不远处几米范围内,再向里,就只有黑漆漆的走廊通道,和一扇扇紧紧关着的门。破败、荒凉总是能带给人最大的惊悚,也许人类从这个荒芜的空间里退出来,却有更适合它的东西住了进去。
白歌、鲁岩两人打开手电筒,顺着墙壁走进左边那条长廊。筒子楼很长,两边都是大门紧闭的房子,只留下中间一条黑漆漆密不透风的过道。原本白色的墙被一片片霉菌染的乌黑,刺鼻的霉味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往前走了一小段,一道金属栏杆将楼道隔离成两段,铁门虚掩着,好像专门留下来,等人进去一看究竟似的。
白歌用手电筒照在一块白色的长牌上:人体与精神意识实验科。“鲁岩,这里也是曾经红洞基地的一部分吗?看来是专门从事精神科研究的。”
“原来是这样!”鲁岩似乎明白了什么。“当年基地里就流传着很多关于二院的怪事,不论是这里的研究员还是守备士兵,都多多少少知道这里是个神秘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比那些顶级的科研工作室更加神秘。
阴暗潮湿的走廊顶部,湿气在天花板上凝结,一滴水‘嗒’的一声落在金属门上,安静的空间格外撩拨心弦。
鲁岩吹了一声口哨,示意站在大厅的四个人跟上来。
周围的环境虽说让白歌有些心虚,可当看见研究科室的牌子总能让他感到丝丝欣慰,至少说明这里的现象都在科学范畴之内。白歌轻轻推开铁门,锈迹斑斑的活页咯吱作响,刺耳的金属磨察声听的人浑身发麻。
噔噔噔~!走廊头顶的灯突然间打开,暖黄色的光线照亮了原本漆黑的空间。
“我说你们两个是瞎吗?墙上这么大的电闸箱,两只手电筒竟然都没有看到!”边圆大摇大摆的走过来,拍掉手上粘连的灰尘。
白歌侧目看着鲁岩,两人皱皱眉头,或许是紧张的心情让两人并没注意挂在墙上的电闸,尽管它的确突出来,很是显眼。
几人绕过那道铁门,走到第一个实验室门前,亮起的灯让整个实验室的氛围都不在那么恐怖骇人。白歌轻轻推开房门,打开墙壁上开关,一间老式手术室出现在眼前。
屋子的正中间放着一部手术台,左边是一张病床,右边堆放着一堆仪器。正对门的地方恰好放下两张办公桌,桌子上还码着一排文件,只是被岁月雕琢在上边留下模模糊糊的文字。手术台与病床之间,从房顶吊下来一个老式摄像机,不偏不移的对准那里。下方一个铁架上,墩着一个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些设备,放在几十年前,恐怕也是比较难得的实验条件。
嘶啦啦~铁架上的那台黑白电视机突然放出影像。
几人一惊!没有丝毫心里准备,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视画面吓得连连后退。
“老白,这又活见鬼了,刚进来就觉得这地方阴森森的,果然还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老妖怪。”胖子勉为其难的挡在苏心前头。
“也不一定,这里除了没有人、灰尘厚一点之外,也没有其它问题,没准是因为设备保存的比较好,你又打开了电闸,所以这些设备就自动启动了。”白歌想要努力解释清楚,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事态是可控的。
鲁岩憋着一股气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本放在桌面上的实验记录,淡淡的钢笔字迹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段文字:
实验体:王洪川。
年龄48岁。
籍贯海都。
精神病情:被迫害妄想症。
病情描述:病人处在极度痛苦中,对身体有极强的被迫害妄想,表现出惶恐、失眠、暴躁等,一度对他人造成严重的生命威胁。
鲁岩不急不慢的读出实验记录上的文字。“看来是个精神病患者,整个二院都充斥着这样的群体,对人精神世界的研究,可能才是二院存在的真实意义。”
白歌听完这段文字,甩开步子走到摄像机前,按下了红色的放映键,那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扑闪扑闪几下,一个人影出现在画面里。
画面右下角出现的时间是1974年9月27日,一个患者极度狂躁,被医护人员死死的绑在病床上,患者表情极其痛苦,像是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狰狞狂躁的表情透过屏幕都让眼前的几人感到震惊。录像年代太过久远,画面有些模糊,嘶啦嘶啦的夹杂着无数的雪花点,时不时还会出现跳帧。
被监控的患者撕心裂肺的呐喊。“我的心脏,它在捏我的心脏!快救我,心脏要爆开了!”画面中,两三个医护工作者死死按住他的身体,连人带床一起丢到手术台上。
“准备开刀,胸部开膛术。”医生站在一旁,双手带了两层隔离手套。
“不麻醉吗?”护士疑惑的问道。
“不用!他自己一直沉浸在痛苦中,或许大脑制造出来的痛苦比这一刀子更甚。”
“明白!”护士转头推过各色刀具,放在身旁。“患者超重度被迫害妄想,反复强调有人一直抓着他的心脏,常规治疗并不见效,从心电图上来说,除了心律不齐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很有可能是患者心脏疾病与精神疾病同时发作,导致两者相互作用产生过渡联想。”
医生将一片柳叶似得刀片捏在手里。“我们接触那么多精神病患者,每个都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规则,而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发现,不一定他们都是病态的,或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病态的。”医生说的隐晦,护士听得一头雾水。
刀子深深割了下去,第一刀划开了皮肤和脂肪,第二刀划开了肉膜,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第三道划开了胸腔膜,心脏就在众人的眼前咚咚的跳动着。
“支架!”医生伸出左手。
“止血钳”护士忙忙碌碌。
“注意止血和输血,不要让实验样本死掉!”医生冷冰冰的话语里,只有对眼前这具生命作为实验价值的认可。
“科长,您看!”护士手里拿着止血钳,惊讶的望着胸腔。
虽然白歌一行人只能通过眼前这台模糊黑白电视机感受现场的震撼,但仍然清清楚楚的看到病人的心脏形状不断的变化,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压扁,记录的影像中甚至能够依稀看到心脏上压出的几个指印。
医生探出半个身子,将眼睛凑上前去看的仔细,并招呼操作摄像机的医护人员将镜头拉近,特地给几组特写。
实验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都是护士之间的对话,还有无麻醉状态下的缝合。病人躺在手术台上,依旧是拼命的挣扎,仿佛痛苦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滋啦啦!录像结束了,黑白交相出现的雪花点铺满了整个屏幕,白歌、鲁岩还有站在四周的其他人一同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这些画面让鲁岩想起了他的姐姐,总是沉沦在自己的世界里,和自己脑海中虚拟出来的人物对话,甚至争吵。
苏心早前在医学院的时候也参加过一些精神科的研究课题,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整套完整的世界观,在他们脑海里,植入了一整套认识世界的标准。“你们看,这段录像就非常典型,其实那些被我们看为是异类、另类的精神病患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都要比我们深刻很多,也许是观察的角度、方法、层次不同,总之都是因为显得与大众格格不入,才沦落到精神疾病这个下场。”苏心摇摇头,有些惋惜,人类科学技术已然很发达,却仍对精神世界一无所知。
下宇摸了摸脑袋上的伤口,隐隐约约从绷带里渗出丝丝血迹。“这个问题千万不要深入去想,很容易走火入魔的,你会发现你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在他们所描述的世界里不堪一击。我就举个很简单例子,你看这四周的围墙是白色的吧?”
几人点点头,目不转睛的看着下宇。
“可是,白色对于这个事物而言就是一个符号,是人类共同认知下的符号,假如现在我一定要说周围墙都是绿色的。那你们一定会说我是色盲!因为根本不符合你们的共同判断标准。”下宇目光锁定在那堵白色的墙上。
苏心似乎也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下宇说的就是群体意识,假如人类第一天起就把墙上的这个颜色定义为绿色,而树叶、青草原有的绿定义为白色。那么,可能现在色彩体系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不过也不是说所有的精神病都有这样对世界怀有颠覆性的认识,就像刚刚看过的这段录像,如果这个病人不是落在红洞基地精神实验科专家的手上,恐怕只会被人当做精神病患者,在铁链或者小黑屋里度过余生。”白歌补充道。
“不过话说回来,苏心姐,为什么这个人的心脏会有不规则的被压迫的痕迹?是心肌变形嘛?”子琪很是好奇,从来没有听说过谁的心脏可以变换形状。
苏心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低下头回忆一番。“心肌自由变形的在人类身上没见过,章鱼倒是可以。从这个录像来看,像是被外力压迫的。”
“外力?你是说隔着胸腔,什么样的外力能够不损伤组织。”
林边圆双腿跨开,一本正经的伸出双手,对着众人喊道“隔山打牛!”
“好冷……”子琪转过头走了出去,苏心紧跟在身后。
“我只是想调节一下氛围而已嘛!看你们一个个紧张兮兮的样子,就是一录像,分析来分析去,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边圆想要努力解释清楚,却发大家都默不作声的出去了,留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背后那张空荡荡的手术台,让胖子感到一股冷风直窜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