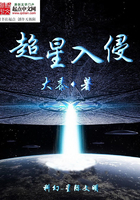5月20日下午19时36分,救灾现场和往日一样三三两两的搜索、挖掘、起重。初夏的夕阳已经开始变成红色,阳光从西面废墟尘埃上折射过来,仿佛尘土都被染上了鲜红的血色。震后这些日子里,除了奋力参与救援的队员,与偶尔突破生命奇迹的幸存者,很少能够看见其它生命再在这片土地上出没。然而今天,也许是为了映衬这片晚霞,从西侧山谷上掠过了几只鸿雁,苍凉了哀鸣响彻整个山城,那声音足以让每一个人都抬头仰望着她的存在。
白歌攀爬在一片建筑废墟堆里,每一步都要都走的坚实,身后时不时会有松散的石块滑落。在攀爬废墟的时候,队员与队员之间自然保持着1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他们之间通过系在腰间的绳索相互警惕着。
“白歌,白歌!指挥中心要你立刻返回回营地。“在废墟下方的队员冲着石堆上的白歌喊道。
白歌下意识地追问了几句,在没有更多信息只知道要迅速返回营地的情况后交接了手中的探测仪便离开了。一路上,白歌内心都在揣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太阳西斜渐渐落进了山谷,地平线上那朵鲜红的云似乎要将所有的红色全部释放出来。白歌走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面朝着那片斜阳,背光的身影拉的很长,一直刺进远处的阴影里。远远的便能望见营地帐篷门前站着下宇,一直摸着脖子向这边眺望着。
下宇看着逐渐走进的白歌,没有任何犹豫,将自己早已想好的说辞和盘托出“你女朋友坠楼意外身亡了!警察只在现场找到一封遗书。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是他杀。你快收拾收拾回去吧,这边已经安排好返程的顺路车。“
“怎么会……“白歌欲言又止,他明白此刻下宇一定是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出最准确及时的消息。他愣在下宇的右前方,双手不自然的垂吊在身体两侧,眼睛似乎看着远方只剩一缕的残阳,白亮的眼仁中还泛着闪闪泪光。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将双手插到裤兜中,低着头从下宇身边走过。
“哥,20分钟后,车在山口公路旁等你。“下宇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一同战斗在救灾一线的老兄,只能看着他的背影,在夕阳中越走越远。
白歌在很小的时候由于工业事故失去了父亲,在后来的十几年中,是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无微不至的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物质。母亲的形象在白歌心目中不仅仅是亲情,更是一种绝对信赖的存在。直到在大学碰到邓雨,才将自己的心托付给第二个人。
上了车,白歌径直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子,将匆忙打包的行李丢在座位旁。此时此刻,在他脑海中,除了情感上的悲伤,就是无尽的问号。小雨是一个乐观、活泼的女孩子,当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开朗的性格总能像阳光一样洒在白歌身上,让白歌在平淡的生活中多出几分色彩。小雨是一个从不悲观的人,似乎所有的矛盾,到了她那里,都是生活的调味剂。印象中最喜欢她15度上扬的嘴角,让人不自觉的舒心。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小雨的美像是一张素描画,用黑白构成的图象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每一笔都勾勒的如此清新。长发披在肩上,当微风拂过的时候,发丝清扬,像极了清水池中一朵圣洁的莲花。
在白歌所有记忆中,没有一片能够和自杀相关联,内心深处早已经将这个选项排除干净。唯独只有小雨留下的那封遗书,也许能够带来一丝线索。
车缓缓使出了山区,渐渐行驶到平坦的公路上,四周可以看见的废墟越来越少了,由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物资却越来越多,他们堆积在距离灾区核心三百公里开外的地方。车窗外远处的地平线随着汽车行驶忽高忽低,呈现出各色不同形状。这令白歌想起了曾经还住在厂区筒子楼里的生活。
他的父亲是个技术工人,在整个厂区,钳工手艺都是数一数二,这在那个基本还没有数字化车床的时代,算得上工厂的技术骨干。白歌家紧临客厅的东面有一面挂满了荣誉称号的墙。在他看来,这些红色的锦旗与证书,承载了儿子对父亲的自豪与骄傲。
记得那是在上小学的某一年,工厂大院里发生了一件家喻户晓的大事。这个工厂是国营器械厂,生产最基本的农用机械,每当农忙季节要来临的时候,总会有各色各样的展销。附近的乡镇生产队都习惯于在这个时节补充些工具。久而久之,除了器械展销外,逐渐形成了临时的农副产品集贸市场,各村各户都赶在这个季节把自己手头攒下来的农产品交易出去。
每逢这个季节,白歌总是伙同大院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搜罗新事物。这一次也不例外,白歌带着几个虎气的孩子大摇大摆的走在农贸市场,一边走,一边把脑袋转到相反的方向,故意指着眼睛看不见的那边说“这是大田庄的鸡蛋,这是官村的斗笠,这是王家店的手工烧饼……”。显然这段记忆,成了白歌对儿时最多彩的一段。
天渐渐黑沉下来,市场上来自各地的商贩有些返程过夜,有些就着附近空旷的地方搭棚混过一宿。这几天时间,往往也是这个厂区最热闹的时候。白歌和几个小伙伴正坐在市场后边的墙头上观望,远远看到一个穿着奇怪的妇人由远处的厂房拐角走过来,头上围着红色的头巾,身上穿着老式的花棉袄,腿上一条黑色的棉裤配上一个深红的布鞋。在他们回忆中,这样的打扮似乎只在赶集表演花子戏里边看到过。只见那人步行缓慢,走到菜场东南角一户售卖鲜羊奶的摊前,打上那么一满壶,又踉踉跄跄走回去了。
起初几次白歌和他的小伙伴们并没有在意。一天、两天、三天那个妇人都按照同样的时间做着同样的事情。
那是一个刚刚下完春雨的阴天,白歌他们终究抵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决定尾随妇人看个究竟。他们躲在妇人出现的拐角后边,悄悄骑在矮墙上观察者一举一动。她还和往常一样,用不急不慢的速度,走到羊奶篷前,打了一壶羊奶,又缓缓的走了回来。白歌紧紧跟在她后边,随她转过墙角,前面是一片50年代建的废弃厂房,眼前这条土路,是通向厂房后边村庄菜地的一条小路。
三个小伙伴悄悄的注视着妇人的一举一动,她走过厂房,走出厂区范围,继续向着前面村庄的空地缓行着。
“哎,白歌,我们回去吧,没啥好看的了。一定是隔壁村的……”小胖子对着藏在路边土堆后边的白歌说。
“隔壁村我们哪个没见过?再说你见过隔壁村谁在这么热的天里还穿着棉袄!”白歌转过头对着躲在后边的小胖子说到。
“白歌,快看!她掉下去了!”寸头目不转睛的看着前方目标。
“不好。快过去看看。”白歌带着三个小伙伴跑到妇人滑落土堆的地方。前方似乎是一口井,井底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到。
白歌与小胖子与平头商量一下,胖子跑的慢,留下来看着,平头回去叫人帮忙救人,而他则四处找找看有没有绳子能够先丢下去试试看。
不一会,白歌的父亲就带着厂里的几位工人赶到了现场,后边还跟着几个赶集的路人,都是闻讯前来帮忙的。小平头一边跑一边继续解释“有人滑倒井里了,就在刚才,快去救人”。
白歌父亲第一个感到废井边上,原来这是一个废弃的塔基,大概是前些年建新厂房,从镇里引入高压线时挖的高塔基,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废弃了。时间久了,外边长满了杂草,不仔细打量,还真看不出来有个竖井。
一行人三三两两砍除野草开出了一条路,用头顶的矿灯照了下,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摔倒在坑底。一行人在坑口,拴了木桩,绑了安全绳,找了一个臂力大的小伙子,慢慢顺着斜坡滑了下去。下边洞口处极窄,恰好能够容纳一人进出,那小伙先前看到有人,没有半丝犹豫就下去救人了。土坑周围的人都全神贯注的观望着,白歌蹲在土路牙子上,与另外两个小伙伴注视着下面发生的一切。
“哇!哇!呜~哇!”洞下传来一阵刺耳的哭啼声。
在场所有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怔。正在洞底救援的年轻人滑了一下,噗一声,落到了坑底。
坑口围观的人顿时砸开了锅,各自议论着,甚至有围观者冲着救援的工人们喊:“还有个娃娃在里边,先把孩子救上来”。
不一会,下到坑底的小伙子爬了上来,右手抱着一个光腚的小娃娃,肚脐上还连着一段脐带,那小娃被抱出来的一瞬间,哭声嘹亮,似乎整个村和厂子都听到了。
小伙慢慢爬出坑沿,动作相比下去的时候僵硬了很多,将孩子交给站在边上的人。白歌看的真切,那人脸色惨白,白里还透着几分紫。双唇微微的有些发抖,眼神涣散打不起精神。
白歌的父亲见状过去掺扶,说“小张,滑下去没受伤吧?是不是被婴儿的哭声吓到了,没有准备,谁知道还有个孩子。大人呢?她怎么样了?”
那人缓缓抬起头,微微带些颤抖的说“女人死了,尸体都臭了……”。
小张的这句话是白歌在现场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随后他们就都被赶回家去了。
自打那以后,白歌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穿着棉袄的女人。
很多年后,白歌从邻居闲聊中无意听得,当年掉在坑里的女人已经怀孕十个月了,也许是走夜路不小心掉进了地坑里,由于杂草丛生,几天时间都没有人发现。然而,肚子里的孩子却神奇的活了下来,熬过了120个小时,真是奇迹。那个孩子后来由隔壁县上一户人家领养,据说后来考上了研究生,并且出了国。
白歌知道,也许只是不愿意承认,也许是时间久了,记忆开始变得模糊。大脑对于究竟有没有看到那个女人每天打洋奶已经没有了确切的证据。印在他脑子里的,只有那每天黄昏,提着奶壶摇摇晃晃走在夕阳下的身影。
这些年过去了,白歌望着车窗外的地平线,突然想到了那个在最纯真年代里的童年往事。这个事情,也许正是他骨子里要去探索未知的原动力。迷信与科学都只是一个名词,一切事物必定有其规律的主宰,只不过这个规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能不能被我们所观察,所理解。
白歌回到学校,去医学院的太平间看了小雨最后一眼,回到系主任那里拿到了她走时留下的那封遗书。
“死亡只是开始”
“丙申年秋见”
诺大的白纸上边,只写了两行字。而这两行字恰恰让白歌掉入了深深的轮回。在人生的这一站,白歌用近乎颠覆来面对面目全非的世界。路上碰到的“人群”的脚步声、幸存者逝去一瞬间的那张安详的篮脸、以及女朋友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离世。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切,恐怕只有“再次”见到女朋友的那一刻,才能让他安心。
白歌站在小雨离世的那个楼层,对着面前的一切,用尽力气喊出自己内心最深层次的困惑:“这个世界!你究竟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