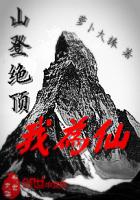整个洛阳,现在分成好几派。
实力最大的的白纪凤是坚定的割剧洛阳派,裘国勤紧随其后,毕自严、元默和史可法是坚定的朝庭洛阳派,但现在毕自严没人理他,元默软禁在家,史可法则是无兵无职,好在还有几支河南的明军,做为这一派的依掌,但也被裘国勤盯的死死的。
李嘉应实力最小,但他属于回师新越派,但人微言轻,也只能嚷嚷那么几句,在洛阳掀不起什么浪花,不过,他后面站着一个新越,也就是说,他也不是没有依靠的,任何人要动他,也要担心那三尊大神同不同意。
只有边上一个左良玉,则是又一次躲得人影都不见。所以,他是酱油派。
“东西在洛阳不能动,属于朝庭的也不用争,不过本官也同意,这河南的事,还是按照你们殿下原来的意思办!”史可法人虽然耿直,但也不是完全迂腐不知变通,当下的形势,撤回去肯定不行,但如果一点都不让步,也肯定会逼反白纪凤。
所以只有先套住这个头生反骨的家伙,再等等局势的变化,希望那个宋王殿下能安全回来,什么事也就好办了。
不过他马上又说:“你们必须把元巡抚放出来,这算什么?扣押一省巡抚,难道你们殿下是让你们造反吗?”
白纪凤一听这话,心里明白,这是要用毕元史三人和几支河南明军,和他分庭抗礼啊。而且名份上这洛阳还是由朝庭控制,那他还怎么玩。顿时火起,道:“殿下自然没让我们造反,可我们殿下人呢?你给我们找回来啊?史大人,永宁的事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殿下帮助朝庭做下多少事,送了多少金银,可是最后呢?这事到底是谁干的?你能不能说个别白?”
“你怎么知道是朝庭干的?”史可法嘴上说道,可心里也打鼓,因为这宋王干的事实在太大胆,竟然把皇帝给劫出了京师,以他对皇帝性格的了解,醒来后一定会勃然大怒,直接指挥张达仁等把这宋王灭了,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说,谁干的?”白纪凤继续逼问。
“也许是建奴,也许是流寇。。。”史可法嗫嚅着说。
白纪凤一声冷笑:“建奴?流寇?史大人还真奇怪啊,建奴和流寇不向皇帝下手,为什么要向殿下下手,这天下还有这么不知轻重的外寇和内贼?”
“这。。。”史可法也无语了,是啊,如果是这两者干的,自然是先下皇帝下手,毕竟,天下是皇帝的啊,不这宋王的。想了半天,才说:“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白纪凤扫了裘国勤一眼,见他没有什么表情,知道是由着自己决定,便道:“我们可以放了元大人,但是,毕大人,元大人和你史大人必须退到黄河以北,左,汤,李三支部队也跟你们走,财物我们可以分一部份给你们,听清楚了,这是我们分给你们,多少要由我们定!”
史可法一听,直接就跳了起来,大叫:“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洛阳是朝庭的府城,岂能容你们窃据,福王的财物,你们殿下都说是朝庭的所有,是太子所有,你们要想私分,除非从我史某身上踏过去!”
白纪凤冷哼一声,阴阴的盯着史可法,一字一句说道:“你当我不敢吗?史兄,你若不肯走,信不信我真的造了这反,我有二千万顷的地,那商洛山里可是还有40万的流民,你可要仔细想清楚喽!”
此话一出,边上裘国勤张大了嘴巴,李嘉应更是吓得冷汗都冒出来,愣愣的看着白纪凤,心里想:这姓白的真要造反啊!”
“你。。。逆贼!逆贼!”史可法“哗”的站起身来,手指着白纪凤,他没想到这文文静静的白举人,竟然有这样的果决和狠辣,直接就要造反。
白纪凤也不管史可法的怒气,只道:“诸位,不是我白某人造反,殿下如果在,以他的神仙手段,或许有更深的想法,也许他觉得这天下太乱,造反意思也不大,还是先把天下救了,再图大事不晚!可是,现在殿下不在了,我等都是凡夫俗子,不能和殿下一般行事,要救这天下,必先图这天下!史大人,若你们实在不愿意走,何不咱们一起图谋大业,轰轰轰烈烈的干一场,也不枉此生!”
史可法气极,却很快的沉静了下来,叹道:“本官虽然与你们殿下共事日断,但本官深信,就算是朝庭害了他,他也不可能造反,若是他知道你白纪凤今日之举,定会后悔自己识人不明,可叹他本欲赈灾救民,却掀起一场滔天的巨难!本官不才,愿随他而去,他日地下相见,也好再探讨一翻救国救民的大道!白纪凤,本官的头颅就在这里,你随时来取,可要我史可法帮你窃据洛阳,想也休想!”
说罢头也不回,正步出了大堂。
白纪凤只朝他的背影看去,吐出一句:“迂腐之极!”
裘国勤有些脸红,可见白纪凤毫不所动,又觉得自己心意不坚,没有图大事的气魄,稍稍抖了抖肩膀,便又回到了烈士暮年的雄思之中,反而有些更加决绝。
“白先生,你真的要造反?”良久,李嘉应觉得还是要问一问。
“我知道你们的心思,觉得我白某人狂悖,可你们想想,殿下为什么要打永宁岚县,为什么要打山西六县,又为什么要打洛阳,这难道不是造反?殿下能造,我等为什么不能造?当然,殿下是为救民,怎么救,我们在永宁也看得多了,无非按着殿下的办法在洛阳和河南再来一场,难道真的象那婆娘说的撤回去,让殿下开创的局面土崩瓦解不成?”
李嘉应叹了声,说:“白先生,我再劝你一句,你没到过新越,不知道里面的神仙造化,殿下能做的事,你未必能做,如果景氏和张三叫一定不让,莫说你一个小小的洛阳,就是这天下,也挡不住他的几千本兵!裘大人,这些,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也不劝说一句?”
裘国勤也没去过新越,但他知道张三叫的本兵肯定比他历害的多,不过,在他眼中,他的民兵也已经很历害了,特别是几个月下来,他从王向科地方学到了大量现代军事知识,用这些知识训练部队,他坚信,不出半年,他就可以带出一支全大明最强大的雄师。
所以,他很想有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使展这些本领,而洛阳,则刚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训练了一支16000人的新民兵队伍。他坚信,就是单凭这支训练才一个月的部队,那几路河南军也不是对手。
不过他知道李嘉应去过新越,肯定知道许多内情,现在他这么说,裘国勤一时也有些慌乱起来,是啊,他真的没见识过张三叫和吕元平的本兵,但他可要感受到,那支军队的战力一定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他最近到达新越的地方就是那个隧道口,而张小山就是从那个地方,开着皮卡用一根长矛刺向了左良玉的咽喉。
看到裘国勤复杂的表情,白纪凤怕他动摇,就开口说: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虽然没去过新越,但殿下的神仙手段也是见识过一些的,不说张三叫,就是那景氏的手段,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是,人无远志,就是百万雄师又能怎样,你没见到他们要我们退回去吗?明显,殿下不在了,他们只是想守着那两个小地方,偏安一寓而已。这天下大势力,不进则退,光靠守,是守的住的吗?再说,他们三个就一定没有分歧,也许过不了多久里面就乱开了!还能顾得上我们,嘿嘿嘿!”
李嘉应心里暗暗叹息:“这白纪凤也算是人才,可人才也是人啊,没到过神仙的地方,张口闭口就谈大势,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好在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有幸去进修了一段时间,否则说不定也会跟着这姓白的走了。唉,算了,见识不同,就随便你们去折腾好了!”
当下便说:“既然如此,李某只是一个商贩,与两位志不相同,你们就留在洛阳,我呢,就自己先回去了,白先生,咱们也算共事一场,莫要留我,留得一段交情也好日后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