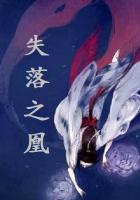(本文不是第一人称)
我是穆禾。
那一年,我八百岁,或者说,那年,我还不叫穆禾。
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南方的大宅,青砖黑瓦,白墙高耸起,有古老石雕的壁檐缝隙,探出瓦松和仙人掌,宅子的光线并不很明亮,房间是木结构的,四面的墙壁、地板、门和窗。窗外晒了衣服,式样简单大方,阳光明亮,似乎听到孩童嬉戏的笑声,从悠远的弄堂那边传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不知道梦里那些别致的景色是怎样的存在,我只记得那一天,我醒来,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我所拥有的以及尚未拥有的一切,都与我失之交臂。
我醒来,日光穿过窗子撒到我的床边,投下一块块被切割了的光块,一如往常。我没有起来,赖床在一个孩子小的时候,是多么正常的事,起码在那个时候,那个我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懒洋洋地起来,推开门,侍女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第一时间出现在我面前,虽然疑惑,并没有多想,我记得我走了很久,还是没有见到一个人,那时我才觉得恐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开始跑,也不知道我是在往哪里跑,但生活的戏剧性往往在于有些事情上,即使你再不想看到真相,它也会安排好一条似乎不存在的定理,把事实血淋淋地放在你眼前,触目惊心。
我站在大堂门口,即使我知道这样有多懦弱,依旧无法控制胃里不断往上冒的酸水。我垂了头,还未来得及打理的头发顺着我弯下去的身体散落下来,覆盖住我的双耳。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血液像止不住的洪流,在我的每一寸血管里叫嚣暴动,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远离我的心脏。
闭上眼睛,眼前一片猩红。
修罗场。
我不能准确地分辨地上红黑的液体。是从面前哪个已经冰凉的身体里流出的,我大抵清楚,昨天晚上,那些祝我八百之年的人,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我面前,再也不可能。可是我没有哭,我知道眼泪的价值,在没有它可以寄托的怀抱的时候,它产生的多半只是自我放逐。
我只是站在门口,站了很久很久。我最终还是踩着满地的暗红,走进大厅,红得晕眩,满地的蔷薇在一股腥味里盛开。
父母的手紧握,他们宁静而自然,似乎只是在沉睡,我站在他们的面前,碰了碰他们的脸颊,踩着满地的鲜红,把手放在大堂正中央的金属桌子上,桌子无声裂开一个洞,我把手伸进去,两封信,一块蓝紫的玉石。
以往每一个生日,母亲都活强调的意外是什么,她总是说,宝宝,你要记得,如果哪天我们遭遇什么意外,不要管我们,拿走老地方的东西,离开这里,千万不要回来,知道吗?
每次我都是敷衍地回答,知道了,知道了。
现在,我却是真的知道了。
我慢慢走出房间,我走得并不快,却很稳。一步一步,我似乎听见有人用清冽的声音喊我的名字,在这个寂静得发指的地方,我偏头,看到一个男孩干净的脸,他没有笑,但我还是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温暖,我来不及开口,眼前就黑成一片。
最后我只记得,他的手托住了我滑下的身体,他的身体微凉,却很安定。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梦见我在一个水乡,在一个城市,从婴儿慢慢长成一个小小的女孩,每天喝奶睡觉,听歌搞破坏,不懂难过不知泪水,原地等待就能迎来拥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梦见我读书,小学,中学,大学,李白,杜甫,牛顿,爱因斯坦。我梦见我恋爱,结婚,生子,四世同堂。我梦见我有一心爱之人,他爱我,胜于生命。我梦见有三两挚友,无关男女,相互扶持,不离不弃。我梦见我的对手,我们互相竞争,互相刺激,有矛盾,但从未恨对方入骨血。我梦见一个美好的世界,与最爱的人相濡以沫,与次爱的人相忘于江湖。我梦见一个人生的尽头,子孙膝下,天伦之乐。再有一日静静离去。
然后我又一次变成婴儿,父母疼爱,却在一个叫耶利米的大陆,没有小学中学大学。也没有杜甫李白。即使百年,孩童之颜未变。
然后我醒来。
看见眼前人的背影,忽然双眼湿润了一片,我伸出手拉住了他的衣袖,他回过头,冷清的面容夹杂了些许欣喜,他的语气温和,他说:“你醒了。”
是的,我醒了。
最终我明白,梦里的那些或许真实的存在,只是相隔太远,我忘记或是我选择性地不记得。
新的人遇到新的环境,只能有蓬勃野心,无关风月心情。
那个自称是家主的男人站在我面前,他弯着腰,揉了揉我的头发,我抬头的时候,仔细地看了他很久,那么近的距离,我却不知,他长的是什么模样。
他却看了我很久,眼底有温柔的温度,末了,他微笑:“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女儿,赐名穆禾。”
穆禾穆禾。
八百之年,血流成河。
以这样啼笑皆非的方式,我变成穆氏一族的小女,穆氏宗家少姑娘。
“他是上弦,以后他护你周全,他大你三百岁,你记住他,有事情找他,又不开心的事情也找他。”家主笑着把那个冷清的男孩带过来,我只是笑,看着那个少年深蓝得发黑的头发,有些恍惚。
我从来都不知道,有一日,我会成为最神秘,最令人惊恐的那个家族的一员,只是这样的存在,令人难以接受。
——穆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