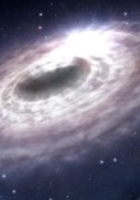第九天,我清晰地记得,太公不见之后的第九天。晚饭过后,父亲还没回家,我在东厢房自家的墙上画正字,记录没看见太公的日子,还差一笔就凑满两个正字了。画完后,我就懒懒地趴到书桌上开始写作业,照理我应该在吃晚饭前就把作业做完的,不过这几天各家都没啥心思管小孩,也就是我妈下班了嘱咐我几句好好学习,但是我记得她的神情却是比另外几房的婶婶们要来的凝重得多,所以我放了学就毫不忌惮地和隔壁厢房的小孩玩闹了一番,一来一去,就到饭点儿了。不一会儿,父亲从外面缓步地走了进来,这几天他也是有些颓废,你说找个小老儿罢,太公100多岁的人,本来就是够稀罕的了,再怎么鹤发童颜,他又能走出多远去,再说了弄堂里天天是些老邻居街坊在走动,老爷子走出去总得有人看见,可这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也寻不见啊,SH诺大个城市,郊区都不止10个县,先不说派出所的叔叔们来回帮忙找,父亲也请了假借了单位的车,各个区县都转了两三圈了,但是今天依旧无功而返。此时的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沙发前,提起双人沙发上我的书包顺手就往旁边的茶几上一扔,顺势倒向沙发:“小清,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沙发上坐人的,不要堆东西。”就只听“当”的一声,清脆而响亮,许是茶几玻璃和书包里的什么硬东西碰撞了一下。我和父亲同时打了个激灵。“小清,你怎么这会儿才写作业?才跟你说过,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往书包里放!今天是不是又从学校里捡什么东西回来了!”
说来,我小时候确实有收集东西的小癖好,但绝对不是那种捡垃圾的主,主要是班里同学玩坏的玩具,甚至是隔壁班同学玩坏的玩具,我会要了过来,攒着,然后把不同的零件拼装组合起来,变成属于自己的玩具,那个时候我每每拿出去显摆,也不关心别的孩子怎么看,就是特别有成就感,或许这一点和我后来选择做医生也有点儿联系。当然我这么做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解释,其中最主要的却是因为太公在我很小的时候曾告诉我说,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灵性的,哪怕是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你如若好生地对它,它自然也会有所感应,你尊重于它,它便尊重于你。所以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萌生了修复玩具的念头,毕竟作为一个小孩,得到玩具的尊重确实是件挺不赖的事儿。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那稚嫩但却已经发育到十足拐弯抹角的小心理就运转了起来:呵,巧了,今天我倒是真没捡到啥宝,隔壁班的强胖子确实是有个被掰折了腿的变形金刚,居然要我承认跑步没他快才肯给我,天晓得,还有人能比他跑的慢,拉倒吧,不给就不给,那折了腿的变形金刚在他手里也玩不了几天啦,前一周默写生词全对,我妈早给我买了个新的了,还是博派汽车人呢,不过我妈说了,这几天爸爸忙,叫我少添乱,玩具的事也不能让老爸知道,那这会儿是个啥玩意儿在我书包里呢,难道是我妈给我买的变形金刚忘了取出来了?。想到这我不由自主地偷瞟了一眼床底下的鞋盒子:“不对,变形金刚吃饭前还玩过,刚才放回去了,那会是啥玩具留在书包里,不管了,现在随便什么玩具在书包里,老爸都不会高兴,不能去看”。瞥了一眼父亲深邃的眼神,我自然而单纯地回复父亲:“没有啊。是铅笔盒子。”(我这种心理状态,太公在我上学读书前就看明白了,他不止一次地和父亲说,这小子七窍玲珑心)。
“哦,铅笔盒子,以后回家先取出来,写作业也要用的,……,嗯……,好小子,吹牛不打草稿了是吧,你写作业不用铅笔盒子啊!!!”父亲起先也是一个没反应过来,这会儿朝我书桌上一瞥,铅笔盒子就好端端放在我作业本前面呢。我家最忌就是小孩子吹牛撒谎,父亲虽然在单位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平时说话客客气气,但是毕竟军旅出身,平时教育我最多的就是诚实,现在明摆着一个吹破了牛皮的谎话,我是上哪儿都喊不了冤了,当时我那小脑瓜子就开始往外汩汩冒汗,要知道这院子里哪家孩子没有尝过父亲手底下的竹笋拷肉,看来今儿个是过不去了。
许是父亲这几天找太公的事也憋屈,转头找了几遍居然都没找到茶几上压在书包下的那把尺子,要若不然,定是噼噼啪啪往我屁股上一顿招呼。趁手的兵器没找着,父亲直接抄起我的书包往里翻,我当然是心里紧张,也是不敢吱声,您可千万别往尺子上看呐。要说这会儿任凭什么东西落在书包里,只要不是学习用品,估计都得被父亲砸个稀巴烂,天晓得,我有什么宝贝忘在里面了,现下不挨揍倒是要紧问题。我惴惴地看着父亲,他也是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眼睛不眨一下地盯着我,这是他生气时特征性的面部表情(后来看解放军题材的电视剧,我领会到,部队首长发怒都是这样子的)。
忽地,父亲的手似乎触及了什么东西,脸上猛地一怔,随后迅速将东西取出书包,父亲手里的赫然是一个带着绿锈的金属匣子,看着再熟悉不过了,这不是太公的宝贝匣子又会是什么。“好小子啊,学会偷东西了,太公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你都能给我翻出来,我看你是不是几天不打,屁股发痒了!”一贯持重的父亲放下手里的东西,没再多一句话,直接走到我面前,夹着我的腰,把我往膝盖上一横,提起巴掌就是一顿暴雨梨花。说实在的,当过兵的就是不一样,第一下痛过之后,我的屁股就彻底麻了,后面就只听见噼噼啪啪的巴掌声,我则完全沉浸到毫无保留的大哭状态里不能自拔。
大概有三五分钟吧,父亲许是手酸了,我也几乎哭晕了过去,在我的记忆里那次家法是我受过最严厉的几次中的一次。事后,我妈把我抱到床上趴着,我回头盯着那个铜匣子抽噎了很久,并发誓以后不能再这么哭了,因为哭得再凶也救不了自己,挨打的只能等揍人的停手,我又天生不是个求饶的主,哭的越凶,挨的越惨。
闲话不表,那天晚上我是撅着屁股睡着的,晚上做了个梦,自己站在一大片树林前方,远处似乎是一片连绵的山脉,一条小蛇通体赤红,两只眼睛泛着黑光,盘在一个像半截儿树桩子一样的石台上,许是看见了我,蛇头机敏地一抬就开始冲我嘶嘶吐信,并且时而仰头,时而在台子上打个转,似乎是想游下石台,每次接近石台边缘却停了下来,有那么几次小蛇很明显是朝着我的方向,略有停顿后忽地探头而起,但是就像是有堵看不见的墙挡在石台的边界上一样,蛇头一旦触及边缘便被弹了回去,接着小蛇就乱打乱撞般在石台上那个2尺大小的空间里到处游走,最后怔怔地仰头盯着我,黑色的小眼睛里,似乎并无什么不悦,倒是多了几分惘然的感觉。第二天早上,我被屁股上的伤痛醒了过来,猛然发现前一天的作业还没完成,总算我家对面查奶奶家的孙女迎春是我同桌,大清早的,我牙也顾不得刷,直接从抽屉里拿上一卷口香糖就奔迎春家,站在她的家八仙桌旁迅速把作业抄了,屁股还兀自疼得厉害,要说抄作业这事也不能让父亲知道,要不然再来一顿家法,今天这学估计是不用去上了。抄完作业,我不声不想地回家吃早饭,四方桌前祖父、父亲和母亲已经坐在了那里,父亲一脸严肃,看着本来话就不多的他,这会儿我是更不敢做什么声响了。要知道平素祖父、祖母一直和二叔家搭伙,这是父亲在外当兵后就形成的惯例,前不久二婶下岗回家,祖父那些退休工资多少也会拿出点儿给二叔家的,没想到今天祖父却一个人到我们屋坐着,想是和昨天那个盒子有些关系。
“小清啊,快来爷爷边上坐,时候不早了,吃完还要上学去呢。”要说我们那时候上学家长就爱挑个近的,一来是孩子接送上学方便,那时候双职工家庭的家长都忙,稍大点儿的孩子能自己走去学校,二来,中午吃饭也能回家吃,免了去学校带饭或是要交伙食费。我上的小学就在弄堂后门一转弯,还是个区重点,自然是极其方便的,要放现在我家老宅就是响当当的学区房了。我瞥了一眼父亲,看他脸色没好看到哪儿去,就绕了大半圈桌子坐到祖父旁边,屁股则是轻轻放在凳子上去的,中间当然也是有点做作和夸张的成分,我就是做给阿爷(沪语:爷爷)看的。
“我说阿大啊,侬昨天打小清,整条弄堂也是都听见了的”,祖父一手端起泡饭啪啦了一口,冲着父亲来了一句。祖父虽然是读书人,但对子女们都还是老SH那套阿大、阿二的叫法,“太公的东西侬刚刚交给我了,就不要再唬着脸了,大清老早的,还是要弄得大家心情好点,找太公也找了十来天了,这个事情侬晚上把阿三、阿四和其他几个都叫到客堂间来,阿二我等下会跟他去说的,总归是要有个讲法的啊。”
“嗯,是的,爹爹(沪语:老SH人均称呼父亲为爹爹),阿爷是全家的一个宝,这一不见,家里确实有点乱了,我们应该是要开个会,大家都停了这么多天去找人,一点结果也没有,后头的事体要好好安排一下,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祖父转头看向我:“小清,太公的那个盒子侬爸爸讲是侬拿了去白相(沪语:把玩的意思)的,告诉阿爷,侬是在哪里寻到的。”祖父一口标准的SH本地腔,不紧不慢的说着。
我瞅了一眼父亲,正看见他也盯着我这边,我一时也想不出该怎么回答,毕竟十岁的小孩,再机灵也来不及现场编词儿,但是看着父亲的眼色,是很想把昨天未结束的审问继续下去。没办法,低头吃饭吧,我伸手就抓了根油条自顾自嚼起来,偷眼还瞄了瞄祖父和父亲,只见他们似乎是目光交汇了一下,居然也没有了下文,即如此我也就顺势而为了,一句“我吃饱了,上学去了”,一溜烟儿跑了出去,此刻屁股倒是没啥感觉了。要说我从小就会见机行事祭出这招脚底抹油的功夫,也该算是太公传授于我的,在后面的一个故事里着实被我发挥到了极致,之后再细细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