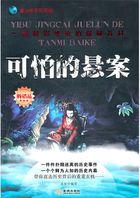上学时间临近,学生们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艾美用眼角的余光扫见,平时对她不爱怎么搭理的同学,在经过身边时,都把好奇的目光探过来,这使她隐隐觉着得意。她终于也站了一次中心位置。
小女孩的话匣子一旦被打开,就滔滔不绝。她告诉他:“我妈叫冯月蓉,是公关经理,昨天飞去深圳了。”她告诉他:“我爸叫艾大力,在公交公司上班,是个司机。”还告诉他,“我今年十岁了,上三年级四班。”直到大胡子笑眯眯地提醒,上课的时间快到了,她才戛然打住,依依不舍地挥挥手:“胡子伯伯再见!”转身跑去。
进了门,扭头看,那大胡子还呆在原地,就又冲他挥手。那人也挥手。艾美觉着。她俩人之间有根丝连着。手连着,眼也连着。
四把鲜虾倒进盆里,用清水涮洗,三遍后盛放盘中。桌上的火锅正嘟嘟翻着热浪,辣酱、白醋早就一溜儿摆好。
大胡子夹起一只虾,伸进滚汤里一摆即捞,就要这鲜劲儿。一旁,艾美正吃得不亦乐乎,白生生的虾仁放调料里蘸一蘸,含在嘴里像要化掉。小丫头嘴巴快,胡子才烫好一只,她就一剥皮,猫儿似地抿进嘴去。面前的小碟很快就堆满了虾皮。
这胡子倒是好耐性,一直笑眯眯地,嘴里还劝着:“多吃点儿,虾是艾美买回来的,艾美是大功臣喽!”
那天早上在校门口发生的事,让艾美着实兴奋了阵儿,下午上美术课时,秦老师满脸欣喜地进来:“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著名画家廖岸先生来咱们海岛写生,并将在咱班找一名小模特,配合他创作油画《海的女儿》……”
马上,艾美就瞧见老校长陪着大胡子走进教室,她登时便云里雾里,胡子伯伯会是老师说的那个画家?这嘴巴一张开就合不拢了,只来得及发出半声“啊!”
四下的叽喳声,一下子就遥远了。她看见胡子点头笑着,校长笑着,秦老师也笑,小朋友也笑,笑声弥漫开了。
几个长相姿俏的女孩赶忙坐正了身子,把胸挺得高高,眼睛随着秦老师的指指点点而眨动。但胡子只是浅笑,嘴里哦哦地随声附和,最后目光撒下来,终是触到了艾美。笑意一下子浓了。
这笑是不一样的,让艾美瞧着心一热,胡子小声对秦老师说了句,又朝艾美指指,秦老师一愣,笑脸先紧了下才缓开。
她走过去,说:“艾美同学,从今天起……”
但我们的艾美却并没有听她老师讲完。艾美觉得自己轻飘飘地飞起来。
海的女儿是天使。天使眼中的世界是最美丽的。
此时的艾美想告诉每一个人,这天起,她找到了童话里的自己。
五我们的海,像蓝宝石碾碎在那里,人亲近它,总有所捡获。
秋天的风只有丝丝的薄凉,海水在它轻柔的呵呼下,便像光滑的绸缎扬起抖落。黑船、白帆、绿藻,连同远处的云,都成了缎面上的饰纹。那成群的鸥鸟,则随着海水的起落,或俯冲或滑翔,让串串嘹响的鸣叫悠然远去。
这些景致落到大胡子廖岸的画笔下,已变得抽象,甚至于变形。让艾美最不能理解的是,海水明明蓝油油的,为什么画布上却少见蓝色?她要画时,肯定红是红,白是白,不让它看上去脏。可胡子告诉她,这样子画才有层次感,才能把光点和影像表现出来。
说来说去,艾美还是没搞懂。孩童的世界本就这么简单,事儿越复杂的反难圆其说。所以,廖岸就换了角度去引领她。
“你想想看,热情应该是什么颜色?”
这问题对十岁的孩子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特别艾美,她从前几曾被人热情过?但她很快就回答是红色。因为大胡子的出现让艾美感到了火热。
“这就是对了!”廖岸嘉许的拍拍她的肩,“有时候,愤怒也是红色的,能烧得人失去理智……你再想想看,黄色是不是让人觉着温馨?粉红会不会营造出一个梦境?”
艾美使劲地点点头。这些都是她从前所贪恋的,每种颜色都让艾美想起离她很遥远的妈妈。
“我们再来看这蓝色,当然喽,蓝也是好多种的。譬如幽蓝吧,常叫人心境发冷;淡蓝呢,又会让你觉着明朗。蓝可是你肉眼能见到的最多的颜色,蓝天、大海,占去一半还多的视觉空间。”大胡子边说着,边指向海天一色的天际。
“我不喜欢蓝色。”艾美突然说,“蓝色是冷的。”廖岸身子一僵,在她面前慢慢蹲下去。不言语,平视着。两对眸子,淡淡流露出的郁怨,感染了各自瞳人里的对方。
轻轻伸出手去,却只触了触她的额发,他还是没说出话来。风在旁代替了,浪在旁代替了。心去说了。
“孩子,知道‘想念’是什么颜色吗?”
艾美摇摇头。
“你要知道想念是什么颜色,那你也就长大了。”六一周有两天,艾美会跟廖岸去海边,其余时间上学不误,但这孩子心野了,晚上也会跑去胡子那里。
这样子话,艾大力这个做爸的便不得不去接她,两个男人也就相识了。喝过酒,吃过虾,公交司机诉倒了做男人的辛苦,也换来廖岸的同情和理解。一句话,谁活着都不容易。
每夜站在阳台上,目送司机领了艾美而去,粗大的身影牵着小小的影子,转眼就溶入夜色里,画家感到怅悯,会想很多事,从前的,现在的,甜蜜的,哀伤的。常常,他跟云天上的月亮一样,失眠了。
但那幅《海的女儿》,廖岸却迟迟没有开画。他和艾美的脚迹已印遍沙滩,现在又转向了别处。他似在寻找什么,或等待什么。
譬如现在,他就远离了海,枕着双臂,仰躺在公园的草坪上。一旁,艾美在咚咚地踢一只皮球。远处,有人放起风筝,是只花色的大蝴蝶。
天上有云朵,已歇在那儿好久了。廖岸看着它,想着事,自自然然地,便把云幻化成一张女人的脸,她冲他笑,嫣然欲滴。他给她系上条红丝巾,让它开成一朵莲。
耀眼的红,像舞动的焰火。莫非,这就是他心目中“想念”的颜色可心动,云也在变,女人脸上的笑意逐渐稀淡了,慢慢染上怒色。终于——啪地声,重重一记耳光,分开了两个人,写下一段冲突……廖岸痛苦地闭上眼,四下一片阴暗。
仿佛有只小兽,蹑手蹑脚地近前,它屏着息,像在窥伺。隔了会儿,便有毛茸茸的物什搔向廖岸的鼻孔。大胡子啊嗤一声坐起,就见艾美笑着跳开,手里犹自拈着根三叶草。
廖岸跳起追去,艾美格格地笑着躲闪。跑着,跑着,他也成了孩子。
西天,夕阳喝醉了,树叶在秋风中轻轻地鼓掌,打着节拍。
放风筝的人竞把“蝴蝶”放飞了,它断线了。
七一晃,画家来到小城快十天了,已尽识了这里的风土人情。除去到海边写生,他倒更愿在一些老街小巷走走,那些坍破的老房子有种怀旧色彩,让画家情不自禁地就想起那个女人,想起十年前,她跟自己讲起过的,关于小城的点点滴滴。
这种老巷注定是清冷的。生满锈的门环,裂开缝的门板:摇晃的狗尾巴草,从瓦檐硬挤出来:凹凸的石板路,染了苔,挂了绿。
它的黑白色调,凝重质朴。人站在这儿,压久了的心事,容易给翻出来,但像羽毛样落在深潭上,不会马上沉底,更难轻飘飞起,给人以浮躁。
他想象七、八岁的她,一蹦一跳地穿过小巷,两条麻花辫子来回丢荡,那两个红色的大蝴蝶结,便拍翅飞舞了……雨像雾一样下,小巷朦胧着,十三、四岁的她撑着竹伞,月白色的衫子黑色的裙,弯弯的刘海,眼眉总是压得低低,笑也不露齿。那种羞态是极惹人怜的……然而,火热的她,艳丽的她终于也来了。那是一个温柔的漩涡,他在里边迷醉了。她的红丝巾,火一样的骄傲的红丝巾,总在他的视野里飘着,一直飘到了今天……折曲的小巷,随风飘落的几片叶子,大胡子男人,眼中的深远,雨丝,伞与红纱巾……慢慢地叠化成廖岸所写的一幅画。画家笔下一挥,起名叫作《思想起……》。
八有些事情,拾得起,放下难。只看心情如何割舍。
十天短短,一闪即过,秋还未深,廖岸便将离去。他给艾美买了套衣服,暗花色的衬衫,蓝色的背带裤。女孩试了试,竟然十分地合身,临镜一照,差点儿连自己都不认识了。
“伯伯,你又没带我去商场,咋会挑得这么合适?”
廖岸笑了笑:“你伯伯是画家嘛!哪能连这点眼力也没有?”
艾美就嘟起了嘴巴:“我爸爸可不行,净会买些过时的货。”大胡子拍拍她的头:“他太忙了……以后想穿什么好衣服。就给伯伯写信,我给你买。”女孩却并没露出喜色,只管用手去撒扯衣带。
廖岸说:“艾美啊,伯伯赶明儿就走了,别弄得一脸不高兴。”一顿,又道,“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心事,说来听听?”
艾美抬起脸来,眼里一汪水儿:“你不是要画《海的女儿》吗?怎么没画就走了?”
胡子蹲在她面前:“伯伯早画好了,放在心里头呢!你就是伯伯要画的画儿。艾美你要记住,你也是海的女儿,大海对谁都是公平的。”艾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道:“伯伯,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别的小朋友,都有人讲故事,我妈妈可从来不给我讲。”“好,伯伯讲。”廖岸的声音发起了颤,“你想听什么呢?”
艾美拍着手说:“就讲小人鱼的故事。”“《海的女儿》你不是已学了课文么?”廖岸沉吟着,“这样吧,我讲个《红帆》的故事可好?那里边的女主人公也是大海的女儿。”艾美点点头,双手托腮,静等开讲。
“从前,有这么一个小渔村,活着几十户渔家。有个叫阿旺的老爹,他是个孤身,日子过得很是清贫。某一天,他在海边捡到了个弃婴,是个小女孩,便抱回家去养活,起名叫红帆。”“小女孩一天天长大,也越来越好看了,父女俩相依为命,日子却越过越紧巴。而渔村里的年轻人,也大都争先离去了。”“在红帆十四岁那年,老爹得了重病,眼看无救,因怕红帆失去生活的勇气,他就骗她说,在红帆十八岁那年,会有个年轻英俊的王子,开着一艘红帆船来接她,去过幸福的生活。”“红帆呢,她丝毫也没怀疑她阿爹的话,真的把这句话当成了寄托,孤身活下去。当然了,乡邻却不这样看,反认为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因为她总爱站在海边向远处看。这样子一等就是三年,红帆十七岁时,出落得更美丽了。”“一天,风浪卷来一个年轻人。他获救后,暂留在这小渔村养息。结果,在看到红帆的第一眼时,他就被对方的纯洁和美貌给迷住了。自然,他也听到了不少她有病的传言,还有那个王子与红帆船的荒诞的故事。但少年却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他不久便离去了。”“他是富商的儿子,有万贯家财,回去后马上打造了一艘红帆船,并穿上华丽的服饰,去小渔村接他的至爱了。”“红帆那天正在海边翘盼,因为过了今天,她就满十八岁了。便在这时,奇迹出现了,红帆船真的来了。一个穿华美服装的年轻人走下来,对她说,我就是你等的那个王子,请跟我走吧!红帆一点疑心也没起。在她心里,一直坚信今天有奇迹发生,因为她从来就没怀疑过她的父亲。”“这下子,全村的人都给惊动了,看着红帆跟‘王子’乘船而去,他们不禁伏首膜拜。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爱能够创造任何奇迹。”九在码头送行那天,艾美觉着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就像一场细雨后,经受了滋润,花苞开始透出了微红。
“答应伯伯,闭上眼睛,默数一百个数再睁开。”胡子廖岸说。
艾美点点头,果真合上眼皮,只睫毛微动着,廖岸的右手从她的额头滑下,轻抚过她的眼睛,指间有了湿意。
他拎起了行李箱,大步走上船去。艾美耳边响起船的拉笛声、浪声和鸥鸟的尖叫声。她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伯伯。昨晚她就哭过,今早起来眼还红肿着。可现在,又忍不住了。
廖岸直到上了甲板,才回转了身。但那女孩一直没朝他摆手。她的眼一直闭着,虽然那数儿早已数过了一百。
他觉着两眼潮潮的。再见了艾美,我的女儿他轻叹了声,走进船舱,一眼就看到那个长相冷艳的女人。她穿套名贵的白套制服,正在等他。
离开船还有十分钟,女人问廖岸:“这样子就算完了?”脸上现出一丝讥讽。
廖岸不愿跟她吵,这比做什么都容易让人倦怠。”我只想亲眼看看她。”“那又能怎样,就能弥补孩子这十年来亏缺的父爱?”
“可至少……艾美她现在改变了,我给了她信心,这不是其他东西所能比拟的。”女人不说话了,只盯着他——从前的廖岸很像个孩子,他有常人所没有的灵气,也有常人所没有的怪僻。他奉行独身主义,从来不想为任何人留下来。
廖岸平静地看着女人——她不再系红丝巾了,但眼里闪射的愤怒是红色的。那个秋日,她打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哭着跑开,掠起了一路的叶子……这就是他俩的爱情故事。如今早已成为往迹。
现在,她长发一甩,再次转身而去。廖岸没有留她。只在后边追了句:“红帆,爱是无罪的。”女人的身子轻颤了下,还是挺胸走出船舱。外面的阳光一下子就温暖了她。
她头也不回地走向码头,走向阳光底下那个孤独的孩子。
艾美这时已睁开了眼,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大步走来,阳光给她身上涂上层金色,不断地闪亮,艾美大叫一声:“妈妈”,便扎进了女人的怀里。
冯月蓉怎么也没想到,才短短的几天,她的丑小鸭便真的被魔棒轻轻点过了,变得美丽了。
她母性的柔情终于被唤醒,紧紧地搂住了她的宝贝,眼泪簌簌而下……船开走了。
孩子在沙滩上跳着,拍着手:“船啊!海啊!”
孩子,你现在知道“想念”是什么颜色了吧在这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勤奋会得到报偿,而游手好闲则要受到惩罚。
走到子夜午后串联着午后,就好像我此刻正在穿行的这条长廊,一样的灯光,一样的墙壁,一样的门扉,一样的锁。声音完全是从身后传来的,鞋子与水泥的摩擦,双臂与两肋的碰撞,心跳与耳鼓的互答。午后,穿行在午后的长廊。
其实已经很久了,一直这样走着。头顶的灯光总是冷漠的,我几乎每一次都是用力地撑过一盏,再撑过一盏。那份冷漠像似前尘被某一个人嚼烂的语言,明晃晃的但不耀眼。我自然要在这些细密的语言中走过,并且在我走过的时候同样会有灰尘泻落,光影般洒了一肩。墙壁,依旧平坦,尽管已经涂满了文字。我知道那是谁写下的断章或者长歌的碎片,在某一个午后,以拇指坚硬纤长的指甲面壁独语,直到墙壁吃尽指尖。至于门扉里的脸孔我又何必去看,窗镜后有窗帘,窗帘后有帏幔,帏幔后有浓发,浓发后……真实的脸给手掌遮蔽,手的背面两股青筋。一样的锁,一样的漆着湖蓝。崭新的一种冷峻的守护犹如远古残垣的青砖,僵硬地垒砌着故事的起点。
而我的午后的长廊依然穿行。我需要穿行。说过的看过的跌过的撞过的俱已退却,眼前竟依然还是长廊。完全从身后传来的声响是我唯一必须留下的声响,眼前秩序的灯影是我惟一必须探寻的走向,门反锁着,钥匙不在身后,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