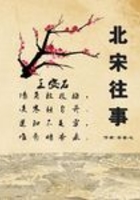福伯急匆匆赶回大高碌路,当他走进屋里的时候,发现他离开时的那些宾客已经移坐到客厅里了,珠儿和那些人都在着急地等待他,他一进来,立刻受到大家的欢呼。
“喂,专砍脑袋的人,国家的支柱,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人问。
“是不是新的恐怖时期又到了?”又一个人问。
“是那个桃花岛魔鬼逃了出来?”第三个人问。”
“侯爷夫人,”福伯走到他未来的岳母跟前说,“我请您原谅我在这个时候离开您。侯爷阁下,请允许我私下里同您说几句话,好吗?”
“呀,这事情十分重要吗?”侯爷问,他已经注意到福伯满脸愁云。
“严重到我不得不离开你们几天,所以,”他又转过身去向珠儿说“是的,事情是否严重,您自己是可想而知的。”
“您要离开我们了吗?”珠儿掩饰不住她的情感,不禁地喊到。
“唉,我也是身不由己。”福伯答道。
“那么,你要到那里去?”侯爷夫人问。
“夫人,这是衙门的秘密,但假如您在篱笆城有什么事要办,我的一位朋友今晚上就上那儿去。”宾客们都不禁面面相觑。
“你要同我单独谈话吗?”侯爷说。
“是的,我们到您的书房里去吧。”侯爷挽起了他的手臂,同他一起走出客厅。
“好啦。”他们一进书房,他就问,“告诉我吧,出了什么事?”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不得不立刻到篱笆城去一趟。
现在,请原谅我不能泄露机密,侯爷,我大胆唐突问您一句,您的手里有没有国家证券?”
“我的财产都买成公债了,——有六七十万两白银吧。”
“那么,卖掉,赶快卖它们。”
“呃,我在这儿怎么卖呢?”
“您总有个代理人吧?”
“有的。”
“那么写一封信给我带去,告诉他赶快卖掉,一分一秒都不要耽误,或者我到那儿时已经晚了!”
“见鬼。”侯爷说,“那么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
“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代理人,命令他不论什么价钱都要赶快卖掉他的证券。
“唔,”现在,福伯把信封夹进他的笔记本里,一面说,“再写一封信!’“写给谁?”
“写给国王。”
“我可不敢随便写信给国王。”
“我不是要求您写信给国王,您叫晋侯写好了。我要一封能使我能尽快见到国王的信,无需经过那些繁杂的拜见手续,不然会丧失很多宝贵时间的。”
“你自己去问掌印大太监好了,他有进奏权,会设法让你朝见的。”
“当然可以,不过,何必要把我发现的功劳让别人来分享呢。掌印大太监会把我甩向一边。而他一个人独亨其功的,我告诉您,侯爷,假如我能第一个进入皇宫,我的前程就有保障了,因为,我这一次为国王所作的事,他永远也不会忘掉的。”
“即然如此,那你就快准备吧,我会叫晋侯欧给您写你所需要的那封信的。”
“最好能赶快写,再过一刻钟我就要上路了。”
“你叫马车在门口停一下吧。”
“您代我向夫人和珠儿小姐表示歉意吧,我今天就这样离开她们,的确是非常抱歉的。”
“她们都会到我这里来,这些话,留着你自己去说吧。”
“多谢,多谢。请赶快写信吧。“
侯爷拉了铃,一个仆人应声走进。
“去,告诉晋侯伯爵,就说我在这儿等着他。”
“现在好了,你可以走了。”侯爷说。
“好,我马上就回来!”
福伯匆匆地走出了侯爷府,忽然他又想到,假如有看见代理法官走路这样慌张,全城准会骚动起来,所以,他又恢复了他正常的恣态,官气十足地走去,在他的家门口,他看到了有一个人站在阴影里,看来好象是等候他的,那是宋丽丽,她因为得不到爱人的消息,所以,跑来打听他了。
当福伯走过去的时候,她就迎上前来,李格銮曾经提到过他的这位新娘,所以福伯立刻就认出了她,她美丽和端庄的仪恣使他吃了一惊,当她问道她的情人的情形的时候,他觉的她象是法官,而他倒成了犯人了。
“你所说的那个年轻人是一个罪人,”福伯急忙说,“我没法帮助他的忙,小姐。”美茜塞苔再也忍不住她的眼泪了,当福伯大步要走过她的时候,她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我想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
“我不知道,他已经不由我管了。”福伯回答。
他急于想结束这样的会面,所以就推开她,把门重重关上了,象是要把他的痛苦关到门外似的,但他内心的痛苦是无法这样被驱逐的,象维吉所说的致命箭一样,受伤的人永远带着它。他走进去,关上门,一走到客厅,他就支持不住了,象呜咽似的,他长叹一声,倒进了一张椅子上。
然后,在那颗受伤的心灵深处,又出现一个致命疮伤的最初征兆。那个由于他的野心而被他牺牲的人,那个代他父亲受过的无辜的牺牲者,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他脸色苍白,带着威胁的神气,一只手牵着未婚妻,她的脸色也是一样的苍白,这种形象使他深感内疚——不是古人所说的那种猛烈可怕的内疚,而是一种缓慢的,折磨人的,与日俱增直到死亡的痛苦。
他犹豫了一会。他常常主张对犯人处以极刑,是靠了他那不可抗拒的雄辨把他们定罪的,他的眉头从来没有留下一点儿阴影,因为他们是有罪的——至少,他相信是如此,但现在这件事却完全不一样,他给一个清白无辜的判了无期徒刑——那是一个站在幸福之门无辜的人。这一次,他不是法官而是刽子手了。
他以前从没有过的这种感觉,现在,当他怀着茫然的恐惧,犹如一个受伤的人用一只手指去接触到他的伤口时,会本能地颤抖起来一样。这一种感觉只有当伤口愈合以后,往往还会再次裂开,并且这一次裂开的伤口更加疼痛。他的耳边响起了珠儿请求他从宽办理的甜蜜声音或是那宋丽丽似乎又进来对他说,“看在佛祖的份上,我求您把我的未婚夫还给我吧!”如果是这一种情形,那他就会不顾一切,用他那冰冷的手签署他的释放令。但没有声音来打破房间的沉寂,只有福伯的仆人进来告诉他长途旅行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福伯站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象是一个战胜了一次内心斗争的人那样,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急忙打开他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把里面所有的金子都倒进他的口袋里,用手摸着头,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最后,他的仆人已把他的大氅披在了他的肩上,他这才出了门口,上了马车。吩咐车夫赶快到大高碌路侯爷府。
不幸的李格銮就这样被定了罪。
正如侯爷所说的,福伯看见侯爷夫人和珠儿都在书房里。他看见珠儿的时候,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她又要来为李格銮求情了。唉,实际上她只想着福伯即将离开她了。
她爱福伯,而他却要在成为她的丈夫的这一刻离开她而去了,也不知道他何时才能回来,所以珠儿非但不为李格銮求情,反而恨起这个人来了,就因为他的犯罪,她和他的爱人就得分离了。
那么,宋丽丽又怎么样了呢,?她在碌琪路的拐角上遇到了亲爱的。她回到了黄龙江人村后,便绝望地躺在了床上。亲爱的跪在了她的身边,拿起了她的手,吻遍了它。但宋丽丽已毫无了感觉,那一夜她就是这样过来的,灯油燃尽了,但她并没觉得黑暗,她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光明,悲哀蒙住了她的双眼,她只能看到一样东西,那就是李格銮。
“啊,你在这儿,”她终于意识到了他的存在。
“从昨天起我就在这儿,就没有离开过您。”亲爱的痛苦地说。
宋刚来兄弟,就没有放弃过努力。他打听到李格銮已经被投入了监狱,就去找他认识的所有的朋友和城里那些有钱有势的朋友,但城里的风声已经传开,说李格銮是被当做黑黑党的密使而被捕的,而且当时再大胆量的人也认为黑黑东山再起是狂妄之举,因此,宋刚来兄弟也四处遭到拒绝,只能是失望的回家。
黄晋升也感到了不安,但是他没有想办法去救李格銮,只是带了一瓶酒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想用酒来忘掉他的回忆。
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已醉的腿都抬不动了,但他却忘不掉那可怕的往事。
只有张瑚房一个人一点都不觉得烦恼或不安,他甚至还很高兴——他认为自己已除掉了一块绊脚石,并保全了他在君山号上的地位。张瑚房是一个一心只为自己打算的人,这种人生下来耳朵上就夹了一支笔,心眼里头放着一瓶墨水,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加减乘除而已,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命还不如一个数字宝贵,因为数字使他有所增加,而生命却只会渐渐消亡。
福伯接过了晋侯欧兄弟写的信以后,就拥抱了一下珠儿,吻了吻侯爷夫人的手,和侯爷握手告别,起程前往篱笆城去了。
李格銮的老父亲正在被悲哀和焦急煎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