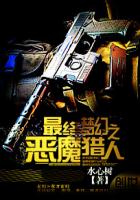巨大的撞击力,震得叶明瞻眼前又飞起成群的金苍蝇。
不等金苍蝇消失,蛾后轰一声吼,口器往上一提,把他甩向左边的洞壁。
眼看蓝幽幽、不知冻结了几千年的冰壁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咬牙使出吃奶的力气,挣扎着做最后一搏。
蛾后的口器不但不松,反而勒得更紧。
只剩不到十米就要撞上去了,他已经可以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坚冰的寒气。
他脸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闭上了眼睛。
他不想看到自己的脑浆溅在那冰蓝色的洞壁上。
“明瞻——!”靳风发狂似的咆哮几乎和蛾后凄厉的嘶吼同时响起。
箍着叶明瞻的口器突然松了,他的双臂有了活动的余地。
他睁眼一瞧,洞壁已近在咫尺,来不及多想,肩膀一耸,在撞上洞壁的瞬间,他飞快地侧身缩起脖子。
他左肩重重撞在洞壁上,疼得几乎背过气去。
撞击产生的反作用力随即将他从洞壁上弹开。
他脊背朝下,摔向地面。
不行!燃料筒刚才已经替他挡过蛾后尾巴扫断的大冰块了,再从这么高的地方砸到地上,不管它是多结实的材料做的,也肯定会破。
燃料筒里的每一滴汽油,对他们来说都比金子还珍贵!
心念闪动间,叶明瞻强忍着肩膀的剧痛,在半空中尽量调整姿势,侧身落地,避免了燃料筒直接爆砸在地上。
燃料筒是保住了,他自己却摔得狼狈无比,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还磕破了脑门,咬伤了嘴角。
他昏头涨脑,拄着地勉强坐起来。
一瞧,只见整个主巢鳞粉漫天,到处是拍翅乱窜的兵蛾、工蛾。模糊的视野里,他瞥见前面不到两米的地上,有条银蛇在扭动!
他悚然一惊,挣扎着站了起来,定睛一看,原来那玩意儿不是蛇,是蛾后的口器。
口器在地上瑟缩、翻卷,速度很慢,已经丧失了攻击能力。
他走过去,发现这不是整根口器,只是四五米长的一截。口器尖细的一头粘着些蓝色果冻状的东西,另一头是个断口,正往外渗红浊的液体。
肯定是靳风把这玩意儿削断了,才救命了他一命。
不然,他现在已经“肝脑涂壁”了。
隔着雪雾烟瘴似的鳞粉,他转身四顾,想看看靳组长在哪儿。
这时,两只兵蛾突然朝他俯冲下来,他愣了一下,立刻站定不动。
一只兵蛾飞到他胸前,弹出黏糊糊的口器戳了戳他痛不可耐的左肩。它油亮的绿松石色的复眼表面映出了他的脸,它手掌大的叶形触角在他下巴上扫了一下。
叶明瞻又痒又恶心,差点忍不住伸手去挠被触角蹭过的地方。
另一只兵蛾飞到他左边,口器在燃料筒上戳得咚咚响。
他还是纹丝不动。
什么意思?他心里纳闷,老子可穿着你们同伙“盖过章”的纱衣!
之前,兵蛾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现在怎么突然拿他当贼似的“搜身”?
是因为蛾后刚才跳“搅拌舞”时发出的信息素吗?虽然他穿着“盖过章”的纱衣,可外形跟它们的茧实在天差地别。在蛾后发出“护驾”信号的非常时期,气味正确,但外形不对的东西也被列入必须找出来干掉的“攻击源”范围了?
他们的纱衣也失效了吗?
他自己的倒还说不准,靳组长的却肯定失效了。
兵蛾“搜查”他的时间里,他一直透过飞扬的鳞粉不停用眼睛找靳风。
现在,他找到了。
削断蛾后的口器,救了他一命的靳组长,此刻已经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身上那纱衣显然已经毫无作用。
就在叶明瞻左后方三十米开外,断了半截口器的蛾后那粗大的肉粉色身子转了九十度,打横趴在他们进来那个腔洞正下方。
蛾后头顶冒火——不是形容,她脑袋上那块蘑菇状肉垫确确实实在往外喷火。在鳞粉尘暴里,这团火焰看起来就像一盏飘摇的风灯。
她肉粉色的庞大身躯则像艘失火的战舰,这一团,那一团,冒出混着黑烟的火焰。
即便如此,这丑陋的蠕虫仍旧没有完蛋的迹象,还在那里精气神十足地攻击靳风。
她高昂着着火的脑袋,把靳风堵在一处凹陷的洞壁前,彪悍的上颚一次次朝靳风咬去。
这丑八怪还有帮手——她用信息素召唤来的十七八个“保镖”,正配合她的攻势,从不同的方向朝靳风扑,有的吐出口器想扎穿靳风的胸膛,有的龇着上颚想咬断靳风的喉咙。
靳风左躲右闪,挥着军刺抵挡,明显已经力不从心。
即便力不从心,这家伙却还是有本事瞅准空子,一军刺削过去,削飞了蛾后左边的上颚。
蛾后咆哮一声,用冒火的大脑袋撞向他。
他往左一闪,蛾后的脑袋撞在冰壁上,撞得冰块、石块山崩似的滚落下来。
靳风逃过一劫,左臂却叫一只兵蛾结结实实啃了一口。他一军刺撩过去,这只兵蛾顿时身首异处。
兵蛾的身子扑棱着掉到地上,上颚却还牢牢钳着他的胳膊。
他一把扯下兵蛾的脑袋扔掉,顺手挑飞了另一只扑向他的兵蛾。
叶明瞻看得心急火燎,拔脚就朝那边跑。
他一动,在他身前盘桓的兵蛾叽一声尖叫,左边绕着燃料筒打转的兵蛾立马张开钢剪似的上颚,咔嚓一声,在燃料筒上剪出道口子。
一股浓烈的汽油味飘到叶明瞻鼻端。
他心脏狂跳,边跑边扭头看……该死!燃料筒破了,宝贵的汽油汩汩流了出来。
汽油味刺激了周围的兵蛾,它们纷纷刹住翅膀,扑向叶明瞻。
他加速狂奔,右手扯过火焰喷射器的喷嘴。
他能听出有不少蛾子拍打着翅膀追在自己身后,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外周蜜场里那个倒在他面前的被兵蛾从枕骨下扎进口器,吸干脑髓的特勤队员……
兵蛾之所以没像袭击那些人一样,用光速扑到他身上来,是不是因为障月寒纱多少还起着点儿作用?它们还有些迷惑,不能完全断定他就是攻击蛾后的“坏蛋”?
想到腔洞里那些被消化酶溶解得水当当的尸体,他觉得腹部好像叫一根冰凉的钢丝绞紧了,恐惧像油一样漫上胸口。
可他一次也没回头,更不打算把所剩无几的宝贵汽油浪费在这些追击者身上。
他绕过地上那个蓝幽幽,直径朝过五米的通往茧巢的腔洞,直奔被堵在那处凹陷的洞壁前的靳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