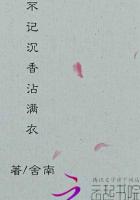白止,我的夫君。他非名门望族出身,也不是什么盖世英雄,更不是江湖草莽,他就是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普通到值得携手白头的人。
———陈忆笙
父亲为母亲在后山的竹林中修建了一座竹屋,父亲母亲走之后我就一直居住在那里。
十年间,我没有想过要下山,除了偶尔为我送来御寒衣物的舅舅一家,我没再见到过任何人。
我不喜欢村子里面的人,村子里面的人同样也不喜欢我。
母亲走得早,我出生没多久后母亲就撒手去了,在我六岁时父亲也去了。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个煞星,他们认为是我克死了双亲。
所以在舅舅收留我时我就坚定地对舅舅说:“舅舅,我不会住在村子里。”
舅舅喝茶思考了一阵子,走到我身边,摸着我的头,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末袖侄女儿,你若是想住在后山的竹林中舅舅绝不拦你,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就跟舅舅说,舅舅一定会帮你的。”
我谢过舅舅,自此一人在山中独居了十年。
寒暑交替,岁月匆匆,门前的那棵老树上的叶子不知道已经枯萎了几次。
时间在翠竹的身上慢慢逝去又慢慢浮现,转眼十余年过去了,我也已长成了大姑娘的模样了。
为此舅舅曾有意为我说上几门亲事,舅舅认为既然我的父母亲已经去了,作为我唯一的亲人舅舅有义务为我寻一门好亲事。
十里八村的没有个几千户人家也有个几百户人家,可就是没有一户人家要娶我,不知从何时开始十里八村的都传开了说我是什么天煞孤星,不仅克父母还克自己的夫君,谁家要是娶了我呀必然没有好日子可过。
舅舅为我的亲事在媒婆那里前后奔走了几十次,终是无果。
舅母将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只是微微一笑,将手中的茶递给舅母,“只不过是下了一场不紧不慢的小雨,没有什么好值得担心的。”
舅母将手中的茶随手放到桌面上,嗔怪道,“你这丫头,这关乎着的可是你的人生大事,身为你的亲人舅舅舅母怎么能不替你担心。”
舅母说的在理,他们二老身为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确确实实为我费了不少的心,只是有些事情不是想急就急的来的,它需要慢慢等待急不来。
“任他们说去吧,没必要为他们的话苦恼。毕竟我们的身上有嘴,他们身上同样也有嘴。”
“我只是怕,,,”舅母终究还是没说出来。
“没什么可担心的,大不了末袖自愿削发为尼,长伴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嫁不出去了,我情愿削发为尼也不愿做一个老姑娘为舅舅一家招来嫌话。
到那个时候那些人又该怎么说呢?到时候他们一定会说,“你瞧,她就是个天煞孤星,注定没人疼爱,只能孤独终老,唉,你说像她这种绝命的人如果削发为尼会不会饶了佛祖的清净,到时候佛祖怪罪下来了可怎么办呀?”
舅母听我说完这句话后立马变得不安起来,仿佛她坐着的不是椅子而是钉子,“末袖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你是你父母唯一的孩子,是他们血脉的传承,倘若你削发为尼,你叫舅舅舅母百年之后如何去见你的爹娘。”
我笑着说:“舅母不必担心末袖只是说笑而已,舅母不必放在心上。”
一句戏言,半真半假,可信可不信。
“你这丫头说的戏言竟这般的真,舅母老了,还真就信了,你且记着这样的戏言以后万万不可再开了,传出去总归是不好的。”
“末袖谨记。”
不知何时风里夹带着茉莉花开的声音,香气由远及尽。记得自己并没有种过任何一朵花,微风徐徐,芳香自来。
送舅母离开后,天的那边又多了一抹胭脂红云,远远望去像月老手中的一根红色丝线为迷路人引着方向。
夜已深,窗外传来脚步落在枯叶上的沙沙声,我惊觉起身,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放在床边的那一把剪刀上,“是谁在外面?”
窗外无人回应,只有知了在树上寂寂鸣叫的声音。一声又一声,在寂静的夜色里显得有几分悲戚。
我又大声问了一遍,心因为受了惊而突突地跳着,“是谁?”
纸糊的木窗上映出一个修长的身影,只听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传来,“小生独自出游,未曾想竟迷了路,路过此地见还有灯亮,便前来询问出路,劳烦姑娘为小生指一条下山明路。”
“公子出了我这竹门,左转一直走,你可以看见一棵古榕树,绕过那棵古榕树一直走你就可以离开这座山了。”
“小生还有个不情之请,小生的灯快要熄灭了,请姑娘赠我一盏灯好照亮前路。”
“你且等着。”
我穿好衣服,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纸灯笼,打开门将那只灯笼递给他,“夜里蛇虫多,公子小心些。”
那公子一身青衣,头发以竹簪束起,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茉莉花的香味,天边的一轮明月散发出如琉璃般的柔光。
不知是哪处神仙的画作竟遗失到了人间?
少年淡淡一笑,我听见了花开的声音,“多谢姑娘,小生白止,姑娘今日之恩,他日必当重谢。”那人转身便隐入一片月色之中,他走后我这院子竟还残留着些许茉莉花的气息。
你的微微一笑很倾城,任谁都不会忘记像你一般一个拥有花开声音的少年郎。
白止,白止。我在心中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
也许琥珀凝结需要经过千万年,但是爱上一个人却只需要一瞬间。从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就知道,这个人,注定会成为我的夫君。
后来,他果然成了我的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