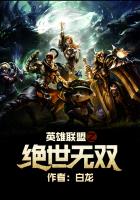一年关难过
过了腊八,乡村的忙年活儿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人们把这段繁忙的时间叫做年关;年关是穷人最难熬的日子,没有吃的,揭不开锅,肚子饿得发慌;没有烧的,家里冷得像冰窖,身子冻得哆嗦。欠债,债主进门逼债;欠租,地主上门催租。还不上债或交不起租的穷人被逼得卖儿卖女又卖妻。穷人在人生的苦海里挣扎。每逢年关,神州大地新坟急剧增加。富人的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洋溢着欢天喜地迎新春的气氛。
然而,这一年,柳家大院的气氛却不比往年热烈欢乐,隐约飘着一种难以言明的阴霾。
历腊月二十三日是小年,这一天,僻静的乡村开始热闹起来,家家户户的门上开始出现大红对联;鞭炮声彼起此伏,鸣响不断;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
然而,这年的小年,柳员外一家人过得并不如意。
吃午饭的时候,柳员外手里端着水烟袋,慢腾腾地走进了餐室。
椭圆型褐色餐桌上,摆放着光灿灿的银质餐具。
三房太太已各就各位,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光彩照人,人人身后站着自己的鲜花般的丫头。她们低声说着家常套话,见丈夫进来,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抬起头用笑脸迎接。三张微.笑的粉脸看去像三朵绽开的山丹丹花,散发着浓烈的粉黛香味。然而,他却阴沉着脸,默默地坐在首席位上,皱着眉头瞟了她们一眼,目光里现出无趣和烦躁的混合神色。
刘夫人扭过头向身后站着的丫头小英说:“去告诉厨娘上菜!”
说话间,美食摆满了餐桌,热腾腾香喷喷,让人垂涎。
太太们望着美食,闻着香味,眼里露出愉悦和贪欲的混合光芒,文雅地伸出舌头舔了舔红唇。
然而,员外却神态淡然,面无表情,默默地坐着,一袋接一袋地抽水烟,若有所思地望着面前袅袅飘浮的烟雾出神。他不拿快子,所有在座的人都静静地坐着,脸上挂起不耐烦的神情,微微低着头,好像都变成了泥塑像;她们心里却不停地翻腾着,猜测着丈夫的心思。一时,餐室的气氛变得无聊又紧张,时间好像突然凝固了,空气仿佛越来越稀薄,氧气越来越少,她们都觉得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儿。
餐桌上的饭菜热气越来越少,空气里飘着让人垂涎的香味也越来越淡。坐在他身旁的刘夫人侧过脸望着丈夫,柔声说:“耀祖他大,吃吧,饭菜快冷了。有啥事儿,吃完饭再说。”她的话打破了沉默,众人慢慢地动了动身子,脸上出现了表情,好像泥塑像突然有了生命。
旧时,中国大家讲究的庭用餐时,一家之主拿起筷子,开始用餐之前,其他在座的人都不能去拿筷子。这种文明的餐桌文化至今还在聚会上和讲究的大家庭里能看到。
员外好像没有听见夫人的话,继续呆呆地坐着,好似一尊没有感情、冷冰冰的石像。
他在想心思。方才,管家孙貌向他报告的消息,在他的脑际萦绕:
他从书房出来,正往进餐室走,不料管家慌慌张张地向他走来。没等他问,管家就说:“不好了,夜儿个后半夜,我们城里的两家店铺都被叼将抢了!”
员外听了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停下脚步反问道:“你说啥?”
“昨天夜里,我们的两家店铺被土匪抢了!”
“消息确切吗?”
“确切。送信儿的伙计在账房等着见您?”
“损失大吗?”
“不小。估计连物带现金损失约五六千大洋。”
“店员们没事儿吧?”
“没事儿,只是惊吓了一场。”
“你去安顿他用饭。我吃完饭就去见他。”
“噢。”管家应了一声,转身离去。
……
三位太太还不知道店铺被抢的消息,当然就不知道丈夫的心思,都以为他担心儿媳妇的病,还在生儿子的气呢。
刘夫人主动地说:“耀祖媳妇儿的病好了些。你别担心。先吃饭吧。”
员外觉察到,夫人说这话时,目光透出了担忧的神色。这说明儿媳妇儿的病情没有好转,只是为了不让他担心,才说“好了些。”于是,他问道:“大夫咋说的?”
“说她的病是从气上得的,肝火太盛,血气凝结。又给开了五副药,吃了看看吧。今儿一早,我让孙管家打发人进城抓药去了。估计半后晌就会回来。”
员外“噢”了一声,接着问:“耀祖哪儿去了?还不来吃饭?”
刘夫人回答说:“刚才我去看过他,他在书房的椅子躺着,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把他叫醒,让他吃饭,他说不想吃,说身子不大舒服。别管他,随他的便。这半年,他在书院刻苦念书,够累的。让他好好歇息歇息。”
“他回来十来天了,该歇过来了吧,还累?。”
“在书院起早贪黑地念了半年书,咋不累呢?他的身子是肉的,不是铁打的。”刘夫人语气里透出对儿子的心疼,对丈夫的不满。
员外皱了皱眉头,用责备的口气说,“你把他惯怀了。”
“我咋惯他了?”刘夫人眉间倏地皱起了两道竖纹,不高兴地说:“那你去把他拉来!”
二房和三房对视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兴奋和鄙视的混合神情。
员外没有反驳,他知道再说下,夫人会大声吵起来。要单独和她在一起,她咋吵都可以,说啥不好听的都行。可是这会儿,在餐室里,二房三房都在场,还有丫头们和厨娘,而且今儿又是小年,吵起来,影响不好。他沉吟着,不出声,放下水烟袋,拿起筷子开始用餐。
接着,刘夫人拿起了筷子。
接着,二房和三房几乎同时拿起了筷子。
大家低着头,默默地用餐,发出微弱的咀嚼饭菜的“吧唧吧唧”的声响。
二耀祖装疯
柳员外和管家一起坐着马拉轿车,去丰同县城处理了店铺被抢的事件,决定暂时关门,留下看门的人,让其余的伙计们回家过年,等年后再择日开张,
腊月二十八早晨,柳员外的轿车驶出县城东门,行驶在通往太平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车轮和马蹄掀起的尘土,漂浮在车后,像一张巨大的灰黄色幕布,遮住了半边天空。。
轿车里,孙管家和员外并排坐着,低声交谈着。
员外问:“地租收的咋样?”
管家说:“截止前天,收上了不到六成。其余的估计年前收不上来。”
员外一听,一股无名怒火向他袭来,立即沉下脸,责备道:“你咋不早跟我说?”
“本来打算前天向您详细地汇报,可是,店铺出了事儿,您够忙的。我就暂且搁下了。”管家低垂着眼睛解释道,脸上挂着谦卑的神色。
“我记得去年这时候,我们全部收上来了。”员外的脸色渐渐变了过来,说话的语气缓和了几分。
“您记得对。”
“那咋闹的,今年不如往年?”
“今年七月下的那场雹子,打坏了好几个村的庄稼。佃户们只好改种荞麦。可是荞麦在开花时节,又遭到了冰雹袭击,因此收成大不如往年。不少佃户的日子不好过,有的已经揭不开锅了。”
“你的意思——”
“今年很难把租子全部收上来。”
“你打算咋办?”
“尽量多派人下去催交。”
“看来得采取些措施。”
“您的意思是,必要是来点硬的,是吗?”
员外没有回答,但管家从他脸上的神色,领会了他的意思——采取强硬措施,逼迫佃户们交租。
近日来,里里外外发生了不少不愉快的事儿,弄得员外焦头烂额,身心疲倦。他闭起了眼睛,很快打起了呼噜。
腊月的天气滴水成冰,西北卷着残雪和尘土呼啸着,搅得天昏地暗。枣红马拉着轿车,顶着大黄风吃力地在崎岖的路上奔跑,不住地打着响鼻,喷着团团白色的热气。穿着白茬皮衣皮裤、戴着黑狗皮帽子的驭手,跨在车辕上,扬鞭催马,嘴里不住地“吁吁!”的吆喝,眉毛、胡须和帽耳的边缘毛上挂了一层厚厚冰霜,看去像童话里的人物。
好像轿车突然停了下来,员外撩起帘子看了看,发现轿车停在旷野上,马和驭手不见了。他感到莫名其妙,非常纳闷,自语道:“这是啥地方?是咋回事儿?”正要下轿子看个究竟,突然从地里钻出一群衣服褴褛的人,手里握着铁锹靶子,嘴里不停呼喊着什么,围住了轿车,用愤怒的目光瞪着他。一个身材粗壮的汉子向他挥着拳头,大声嚷嚷,可是他一句也听不懂,好像置身于异国,心里十分害怕,仗着胆子问:“你们都是啥人?”
那群人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是你的佃户。”
一听是佃户,员外胆子大了起来,接着问:“你们想干啥?”
“我们交不起租子!”
“交不起也得交!”
“你要把我们逼到死路上,我们先让你死!”
众人几乎同时举起铁锹和靶子,向他袭来。他大声呼救:“救命!救命!”
坐在员外身旁的孙管家正在打盹儿,被惊得激灵了一下,伸手轻轻推了推他,说:“醒醒!醒醒!您在做噩梦吧?”
员外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心咚咚地跳了半天,才平静下来。他没有应答管家,开始琢磨着这个梦。他突然悟到,这个梦是天神警示他,心想:“要是对佃户们逼得太甚,他们说不定会抱起团儿来反抗。官逼民反是常事儿。绵羊急了,还会顶人,何况人呢?我的先辈都没有和佃户发生过冲突,在佃户中留下了好名声。父亲信佛,临终前叮嘱我说‘要练就一颗慈悲的心,对佃户要宽容。相信因果报应。’常言道,和气生财。这是我柳家发达兴旺的重要原因。”想到这里,他对管家说:“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收租子的事儿。要尽快地收上租子,但方式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激化我们与佃户之间的矛盾。对确实交不起的佃户,我们不要逼他们,欠着等有了再交。”
管家赞成道:“你说得对。我回去和下去收租的伙计们好好合计合计这码事儿。”
马拉轿车驶进柳家大院,停在了当院,管家先从轿车里钻出来,伸出双手扶着员外下了轿子。
听说员外回来,家人和佣人们立即出来迎接。员外向大家扫了一眼,看见二房和三房都在,却不见刘夫人、儿子和儿媳妇儿,感到事情不妙,以为儿媳妇的病重了,一种无名的惆怅突然向他心头袭来。他走过去把淑云拉到一边问:“耀祖媳妇没事儿吧?”
淑云说:“这几天好多了。”
员外听了,长出了一口气,接着问道:“咋不见耀祖和他妈?”
淑云慢悠悠地说:“昨天上午,耀祖突然光着膀子,跑到院子里,又唱又跳,又说又笑,又哭又闹,折腾了半天。人们费了很大周折才把他弄会屋子。这会儿,他们母子俩在屋子里……”
仿佛突然听见了晴天霹雳,员外感到十分震惊,脑袋“嗡”的响了一声,几乎昏厥过去,没等淑云说完,就疾步向刘夫人的屋子走去。
前天下午,刘夫人进书房对儿子说:“你媳妇儿的病吃了汤药很见效,她能下地走动了。我看你明儿回去睡吧。”
耀祖心里不情愿,但怕母亲生气,答应道:“我听您的。”
刘夫人见儿子听她的听话,兴冲冲地离去了。
母亲走后,耀祖开始琢磨着不回去睡的借口,他想:“离家出走?不行,不行。冰天雪地的年根儿,无处可去。去躲到附近同窗家去?也不行。他们很容易找到我,而且,大年时节的,不能打扰人家。装病?要是装病,他们又要请大夫来看,让我喝苦死人的汤药。无病喝汤药,真是自找苦吃。装啥病能拒绝吃汤药?”他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在地上团团转。突然仿佛耳边响起一个声音:“装疯!”他跟着重复道:“装疯!”他感到很震惊。这是谁在说话?他向四周瞅了瞅,书房里没有别人。于是笑着自语道:“这是我的心和我说话,是天神叫我的心告诉我这个办法。妙哉!妙哉!”接着他绞尽脑汁想如何装得真切,露不出破绽?一边想,一边默默得表演。他感到很好笑:自嘲道:“我竟然变成戏子了!”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反复的练习疯子的行为语言,直到自己认为,装得很自然,不会露出破绽才结束。这样,才有第二天上午让人惊悚而担忧的表演。
这会儿,他在母亲的炕上闭着眼睛躺着,听说父亲回来了,一骨碌爬起来,跳到地上,光着脚一边舞蹈,一边大声说唱:“一个蛤蟆四条腿,两张嘴哇哇!呱呱!两个蛤蟆一条腿,三张嘴哇哇!呱呱!哇哇!……”
刘夫人正穿外套,准备出去迎接丈夫,见儿子又闹腾,赶紧放下外套,去制止,拦腰抱住他,哄着说:“听妈的话,别闹,别闹,上炕好好躺着!”她的哄劝反而使他闹腾的更厉害了。
正闹腾着,门突然被推开了,员外出现在门口,他用惊疑的目光,看着儿子闹腾。儿子好像不认识他,扭过头去,瞟了他一眼,继续说唱:“蛤蟆,蛤蟆,呱呱!哇哇!呱呱!哇哇!呱呱!……”
员外站在门旁,用惊疑的目光观察了一阵子,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