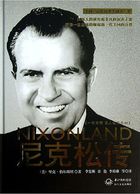见此情此景,女孩暴怒,一个箭步跨到,手中弯刀直刺黑猡,黑猡旧力未收,新劲未发,哪里还有余劲躲避,只得闭眼等死。
眼见刀尖刺入胸腔,女孩却将刀尖倒转,刀柄一拐,击撞黑猡腋下,黑猡双臂立时僵住,再也不能动弹,失去了攻击能力,瘫软在地上。
女孩伏下身子,一把揽起狐猴的头,狐猴最一口气徐徐吐尽,眼睛一闭,脖颈软塌塌地耷拉下去。女孩扑通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林立赶到,一脚踢在黑猡额头上,黑猡哼了一声,手脚一伸,便昏死过去。
女孩悲痛欲绝,泪涕横流,极为伤心。
林立在河滩掘了个深坑,埋葬了狐猴。
女孩对着坟头又是一阵低泣,自念道:“幸亏你,一路陪我,要不……”又抽泣道:“你都跟我十几年了,我一直把你当作家人,现在你不在了,我一个人……会想你的。”
女孩哭得哽咽悲恸,林立听着也跟着一阵阵心酸。
女孩拭干泪痕,将黑猡拉到狐猴坟前,用弯刀拍拍黑猡的脸轻声道:“说吧,是谁派你们来的?”
黑猡双眼圆睁,呲牙咧嘴,口中嗬嗬有声,其情甚是骇人,却不回答半个字。
林立奇道:“他们会说话?”
女孩道:“大多都会说一点人语。”
林立道:“可是,自始至终也没听他们讲过一句话。”
女孩道:“黑猡是一种没有畏惧,不怕疼痛,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只忠于主人的杀手。他们一旦接到命令,执行任务时极少说话,是怕泄露什么机密。”
女孩伸臂扬手,出掌如风,啪啪两下,扇在黑猡脸上,黑猡只是冲她呲牙耍凶,却是咬口不吐一字。
女孩讥笑道:“哼,知道你们这群家伙个个都死忠,看我怎么折磨你。”
女孩用刀尖在黑猡的腋下划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立时流出墨色的血来,散发出阵阵扑鼻的腥臭。
林立不知她要做什么,又不便多问,静静地立在身后。
草丛中一阵梭梭声响,爬出一队巨鳌红蚂蚁来,它们闻到血腥,霎时倾巢出动,成千上万只密密麻麻,将黑猡团团围住,伸出长长的锯齿的大鳌,又凿又剌,嗤嗤有声,上下齐口,噬咬吸啄。
片刻之后,黑猡全身血肉模糊。
黑猡又被女孩点了穴道,动弹不得,翻转不动,只是张牙舞爪,手脚痉挛一般,身体一纵一纵抖动,嘴里嗬嗬呼呼,含混不清,却是强忍硬撑,也不求饶。
女孩喝道:“你说不说,到底是受谁指使?”
黑猡索性牙关紧绷,连呻吟声都不再发出。
女孩冷笑道:“哼,还怕你不开口?”将短刀逼在黑猡额上,轻轻虚划两下。
黑猡倒是硬气,双眼一闭,任她威逼,干脆不再挣扎动弹,上下两排牙齿紧扣,便是钢钻难凿。
林立见他如此执拗倔强,内心竟生感叹:“世上竟有这般忠于主人的杀手,真是罕见。”
林立向女孩问道:“这是些什么人?人不****不兽的,比老虎野狼都可怕。”
小寻道:“你难道没听说过?绝对忠于主人的黑猡杀手。”
林立摇头:“第一次走出昆仑山,没听说过。”
小寻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古老的伊特洛族群,他们生活在的昆仑与天山的深山老林里,用一种古老的法术专门驯服怪兽,把怪兽变成既不是人也不是兽的杀手。”
提起伊特洛人,林立倒是记起,以前听爹爹说过,那是生活在西域一带古老的民族,他们善于冶炼,制造出来的兵器天下无双,羽箭就是伊特洛人发明的武器之一,战国时期,有一支伊特洛族人迁徙到了渭水、祁连山一带,凭精钢羽箭帮助秦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所锻造的武器被秦始皇赞誉为天下精绝,秦封伊特洛人建楼兰、精绝城邦,这也是楼兰城与精绝城的来历,伊特洛人于中原西域之间行商贸易,族人享秦皇帝赏赐,于楼兰一带自成一国。
林立道:“伊特洛人,我倒是听说过,就是楼兰人的先祖。”
小寻道:“不错,他们有几派分支,其中一支习惯在深山里生活,并用古老的魔法驯兽,养成黑猡,奴役使用。”
林立缓缓道:“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残忍的魔法。”
见黑猡以死相拒,女孩怒火更盛,气道:“我就不信还弄不了你?”手腕动劲,短刀横开竖剌,在黑猡额头上划出“王八”二字,立时额上墨血窜流,顺着干瘪的脸颊流下。
林立见女孩手段残忍,竟是看不下去,便劝道:“他虽可恨,你也不必这么折磨他吗。”
若是平时别人用这般手段,林立必定恼怒,激愤喝斥,可是,面对这么一个俊俏慧黠的女孩子,他胸中怒火一到嘴边竟然火爆不起,变成寻常语气。
女孩嘴角一扬,道:“这你就看不下去了?更厉害的招还在后头呢。”
她话未落地,只听嗡嗡作响,从河滩草从里飞来上千只长腿蚊虫,只只硕大,二寸有余,长刺如针,双钳如鏊,一路嗅着血腥,爬到黑猡脸上,钻进皮肉里,一阵刺骨舔血,锯骨吸髓,痒痛交叠。
黑猡实在难忍,一时面目狰狞,喉腔里发出绝望嘶哑的咝咝惨叫声。
直听得林立刺耳钻心,已知黑猡极是难耐。
那黑猡倒是被主人驯养得忠心不二,无论如何难忍,两排白牙只是紧扣不开,连大声呻吟都不发出一声。
女孩道:“你不说就不说吧,我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让你活活流血而死,用不到半个时辰,你也就只能剩一堆白骨了。”
林立见黑猡痛苦难耐,已动恻隐之心,生怕女孩再生出惨酷的手段,便劝道:“好啦,他不说就算了,别再折磨他了。”
女孩怨恨道:“折磨他?这是轻的,他们差点把我害死,要不是遇到你和游侠相救,我早就……哼!”
这时忽听一阵翅羽震动之声,打树丛里又飞来数百只赤头火蜂,见到黑猡便一头扎到他身上,将整个头扎进蚂蚁割烂锯开的伤口及骨髓里。
一顿饱吸,瞬间便吸得尾巴鼓鼓胀胀,墨血黝黑。
再看黑猡,这一会儿的工夫,身体干瘪下去,皮毛千洞百孔,被蚂蚁早已啃噬得像一张薄网,仿佛一张黑网罩着一堆白骨之上。
女孩神色自若,眉舒目展,似乎这种残酷手段于她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