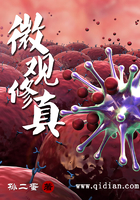御书房内,熙烈皇帝笑盈盈的送走雍王与郎亭集,他手里攒着郎亭集递上来的定州万民书,万民书里的请愿辞较朝会里闻风使的弹劾鲁放的奏章更加生动,但此刻熙烈皇帝已无心对此再做深刻的处理,毕竟“墨陵观风使”的任命已经发出,好在有郎亭集的面子,熙烈皇帝当即令户部拨付定州库银十万两,以资修建墨陵,料想经此一来,鲁放断不会竭泽而渔了。
熙烈皇帝之所以此刻面带笑意,原因是郎亭集应承了他的邀请,会在墨陵竣工时随同熙烈一道北巡,此举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也不为过。
雍王搀扶着郎亭集从禁宫的玉阶一路行出皇宫,待走出戒备森严的玄武门之后,雍王方才轻声一叹,郎亭集寿眉一皱:“雍王,何出此叹?”雍王回望玄武门后巍峨的观天台,半晌才道:“大宗递的万民书与朝会的折子相互印证,摆二十年前,剥皮充草是鲁放的唯一出路,可是现如今,唉!”熙烈皇帝治吏素以严苛出名,这多年来折在他峻法之下枉法的皇亲国戚已不下手数了。
“墨陵啊!”郎亭集说道:“卞礼拿大皇子秦墨的旧事重提,阴差阳错了!”,随后郎亭集再不言语,独留下雍王凝神思索他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郎亭集与雍王对谈的同时,熙烈皇帝亦在御书房里开始了另外一场对谈。
“定州出了个天师道北天君,纳凉,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方才面带熙色的皇帝,此刻一脸冷峻的望着坐下的密谍统领纳凉。
“‘问寒问暖’司徒钟,定州人士,师承刀宗景童,鲁侯爷当年爱才将其引入赤蟒军,副将的批文是陛下钦准的!”纳凉回道。
“哦?”天南景氏,以刀立身,现如今的家主正是刀宗景童,熙烈皇帝反问纳凉道:“景氏也卷入天师道了?”
“陛下,景州节度使是景家的庶子景田!”景州在大焱最南端,八年前平景两州大旱,平州被天师道纳入囊中,而紧邻平州南面的景州却岿然不动,只因它最南面的望族天南景氏一力支撑,因此熙烈皇帝方才的问话有些多此一举。
“十年了!纳凉!这十年朕愈发觉出天师道的莫测来!”熙烈悠然一叹,旋即话锋一转:“鲁放是那等竭泽而渔的人么?”
“鲁侯爷自大皇子过世之后,性情便起伏不定,这些年诸多变化,只怕还有他人居中出谋划策!”纳凉回道。
“幕僚?师爷?!”熙烈皇帝反问道:“纳凉,顺着这条线查!”熙烈素知鲁放秉性,心知若无他人作梗,鲁放决计做不出天怒人怨的事来,只怕其中还有天师道的影子!
“那么,木渎桥雍王遇刺,你怎么看?”熙烈端起桌上的茶盏问道。
纳凉说道:“明楼的手笔!军弩虽然烧坏,但铁钉却烧不掉。这批军弩用的是二十年前的旧式钉。我亲自去查看了军作监的记录,十年前禁军有十具军弩报损。”
“哦?”熙烈皇帝闻言一愣:“莫非禁军报损的军弩流出去了?”
纳凉:“陛下难道不清楚军弩的分配么?”大焱的军弩主要配置在八支精锐主力军团里,鲁放的赤蟒军便是其一,此外皇都禁军也有配备。制式军弩一进一出军作监俱有详细记载,而近十年来,只有禁军上呈的十具报损颇有疑点,而这十具用的正是旧式钉。
纳凉继续道:“木渎桥下有一卦幡遗落,密谍司查探下来,此卦幡正是发动伏击的讯号,正合明楼青岬的风格。”青岬,明楼杀手的后起之秀,尝以算师示人,做的却是谋杀伏杀的勾当。
纳凉话里蕴带的含义,让熙烈陷入沉思,半晌,熙烈方才说话,声音肃杀且苍老:“那么,十年前,镰刀镇的旧案也就有眉目了,是这意思么?”
“算是!”纳凉回道。
“还有一件,比较蹊跷!”纳凉说道:“木渎桥上的死尸,表面上看没有明显伤口,实则脚踝处都有一微不可见的咬痕,似是毒物所为。”
品茗了一口香茶,熙烈皇帝笑道:“看来今年的春宴,将会比往年更加精彩!纳凉,你须为朕好好准备!”
“陛下!”纳凉说道:“您将《太学笔记》赐给了郎大宗新收的弟子?”
“有问题么?”熙烈皇帝瞟了一眼纳凉:“郎大宗在赤龙山下收到的弟子,与朕很有缘分哩!”
纳凉欲言又止的模样被熙烈看在眼里,熙烈大手一挥,笑道:“莫要多想,此事朕自有区处。”
郎亭集自皇宫回到直湖精舍的时候,门房递给他一张烫金的帖子,翻开一看,竟是四皇子秦彻的请帖,一通花团锦簇的客套言语之后,才显出真正的目的,明晚,秦彻欲在皇子府邸盛宴郎亭集一行。
郎亭集看罢,摇头一笑,对那殷勤的门房说道:“再有这等帖子过来,劳烦替老夫回了。老夫先要参加大皇帝的春宴哩!”郎亭集不着边际的话让老实门房摸不着头脑,正在此时,内屋的曹容闻声跑了出来:“老师!你总算回来啦!秦律欺负我呢!”
“哦?”郎亭集见曹容换了一身衣裳,不禁问道:“律儿如何欺负你了?”
此话一出,曹容哑然,白皙的小脸重又变得红扑扑起来,郎亭集见状便不再追问:“律儿他们呢?”
“秦律在熊叔屋子内耍,柔姨出去逛街花钱啦!”曹容回道。
阿柔当然在逛街,此刻她身着一件黛色的衣裙走在皇都的大街上,就如一位寻常人家的小媳妇。她手上提着一路买来的蜜饯,点心,看模样似是走累了,正欲找个歇脚的地方,此时斜对面的茶摊那传来一声淳朴的招呼:“阿妹,我在这里哩!来饮茶!”迎面望去,李井松正穿着一身绸坎肩坐在茶摊外围的木桌边!
阿柔眼睛一亮,嫣然一笑:“大表哥!”说罢便熟络的坐到李井松的茶桌旁。刚刚采办的蜜饯被拿出几份来摆到了桌上,外人一看,还道这位表妹如此贴心,在这样的氛围里,阿柔与李井松开始了交谈。
“这趟路难为你了,吃些点心。”阿柔瞅着李井松风尘仆仆的模样,心里生出些歉意来。
李井松倒也不客气,一把抓了只蜂窝糕团便塞入了嘴里,边嚼边道:“嘿嘿,倒也真是饿了!”
“码头上的事情你做的不错!”阿柔毫不吝惜夸奖,当日若不是李井松的浑水摸鱼和牛倌阿江的神来一刀,后果当不堪设想,她见李井松一副狼吞虎咽模样,不禁峨眉一皱,问道:“怎的,一天没进食了?”
李井松讪讪一笑:“从家里走得急,带的银两不多,一路下来盘缠花的差不多了。”
“不过不要紧的,到了皇都,俺有的是办法!”李井松露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态来,此时四周也无旁人,李井松压低嗓门对阿柔道:“那位老爷子只怕被南面的朋友盯上了。”
阿柔闻言眉头一跳,右手伸出,对着李井松比出了一个“二”字,李井松重重点了点头——明楼十三重,皇都中州正在第二重楼的势力范围里。阿柔问道:“你如何知晓的?”
李井松回道:“青岬!今日在你们的住处,我看到青岬了!”
青岬,二重楼年青一代的核心人物,阿柔自然熟悉,因此不须多想便可知,木渎桥上的刺杀定是青岬的手笔!
这得花多少银两!阿柔第一反应竟是买凶者请出青岬的花费来,不过这荒唐的念头一闪而逝,随即似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执念涌上阿柔心头,阿柔在第八重楼的地位就如青岬在二重楼一般,他们都是属于种子式的人物,种子是决定明楼十三重楼主的重要因素,因此种子之间必有一战。
此时街面上传来一阵喧哗,二人打量过去,发现从外城方向行来一队人马,打头的是十骑通身黑甲的骑士,面无表情的脸上煞气逼人,一望便知这十骑是军中精锐里的精锐。紧随其后的是一位骑着高大白马,身着重甲的老将,他灰白的胡须与身上亮银的铠甲相映成辉,国字脸上一双虎目透出一股厚重的煞气,腰间配着一把无鞘的长剑,那长剑的剑锋上似凝着一股寒霜,让人望而心寒。
这是?阿柔与李井松对望一眼,这队自外城过来的人马,俨然不是皇都禁军,如此公然踏马进入皇城,这白马上老将的身份非同小可!
此时,茶摊内围出来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人说出了老将的来头:“郑侯!他来喝大皇帝的春宴啦!”
“当朝太子的岳丈,大皇帝的亲家公,好大的气派!”有人赞叹道!
“那是当然,当年郑侯统帅禁军时的威风气,你是没瞧见,可不是上官将军能比的!”
此时,阿柔望向郑侯身上的亮银甲,脑海里不禁闪出太子世子被秦律痛殴时,身穿的那身银色亮甲来。
郑侯,太子秦致的岳丈,原来皇都的禁军统帅,如今坐镇永州的一方大员,在春宴的前几天终于到达皇都,而接下来陆续还会有更多的大焱贵胄、名流齐聚皇都。
阿柔低声与李井松交代几句,随后自袖内掏出一只鼓囊囊的小锦囊放到李井松面前:“大表哥莫要再赌钱啦!”说罢,拿起茶桌上的蜜饯和点心包裹,便依依的离开。
众人不由的羡慕起茶桌边看似窘迫的李井松来:“乖哉!滥赌,还能有表妹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