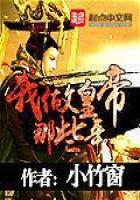赤龙山南麓,山脚下,一条狭长似镰刀的山谷里,坐落着方圆百里唯一的小镇——镰刀镇。
镰刀镇因其位置的特殊,在这相对平静的五十年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如今俨然已成了两国民间通商的纽带。当然,这种通商不会得到官方的肯定,公然的通商,必将遭到官方激烈的反应,因此行走在这条商道上的要么是刀口舔血的单帮客,要么就是背后有通天背景的豪客。而作为民间私下通商的纽带,镰刀镇同样也是两国密谍交错的情报必争之地。
原先镰刀镇的居民以赶山的原住民为主,而今,因看到商机而举家迁徙到镰刀镇做生意的人,亦不在少数,如今镰刀镇的不少好生意都让外来户做了,譬如镇上的福记车行,一家客栈,东西典当等等。
清晨的镰刀镇,并未因冷冽的北风变得冷清,镇外一座高大的木栅栏上依旧留着新年的喜气,两只大红灯笼悬在栅栏两边,一条青石板路从栅栏旁,直通到镇里。栅栏旁的空地上,卖早点的生意人已经陆陆续续的支起了摊位。镰刀镇的早点以种类丰富,价廉物美而出名,这里有大焱定州的高粱饼子,梁州的驴肉火烧,雍州的油条串子,北漠特产的羊**早茶,羊肉夹馍等等,各式各样,应有尽有。
等到正月年节过了之后,北漠的积雪才会慢慢消融,商路才会通畅些,因此镰刀镇里滞留了不少客商,新年里旅居在外,无非吃喝玩乐而已。
故而,早点摊子前面,陆陆续续的会有三三两两的食客,而历来生意最好的郑记驴肉火烧前已有不少食客在等候。
两位食客,正一手拿着火烧,一手拿着碗豆浆,蹲在摊位旁边的青石上边吃边聊,而青石旁边的木桌上,则另有两位也在慢条斯理的吃着早点,这四位一望便知,蹲着的来自北漠,坐桌头的来自大焱。北漠天高地大,幕天席地,民众风俗粗犷,能蹲着绝不坐桌头。
北漠的食客,嗓门自然大些,一大早便聊些头晚在镇内清水楼的趣事,而大焱的食客则一边慢条斯理的嚼着火烧,一边倾谈。那位络腮胡须长满圆脸的北漠粗放客,正说到兴头上,言语里那清水楼的头牌已被他像剥粽子一般捋去衣裳摆上了月牙床,旁边不少故作正经却又屏息细听的食客正等他说下文的时候,他居然又不说了。
“咿呀!”半晌,那汉子发出一声惊呼:“大早上的,莫不是见鬼了。”只见他双目圆瞪,嘴巴长的老大,火烧的碎末掉在胸口浑然不觉,众人顺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一瞧,还真是见鬼了!
只见不远处的雪道上,四位黑衣轿夫正抬着一个大红色的轿子,朝着镰刀镇缓缓过来……
清晨,赤龙山脚下,方圆百里的大雪地里,大红的轿子,这景致连在一起,实在诡异,有谨慎的食客,放下手上的早点,用手轻抚腰间,确认防身的武器是否贴身。而在镰刀镇已经做了将近四十年火烧的郑二,将一屉火烧放入火炕之后,亦愣愣的望着这景象,周遭有食客问:“郑二!在镇口卖了这么多年火烧,可曾见过这景象!”郑二的瘦削脑袋像拨浪鼓一般,在风中摆动起来。
胆小的食客,纷纷卷走早点,返回镇子。而好事的则留着不走,继续品尝早点,等待不速之客的到来。约莫一碗羊**早茶的功夫,那顶大红轿子便依依的来到木栅栏前面。四位青壮的轿夫,将轿子缓缓落下。
众人望不透门帘,只得先打量起四名轿夫来,只见那四名轿夫,一身水墨色雍州水绸做的劲装短打,二十出头的年纪,四人身材一般无二。出于客商的习惯,食客们各自打起了算盘。
有人惊叹于哪家的富豪能够养的出这等劲仆,有人目测这身水绸的等级来估算它的价位,也有冷静的,在雪地里,这身短打,而不被冻死,这四人远不是轿夫这么简单啊!
正当众人交头接耳的盘算时,冬日的暖阳随着轿帘的挑起,而升了起来。一身大红缎服的女子,着着大红色的锦鞋,就像一团火,出现在大家面前,她藕白色的素手仍挑着轿帘不放,她明媚的笑脸丝毫不逊色天上的暖阳,或者更胜一筹。那女子低身出轿,对着众人,笑道:“大家早啊!”
“娘咧!”那北漠的粗汉,忍不住丢下手中的海碗,一下站了起来,怔怔的盯着那女子,显然是被迷住了,其他人何尝不是呢?——这是要搞事情啊!
那女子不理痴愕的众人,带着一名轿夫,径自行到早点摊前,一一询问风味,譬如咸淡,甜辣与否,片刻便收获了不少中意的早点。有识相的食客,早就让出了一张空桌,翡绿色的绸布被轿夫铺了上去,一张雪熊皮裹着的圆墩从轿内取了出来。早点在桌上摆置好,红衣女子轻轻坐下,安然享受起来。——木栅栏仿佛她家的庭院。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现在不论内行,亦或是外行人,谁也不想轻易招惹这位凭空出来的红衣女子。镇内的客商都是聪明人。
可世上,总有不识相的人,譬如那女子一只火烧恰要咀完的时候,又来了一行客人——他们也是从镇外的雪道上来的。
三辆雪橇车在一群角鹿的牵引下,由远及近,片刻便到了木栅栏下面,角鹿起伏的嘶鸣声让镰刀镇外的早市变得更热闹。可交谈的声音却变得少了,方才嗓门震天的北漠粗汉,将火烧强塞入口里,鼓囊囊着嘴巴,早就跟同伴一起溜进镇里。北漠的客商纷纷溜进了镰刀镇,那是因为角鹿的到来。
在北漠,角鹿是特殊的象征,祖神降临到世间,角鹿是他专属的坐骑。北漠的百姓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祖神的庇佑里,他们见不到祖神,因此,只有把对祖神的崇敬、爱恋奉献给祖神的坐骑角鹿了,所以角鹿是北漠身份最神圣的动物了。而此刻由角鹿牵引,雪橇车上的客人应该就是祖神在世间的代言人——祖神殿的祭司。
祖神用乌石垒起了山川和田地,她的汗水化成了奔涌不息的乌玛河,滋润万物的声息,祖神哟,她向撒下万千的种子,种子化成了阿爷,阿姥,阿爸,阿妈,还有我们——兄弟姐妹!——这段北漠流传的民谣里,祖神用乌石创造了世界,而在现实里,祖神则用乌石来区分了祭司的等阶。
第一辆雪橇车上下来六名身着灰色皮甲的大汉,左胸前三块垒在一起的黑色乌石标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祖神殿的三阶黑石卫士。黑石卫士是祖神殿传统的护教力量,而根据实力高低,又分为一到五阶,三阶以上的黑石卫士在世俗界便已是以一挡百的存在了。整个北漠,三阶黑石卫士不足一千,四阶卫士更少,等到了五阶卫士,也就寥寥数人而已。
第二辆雪橇车上下来的是四名身着白色祭司袍的中年人,左胸前亦是印有祖神殿的标志——两块精巧的靛青色乌石。这四人迎向后面一辆车。最后一辆雪橇车明显要比前两辆要大上很多,漆黑的车厢上,雕刻了神秘的祖神殿符号,那玫红色的线条,圆润而又洒脱,显然出自祖神殿神画大匠的手笔。
车厢呀呀的打开,出来的是一位神态睥睨的青年,他丰满的额头下,是瘦削的双颊,双颊下面的下巴,更显瘦削,倒三角的长相却不妨他展现嘴角那一抹轻蔑的笑。他的胸口亦是两块靛青色的乌石,只是衣着比纯白色祭司袍要多出了一些花哨,袖口跟衣领上,密密的绣着金红相间的条纹。四名白衣祭司让过那青年,然后对着后面的车厢,恭恭敬敬的行礼,便不再走动,束手侍立在两旁,车内显然还要有更重要的人物。
那轻蔑的青年,显然有足够的资本骄傲,以过往的生活经验,青年显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识相。
故而,他率性的对着六名黑石卫士挥了挥手,便昂着脑袋逛起了木栅栏旁的早市。不经意碰翻了隔壁的豆浆摊之后,他在羊**早茶摊上接受了那个可怜的北人老板的敬茶,茗了一口之后,“啐”的一声,便吐了出来,显然是对羊**的新鲜程度不满意。他虽然昂着头,却不妨碍他看到木栅栏早市上的那一抹惊艳,他额下的双眼,愈发明亮起来。
六名黑石卫士,随着那青年,径直便到了红衣女子的桌前。
早市上,只剩下大焱来的客商吃早点了,他们目睹了整个经过,现在纷纷望向红衣女子那里,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见两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那女子笑嘻嘻的托着下巴,仰头望着祖神殿的青年,不知在说着什么。几句话的功夫,只见女子的轿夫走出一位迎向青年身旁的黑石卫士,一名黑石卫士轻吼一声,如同一只黑熊一般,便扑向那轿夫。眼看快触到轿夫了,不料轿夫轻便的一闪,便到了黑石卫士的身后,他在黑石卫士后背上轻拍一掌,黑石卫士宛遭蜂蛰,惨叫一声过后,黑石卫士跃到场外,眼尖的食客能看到黑石卫士后背上竟留着一个殷红的掌印。那黑石卫士,仍不服气,双手接天举着,响彻全场的一声怒吼之后,上身的皮甲竟如裂帛一般碎去,精赤而粗壮的上身,可见块垒一般的肌肉如丘壑一般,身形也胀大许多。
吃过一次亏之后,那卫士很快明白了以静制动的策略,再不去轻易扑捉轿夫,而是峙立原地,捕捉轿夫的破绽。所以局势变得僵持起来。
那女子依旧撑着下巴,笑吟吟的看着打斗,说不出的惬意。而那青年,在黑石卫士吃亏的时候,眼角闪过一丝愠怒,待到黑石卫士转变策略,稳定局势之后,轻蔑而暧昧的笑意重又从瘦削的唇边漏了出来,但这种笑意却不能保留很久,顷刻之间,青年削尖的下巴,似被风吹掉下来一般,彻底惊住了。
场内黑石卫士与女子的轿夫,正在对峙之时,骤变突起,那卫士忽然惨叫一声,然后嘴边鲜血四溢,熊一般的身躯,颓然倒下,脑袋重重砸在地上的青石板上,眼看是没救了。
看热闹的食客们,亦被惊到。再望一眼,却见,倒地的黑石卫士身上,自脖子到胸间,一道道黑线,密密麻麻的,自皮肤内若隐若现——好厉害的毒!
顷刻之间的事,青年立马反应过来,他厉声对着红衣女子道:“小娘皮!说好的切磋,你的人用毒了!”眼见同伴毙命,另五名黑石卫士怒火中烧,迅速将红衣女子围了起来,只等青年一声令下。
那女子却不惊怕,对青年道:“好笑的北蛮!你的人学艺不精,打不过就罢了,却还自己带毒来吓唬人,哈哈!”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不过本姑娘手上的人命多了去了,再算上一条也不多,何况还是北漠神棍的!”说罢,那姑娘葱白一般的手指,轻轻指向青年身侧的另一位黑石卫士道:“诺,你也带毒了哦!”
目光望去,那黑石卫士,此刻竟是面如死灰,喉咙间亦有黑丝织缠起来,那卫士仆然倒地。
须臾之间的变故,让那青年和剩下的四名卫士面面相觑,所幸互相端详起来,大家均无碍。
雪橇车那里也发现了这边的变故,一位白袍祭司走了过来。青年见那祭司过来,如释重负,厉声道:“好狠心的小娘皮!木坤祭司!……你要是跟了我就……”那白袍祭司的到来,打断了青年的呓语,他枯瘦的脸上生了一双鹰隼般的双眼,精光烁烁。祭司木坤,俯身查探了倒地的两具尸体,只见他从腰间的囊袋里迅速一掏,一只沙蝎便出现在掌心,那沙蝎迅速的爬上那具精赤上身的尸体上,便蛰在在心口的黑线上,原本暗红色的蝎壳转瞬便漆黑一片,沙蝎也翻身死掉了。
“相思魂断”木坤缓缓起身,沙哑的嗓音道出了剧毒的出处:“南人张甲士的秘毒,绝迹南北二十年了,你是毒伯伯的什么人?”
那女子闻言,笑容愈发灿烂起来,回道:“北蛮,还真有识货的。我说我是张甲士的大侄女,你信么?毒伯伯的名声很响啊,可我都快忘掉了,哈哈!”
木坤凝神望着那女子:“若是张甲士的后人,那你该叫我师叔。”
“哦?”红衣女子此时倒有些诧异起来。
木坤说了五个字:“一毒分南北。”
百年前毒宗奇才姬森,突发奇想,在大焱与北漠各选了五名天赋异禀的少年入门学毒,以残酷的法门炼徒,十年之内,让徒弟按照南北两派用所学互相下毒,直至南北各余一人方才罢休。而幸存的两位徒弟,则各自在大焱与北漠开枝散叶,这便是“一毒分南北”的典故。木坤的话里,应该明了,张甲士与木坤应该分别是,毒宗南北两脉的传人。
木坤指着地上的两具黑石卫士的尸体,对红衣女子道:“你连杀祖神殿的两名卫士,可知后果是什么?”红衣女子浑然不惧,讥诮的望着木坤,反问道:“那又如何?”
木坤干枯的喉咙里难得发出笑声来:“除非毒伯伯亲至,否则你那几手毒术,想必难不住我吧!”话锋又是一转:“若非这两个蠢材大意,又怎会着了你的道儿,镰刀镇是那么容易闯的么?”言语中的许多不屑,不知是征对红衣女子,还是地上的两个倒霉蛋。
似无更多的选择,那红衣女子的朱唇不禁渭然一叹:“唉……”
木坤可不容红衣女子多做考虑,紧接着说:“南北毒宗本是一脉,所以我俩也算是自家人。两名三阶卫士莫名其妙便死了,这不是小事,我也压不下来,好在这次师叔陪侍了一位大人物,在他面前,我一定会帮你美言几句。”
红衣女子的美目中,波光翻转,似被木坤的话感动了,她抿着嘴唇,轻轻地低下了脑袋。
木坤身后那个睥睨的青年,此刻似捡了宝贝一般,他仔细打量着红衣女子的举动,就像赏看一件物事一般。
木坤嘿嘿一笑,干枯的脸上难得挤出一种他认为很和熙的表情,对红衣女子道:“师叔我也有十来年未南行了,不想这次南下竟能碰到同门,也是天大的机缘。你可在此稍候半日,等师叔此间事了,再跟你好好叙旧!”
红衣女子轻轻舒了一口气,似是如释重负,对着木坤强笑道:“师侄在此先谢过师叔了,全怪师侄不知轻重,妄下重手,才误了两条人命。师侄在此,敬候师叔教诲。”说罢,女子轻起身段,随后朝着木坤一行歉然一笑,眼角却有一瞥艳波流转到那青年的眼里,让那青年愈发骄傲起来。
女子重又回到了轿内,冬日里的一团火,在众人眼里逐渐熄灭,剩下的便是半空中惨淡的日头与木栅栏下早点铺子腾空的热气,交相呼应。
木坤似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双手重又缩回袖内,他对身边的青年道:“镰刀镇的早市,十几年前,老哥我吃过一次,味道很不错的,阿伦少爷,我们吃会,填填肚皮。”
殒命的两名黑石卫士被同伴们抱回雪橇车,他们将被带回祖神殿,回归到祖神的怀抱里。
方才的一切就像没发生一般。而阿伦少爷宽额上的双眉愈发的舒展开来,削尖的下巴挡住了自己的喉结,他自在的回应木坤祭司的提议:“好啊!填实了肚皮,还有大油水等着咱吃咧,哈哈!”
这番事故,让早市的生意冷清了不少,郑二搓着皴裂的双手,望着火炕上垒成一堆的火烧,不免有些发愁,这光景已经多少年没见了啊!他望向雪道,却发现打远处又一队人马来了——一辆红漆马车在雪道上甚是打眼。郑二喃喃道:“真是见了鬼咯!”
秦墨一行,因在半路被熊帅阻了一阵,故而到达镰刀镇的时间,比预想的晚了些,但不妨碍他们赶过来吃上热腾腾的驴肉火烧。
秦墨在马上,老远便望到木栅栏上两只红通通的大灯笼——西海试炼,在外两年,这次总算快到家了,镰刀镇再往南一百里,便是大焱定州了!
只是,能否顺利通过镰刀镇,这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