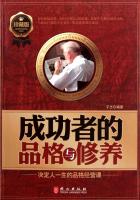从闽月楼步行到景传志租的房子,只要十几分钟;几间很普通的外红砖、内白垩墙的建筑,前后两排,两侧有高高的围墙连接,中央形成了一个大大的院子。前房开药铺,后房住人,院子里放点零散的东西或晒些药材。
从父亲的脸上,景腾知道他对这儿很满意;从父亲的言语中,景腾明白他对孙建凯及邹道奇的帮助充满了感激。景腾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抛开他们对家人的帮助不说,让高进到新兵连锻炼两个月调回做警卫,还不是孙建凯考虑到他和高进的关系了嘛!能做团长的警卫,就意味着可以寸步不离地跟团长在一起;战争时期,指挥官的伤亡比冲锋在第一线的士兵要小得多。有这个想法是自私的,但景腾不是圣人,他必须要为妹妹的幸福着想。
景腾和父亲在前房来回地走着,看着;倚墙而立的大柜子上,一个个写着中药材名称的药橱告诉他,这里以前也是个药铺。
“爹,之前的老板为什么不做了?”景腾问。
景传志答:“老板夫妇年纪大了,他们远在宝岛的女儿不放心他们留在这儿,接他们去安度晚年了。”
“宝岛?”景腾若有所思。
“是的。”景传志答,“这一去,他们此生或难再有回来的一天了!虽说宝岛是华夏的领土,可千里迢迢的还隔着大海,上了年纪的人,想回来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景腾点了点头,问:“明天我把景飞和高进带走,就没人帮你干活了;您的身体吃得消吗?”
“没事,这儿的活也不重。”景传志笑着答,“我的身体好着呢,颜儿和彩蝶也可以帮我;不过看彩蝶的情形,似乎对这行没什么兴趣。”
“人各有志。治病救人本就是个严谨的事,不想做,不必强求。”
景传志笑着说:“我本想让你和景飞继承我的衣钵,看来不可能了。”
“还有小妹啊。”景腾笑着说。
景传志捋着胡子,说:“颜儿还是很聪明的,也能吃苦,倒不失为一个可造之才;假以时日,或许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至于彩蝶,先让她跟着我干些力所能及的,如果对这行实在提不起心思,再帮她找别的事做。”
景腾正想回答,却见景飞探出脑袋,小声地说:“我好像闻到了有人在说我坏话的味道,原来是爹和大哥。你们不睡觉吗?”
“你不也没睡吗?”景腾笑着问,“你做了什么坏事怕别人说?”
“我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做坏事?”景飞眨着眼睛答,“小妹还在我们的房间和高进眉来眼去,我在那儿是个多余的,所以很自觉地出来了。”
“这么大孩子说话还是不经过脑子考虑!你就这样说妹妹?”景传志严厉地训斥道。
景腾笑了笑,问:“明天要走了,怎么不去和彩蝶说说话?到了部队,要三个月才能回来;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一定要哄好哦。”
景飞答:“我刚才在她那儿了。她要睡觉了,我才出来的。”
“我和爹商量,准备把你们的婚事办了。你们有意见吗?”景腾笑着问。
“我们还不想结婚。”景飞小声地答。
景传志蹙着眉头,问:“是你不想结婚,还是彩蝶不想结婚?你是我儿子,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别看你整天嘻嘻哈哈的,彩蝶的心思不一定揣摩得透。”
“她的心并不坏,只是有爱贪小便宜的心理。她也是想我们好。谁能没缺点?我相信她会改的。”景飞说。
景传志说:“占小便宜吃大亏!这习惯会害了她。你们在一起什么话都好说,你可以直接劝,也可以旁敲侧击地劝;忠言逆耳,说了是为了她好。”
“我知道了。”景飞答。
景腾拍着弟弟的肩膀,笑着说:“爹说的都是对的,听爹的;话怎么说?事怎么做?自己想好。”
景飞点了下头。
二
洁白无瑕的蜡烛,纹丝不动地立在桌子上,偶尔向四周摇晃的火焰里,有着两种不同的颜色——包裹烛芯的是一小簇红色的火焰,笼罩在红色火焰外层的,是一团白色的火焰。它们就像亲昵无间的爱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景颜关上卧室的门,倚靠在上面,温柔地说:“过来,抱着我。”
“不行,景腾哥他们在外面。”高进小声地说。
“你怕他们?”
“是尊重。”
“尊重有很多种,对我好,满足我的要求也是。”景颜不依不饶地说。
高进咬了咬嘴唇,深吸了口气,走到她的身边,深情款款地看着她;景颜双手勾着他的脖子,痴痴地和他对望。突然,娇喘着的她将香软的吻,如雨点般落在了高进的脸上……
高进的“无动于衷”,让景颜停止了亲吻;正想着她的高大哥是不是一时半会儿还不适应时,高进已将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柔情蜜意地吻了起来……
默默燃烧的蜡烛,将温柔的光线轻盈地洒满整个房间;房间里的人,就好像蜡烛的火焰,热情地忘记了尘世间的一切!
“早点睡吧。”高进松开景颜说。景颜羞涩地笑了笑,像朵娇艳欲滴的花儿依旧盛开在他的胸膛里,将深情厚爱肆无忌惮地宣泄在恋人的身上……
“我走了。”景颜重新倚靠在门上说。
“嗯。”高进点了点头。
目睹了这一切的火焰,随着门的突然打开猛烈地向一边摆动,产生了想要脱离蜡烛的冲动;只过了片刻,它又随着门的关起镇定下来。如出生于春天里的小草,偶尔被风诱惑着起舞,却从不舍离贪恋的泥土而去。
景颜回到自己的卧室,彩蝶还瞪着两只滴溜溜的大眼睛躺在床上。“你还没睡?”她问。
彩蝶答:“想睡,睡不着。”
“是不是想二哥了?我去帮你叫。”景颜笑着说。
“别闹!”彩蝶娇嗔道,“你以为我是你呀。老实交待,你和高进在隔壁干嘛呢?”
“没……没干嘛。”景颜红着脸答。
彩蝶小声地说:“刚才我去找你,看高进的房门关着,他们爷三都在前屋;我就想这房间里的人在做什么呢?不会是在耍流氓吧?”
“彩蝶姐,我们没有……我们……”景颜吞吞吐吐地急忙解释。
彩蝶笑着问:“没有什么?”
“不理你了。”景颜娇声道。
彩蝶笑了笑,说:“好了,我不问了。行了吧?”
“二哥明天要走了,你怎么不和他说说话?”
“有什么好说的?”彩蝶问,“你说我们该结婚吗?”
“咦!二哥向你提出来的?你要是问我,我肯定说‘该’了。”景颜笑着答。
彩蝶笑了笑,说:“不是我不想结婚,我只是想在我们有孩子之前多存点钱,这样婚后我就有安心带孩子的物质基础了;现在两个人辛苦,总比以后让景飞哥一个人辛苦好。”
“我替二哥谢谢你!”景颜认真地说,“别想那么多,还有我们可以帮你们的。”
“你和高进会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生活。景腾哥也会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传志叔会老。你们的帮助都只是暂时的,与其这样,不如一开始就靠自己。”
看着语气平缓但态度坚定的彩蝶,景颜突然觉得自己从未真正了解她;如果说以前她认为彩蝶太过现实的话,此番彩蝶的一席话,多少改变了自己之前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都有对于金钱名利不同的看法,只要出发点是好的,不出卖自己、伤害他人,孰是孰非,谁又下得了定义呢?
三
高进整理了一下衣服,咳嗽了一声,来到了前屋;和景飞说笑的景腾见他到来,对他点了点头。高进笑了笑,问:“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景飞偷偷地看了一眼在柜子旁翻弄药橱的父亲,小声地答:“我们在商量把你和小妹的婚事办了。”
“别胡说。”景腾轻轻捣了他一下说,“我在交待这家伙到部队的注意事项,我怕他不老实,他的班长会对他大邢侍候。”
高进笑着说:“那我也要注意。”
“也没什么,具体的你们班长会说的。训练是很辛苦,一定要坚持,绝不能做逃兵。”景腾说。
“我记住了,绝不做逃兵。”高进答。
景传志将药橱一个个地打开,里面有药材的,放在鼻子上闻一闻;想认真地看看,却无奈光线朦胧。景腾走到他的身边,说:“爹,时间不早了,早点歇息,明天再忙吧。”
“嗯。”景传志点头道,“这些药材都需要重新打理,能用的先晒一下,不能用的只好扔掉了。走吧,睡觉去。”
第二天黎明,康文玉驱车来到了景传志的住处;给景腾送来了西服、和他嘀咕了一番后,带走了景飞和高进。
康文玉对于景腾,绝对算得上不可或缺的心腹;团里大大小小的事,他只需简单说明一下方向,康文玉就可以非常细致地做到完美。在以前的战斗中,景腾曾有过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康文玉、自己只带上警卫深入敌军内部作战的战例。
遵照景腾的意思,康文玉将景飞划归特务营2连1排1班;因为每天都在超强度的训练,以致该班有“魔鬼班”之称!班长柴洪亮,湖南人;性格火爆,入伍前是个屠夫,较起真来六亲不认。因为没有老婆,得罪的人又多,所以大家背地里都称呼他为“柴鳏夫”。但此人军事技能过硬,无论射击还是格斗,都有出类拔萃的方式方法;只因不善交际,如今还是个班长。景腾想着弟弟在他的手下虽然要多受些皮肉之苦,但能快速成长为合格的战士,倒也不必在意太多。
短短一个上午,进进出出的景传志像变戏法般在药铺里添置了三个火炉、十几只砂锅,以及桌椅板凳等物件;挂在墙上、他亲手绘制的人体经络穴位图告诉来人,这里的郎中医术精湛。换上便装的景腾有条不紊地跟着父亲忙碌,满头大汗,欢快之心却不言而喻。景颜和彩蝶将一个个药橱中的药材拿到院子里摊在干净的纸板上晾晒;阳光的照耀,使药材的味道比之前大了好多。彩蝶嘟囔着鼻子,向恼人的气味提出抗议。
四
高提鸟笼、咧嘴剔牙的雷赟左摇右晃地走在外滩的金陵路上,吊儿郎当的;跟在他身后的许诺和魏青松看上去要低调很多,将手插在裤兜里,一言不发,神情自若地踏过一块块地砖。身为一行三人的老大,雷赟的外表格外地引人注目——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高突的颧骨、奇长的眉毛。每次收保护费,基本不用魏青松和许诺开口,雷赟的这些“坏人特征”,足以让他们的“衣食父母”们不寒而栗、乖乖就范。来到景传志的店外,雷赟干咳了两声,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整理药材的景传志见“生意”上门,微笑着问:“看病?”
“到药铺不看病难不成是来洗澡的?”雷赟抬起高高的头颅,没好气地答。
景传志看了看几位不像是病人的来客,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上读懂了隐藏的另一层意思——来者不善!“哦!请问您哪里不舒服?”他故弄玄虚地问。
雷赟摸着头答:“头痛。”
“什么样的疼痛感呢?胀痛、钝痛、麻木痛、压迫痛?还是紧箍感的痛?”
景传志说完专业的问诊术语,雷赟“呃”了一声,不耐烦地答:“你别再说了。我是缺钱引起的头痛。”
“那我治不了。”景传志微笑着说。
“你治得了。”雷赟笑着说,“直说了吧,按照这家店之前交的,你每个月要给我们一块大洋。”
“这一块大洋交给你,有什么说头呢?”
“保障你在这儿安稳做生意的前提和资本。”
翻弄药材的景颜察觉到店里的异常,急忙跑到了父亲的身边。将一切尽收眼底的彩蝶也丢下手中的活儿,走到生炉火的景腾身旁,小声地告诉他屋内的状况。没有去看,却将父亲和来人对话听得一清二楚的景腾微微一笑,放下手里的火钳,走进了屋里,问:“张啸天老板是你们什么人?”
雷赟干脆利落地答:“我们老大。”
景腾气宇轩昂地出现,雷赟有些意外;但每天走街穿巷地收保护费,他可是各种各样难缠的人都见识过。很快,他就恢复了狰狞的面孔。
“劳驾你回去跟他说一声,改日我亲自把钱给他送去。”景腾笑着说。
雷赟愣了一下,问:“你认识我们张老板?”
“哦,认识。”景腾答,“他请我吃过饭;在他家里。”
雷赟取下嘴里的牙签,撇着嘴看了一会儿景腾,说:“这个钱是我们二老板负责的。”
“吕祚行?”
“是的。”
景腾笑着说:“谁负责都一样,你说是姓景的欠的,他不会为难你。”
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搬出了张啸天,雷赟知道这家的钱难要了;虽然一时半会儿搞不清对方的底细,但能被张啸天请回家吃饭的自然不是一般人。不管他是不是吹牛皮说大话,等上一两天也不要紧,反正张啸天和吕祚行最近都不在淞沪:
“大老板和二老板都不在家。既然你们熟悉,我想他们是不会要你钱的;但还是劳烦你亲自去说一声,免得我们难做。”
雷赟闪烁其辞的眼神告诉景腾,他是不信任自己的;他的话中意,是把包袱甩给自己——既然认识,你给不给钱,张啸天收不收钱,都一定要去登门拜访啦;否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
景腾不是在乎区区一块大洋的人,他只是担心父亲带着两个女孩子在这儿,被心怀叵测的人认为没有依靠,时间久了难免会受到欺凌;与其如此,不如一开始就让那些鸡鸣狗跳之辈望而却步。
“张老板没在淞沪?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景腾问。
“他去了杭州。”雷赟答,“应该就这两天吧。”
景腾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雷赟抱拳道:“我们先告辞了。”
“请!”景腾说。
彩蝶趴在门框上偷偷地看着雷赟等人走远,才缩回景腾身边,心有余悸地问:“这些是什么人?张嘴就要钱,跟强盗一样!”
“差不多吧。有些强盗在人少的地方抢,这些强盗在人多的地方抢。”景腾答。
彩蝶问:“景腾哥,他们好像有点怕你;你又没穿军装,他们知道你是大官吗?”
景腾笑了笑,答:“我哪是什么大官?我认识他们的老板而已;他们害怕自己的老板,在没摸清我的底细之前不敢怎样。”
“这样啊,你认识他们老板吗?”彩蝶问。
“认识。”
“那就好,不用交钱了。”
景颜带着责怪的口气问:“大哥,你干嘛要认识这些坏人啊?”
景腾笑着答:“认识他们有两个好处,一是没人敢欺负你们,二是不用给他们钱了。”
景传志说:“这些人都是刀口舔血的主,不可深交,更不能不防。”
“爹,我知道了。”景腾答。
景颜将头探到院子里看了一眼,惊呼道:“大哥,你的炉火都冒出来了!”
景腾一拍脑袋,道:“哎呦,忘了!”
经过一天的整理,药铺已经变了面貌,从只零售中药材的小店变成了集诊断、开方、熬药和短暂歇息的诊所。除了景腾,景传志和两个女孩都有些疲倦,但看着已经像模像样的“根据地”,也都累并快乐着;更何况今天已经做成了几单生意。
吃完晚饭,景颜和彩蝶睡觉去了;等康文玉开车接走了景腾,景传志又简单收拾了一会儿才草草地洗罢,躺在了床上。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他不禁有些担心,要钱的人明天还会不会来?景腾不可能天天在这儿,如果哪天他们再来,自己该怎么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迟早会来,担心也没用。想到这儿,景传志将烟斗里的烟灰磕掉,闭目进入了梦乡。清晨,准备营业的他来到前屋,抽掉第二块门板,看到门外竟然跪着人;仔细一看,是昨天来要钱的三个人。他皱着眉头,不明就里地忙碌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过去对雷赟说:“老弟,又来要钱?有什么话咱到一边说;都是男人,跪着不难堪?”雷赟想:这老头儿不会以为我是在故意为难他吧?许诺难为情地说:“我们不是来要钱的。昨晚大哥二哥回来了,我们提起白天的事,大哥勃然大怒,骂我们瞎了眼……后来就让我们来您的门口跪着了。”景传志想:他们在这儿跪了一宿?他们的大哥是景腾说的张老板吧?骂他瞎了眼、让他跪在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
“您忙您的,不用管我们。”雷赟认真地说。
“你们跪在这儿,我别想开张了!”景传志说。
雷赟朝周围看了看,还真是——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往这儿一“杵”,搞不清原因的谁敢往里进?他苦笑着说:“真不是为难您,不按大哥说的做,我们的下场会比在这儿跪一夜惨十倍。希望您理解。”
“那你们朝旁边挪挪;我没法做生意了。”景传志无可奈何地说。
雷赟答:“不行啊,大哥不说话,我们不敢起来。”
“好,愿意跪,你们就跪吧。”景传志摇了摇头。
景颜等父亲回屋,小声地问:“爹,他们想干吗?”景传志说明了事情的缘由,景颜和彩蝶感觉又好气又好笑;景传志并不觉得好笑,因为他已明白,这个素未谋面的张老板绝非等闲之辈,而等待自己的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