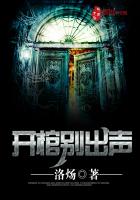1.
相比小麦,我更喜欢Max这个名字,强势,所向披靡。
小麦,小麦,外表披着的是Max,内心是永远17岁的小麦。
我17岁时,形单影只到加州读大学,妈妈在电话里对我说:“小麦,还有3个月你就成年了,妈妈不再管你了,得学学他们管小孩的模式,学费我出,生活费你自己赚。”
我挂了电话,加州南部秀丽的风光照在脸上,我贪婪地吸了口气,“HereIam!”
靠着导航仪,我顺利地找到住处,大学,波澜无惊地开始,刺激的过程,迅速地和室友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打成一片,聚会不断。
第一次遇到他是什么时候?哦,大一的中秋节。
第一次遇到苛钟逸,才知道他在华人界是多么出名。虽然自己是华人,可是我对华人学生关注的并不多,从记事起,我就一直呆在国外,只是自己长了一副亚洲人的面孔。
众星捧月的他为人却很低调,听说他家里很有钱,其实,有钱的公子哥多了去,不缺他一个,唯独不一样的是他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整个人西装笔挺地站在那,就是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中秋节,其实我也并不常过,有时候妈妈记得了,就从超市买几个月饼,妈妈不记得我当然也不会记得。这次来完全是因为无聊加巧合的缘故。
那年的在中秋节,月亮特别圆。
男同学架起了烤肉架,女生则在包月饼,然后送到烤箱中烤。
包月饼也不知道是谁想的,只听说过包粽子,包饺子,做汤圆,没听说过包月饼,旁边的一个华人女孩子说,“还不是那个邹晖。”
邹晖托着盘子,踩着杂草,走了过来,给几个包月饼的女孩子分刚烤好的烤肉,我笑着说“谢谢。”
邹晖眼睛亮了亮,说:“为你们服务,是我的荣幸。”
邹晖不知道在哪儿弄的烟花,不是在天上轰隆隆放的,是拿在手上甩啊甩的长条烟花,刺啦啦的闪着妖艳的花火,我一时迷了眼,和邹晖哈哈大笑着斗烟花,空气中除了烤肉的香味,还有烟花的硫磺味。
不小心撞到了他,苛钟逸,抑或是我刻意为之,喜欢就是喜欢,我也从不会压抑。
他扶了我一把,笑着说“小心。”
夜那么黑,月那么亮,他的轮廓有些模糊,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日后数夜,我梦里总是出现他的那句低沉的“小心”和那轮圆月下模糊的剪影。
2
我十八岁生日party,租了一个场子,邀请了很多好朋友,包括苛钟逸和邹晖,还有我的现任男友,一位白人,很帅,很结实。
生日party上,我记得我穿了一件黑色小礼服。
我唱了一首Iknewyouwereatrouble
Onceuponatime,afewmistakesago
在很久很久之前,当一切都是无容置疑的时候
Iwasinyoursights,yougotmealone
只身一人我在你的视线里
youfoundme,youfoundme,youfoundme……
你寻寻觅觅地找到了我,是的,你找到了我
Iguessyoudidn’tcare,andIguessIlikedthat
让我猜猜看,你一定毫不在乎,再让我思索一下,你的毫不在乎是我喜欢上你的理由
andwhenIfellhard,youtookastepback
我深陷了有你的爱河里,而你却不是原地等我,而往后退步
withoutme,withoutme,withoutme……
离我而去,没错,你离我而去
andhe’slonggone,whenhe’snexttome
他的心永不属我,千里之外,即使他不过近在咫尺
andIrealizetheblameisonme
我暮然忆起所有问题的差错在于我身上
cause
因为
oh,Iknewyouweretroublewhenyouwalkedin
当你走近我生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是我无法逃避的陷阱
soshameonmenow
只能深深地埋怨自己
flewmetoplacesI’dneverbeen
你带我领略我未曾浏览的风景
nowI’mlyingonthecoldhardground
而此刻,我却只能将心贴在在冰冷的地面
ohohtrouble,trouble,trouble
劫难,陷阱,无法躲避
ohohtrouble,trouble,trouble
劫难,陷阱,无法逃避
andnowIsee,nowIsee,nowIsee……
此刻,我如梦初醒
hewaslonggone,whenhemetme
他不属你,他的挚爱在万里开外,即使他近在眼前
andIrealize,thejokeisonme
我清楚的意识到,这是我对自己开的一个天大的笑话
唱完之后,我要等的人,始终没来。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对自己开的一个天大的笑话。
男友冲上来吻我,我丢下了话筒,和他一起忘情深吻,周围全是鼓掌,我也没找到那双淡漠的眼。
然后他们全都很识趣出去了。
男友开始撩我的裙子,我被吻得意乱情迷,推搡着他的胸膛,他半开玩笑的说:“Isthatyoufirsttime?oh,relax,baby…….”其实,真的是第一次,虽然我的同学就是14岁就做了,但是我14岁个头比他们小多了,还未发育完全,对那些事没那么期待。
他顺势把我放倒在矮沙发。
混乱中我抓住一丝清明,竟是苛钟逸那双淡漠的眼,我推搡着他,“No,getawayfromme!Sonofbitch,getawayfromme,.”
我却只能发出含糊的呜咽,他扒下我的衣服,我发狂地咬他,鲜血淋漓,他给了我一巴掌,“Bitch!”
身上的重物突然消失,混乱中我慌忙坐起。
只听男友一声惨叫地夺门而逃。
迟到的苛钟逸把外套披到我肩上,我抱着他的腰,结结巴巴抽噎着用中文质问他,“你为什么来这么晚。”
他说“对不起”,一下一下抚着我的后背,我却哭的更厉害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我大二时,他就回国了,听说家里有事,他哥哥被枪击,爸爸被审查。
几年的跟屁虫生涯,结束了。
最后一场见面是一处海滩,他潜水被蛇咬伤,我救了他,我也因为患了幻听症。不过,我从未后悔,我希望他永远记得我。
后来他和我表妹相爱了,他的神情温柔得可以滴水,我嫉妒,疯狂的嫉妒,我故意破坏他们的感情,凭什么她可以,我是Max,所向披靡的Max,论手段她耍不过我,论美貌她和我差不多,论工作能力当然是我强……
我却失败了。
他让我辞职,结束了。
我回到了能容下我的国家,却不料在他出事的那片海域我也出事了,他来了,可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他的心不在这里,我终于懂得了那句歌词hewaslonggone,whenhemetme
(他不属你,他的挚爱在万里开外,即使他近在眼前),我知道我输了。
我去德国新天鹅堡度假,世界上最美的童话城堡,而我却仿佛看到了路德维希二世悲情的一生,一个沉浸在幻想世界的****,等了一生都没等到他的茜茜公主。
多么像我。
我站在玛丽安桥上拍新天鹅堡美丽的侧影,青山碧野中的天鹅堡,娇贵孤艳的让人心疼。
小小的吊桥上人很多,木板被踩的吱吱作响,不安从脚底蔓延,再也没有人在过吊桥的时候牵着我的手了。
一只温热的手掌按上了我颤抖的肩膀。
那个人是由理。
我和他一起在德国各处去玩,喝慕尼黑的啤酒,洒脱放肆,从未这么快乐。
与其痛苦,为什么不选择快乐?
无论到哪儿他总是牵着我的手,很温暖,很安心。
我们躺在柔软的大床,他问我:“可以吗?”
我看着他虔诚的眼,点点头……
窗外在下着绵绵的雨,我永远记得那晚的雨,那么柔,那么润物无声。
我随他一起到了新加坡,我发现我和他很契合,无论是床上还是饮食起居,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我也开始学做个贤妻良母。
这之前的我来说,是多么不可能的事。
由理很好养活,无论是西餐还是中餐,都可以接受,其实他更偏爱中餐一些,总是和我一起吃我习惯了的西餐。
我们是谁先回家,谁就做饭,大部分时间是我。
又是一年中秋节,我打算做点中餐,可惜中餐,我学来学去也只会酸辣土豆丝,辣椒藕片,一样肉的都不会。
他从后面环住我的腰,把下巴搁在我一侧肩膀上,“好香。”
“说我吗?”
他笑笑,亲了一下我的脸,“都香,我来吧。”
说完就开始系上围裙,一派家庭妇男的模样。
我看着他刚带进来的月饼盒子,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
“太辣了,呛眼,你先出去,好了我叫你。”由理把我推出去。
我抱了抱他,“谢谢。”
对于我的过去,他从不过问。
我不死心问他,“你不问吗?”
他拿着铲子,“你现在是我的吗?”
我点点头,不带任何犹豫。
他笑,自己忍不住咳了几声,“你在哪儿买的这么辣的辣椒?!”
由理看到我出来的那一刻哭了,我提着婚纱摆,嘟哝着,“好重。”
他抱起我,我抹掉了他的眼泪,拍拍他的肩,“男儿有泪不轻弹。”
“成语学的不错。”他说道,然后突然问我,“后悔吗?”
我一愣,咬了一下他的唇,“你终于吃醋了?!我还以为你不在乎我呢。”
“我可知道某人一直留着暗恋对象的照——”
我捂住他的嘴,“那是三人的照片!”
他笑得有些得意。
这样的男人,居然爱上了我,此刻,我觉得无比幸运。
我和由理的婚礼上,安然再次挺着个大肚子来参加我的婚礼,抱怨着,“我又错过了一次当伴娘的机会。”
点点在我婚纱上蹭,苛钟逸眼疾手快地制止儿子的举动,“不许弄坏了阿姨的婚纱知道吗?”
点点委屈地看向妈妈,我笑,“没事,小孩喜欢玩嘛。我老公来了!”
由理进了我的化妆间,和他们几个打了个招呼,给我整理了下衣裙,眼里映着我的影子:“别累着了,待会桌子比较多。”
我笑眯眯地说,“好。”
再累,都是幸福。
我带四岁的儿子嘟嘟回国。
和安然大谈育儿经,安然此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由理在和苛钟逸谈生意,时而大笑声传来,我嘟嘟嘴,不知道又是谈哪里赚了多少,哪里的姑娘漂亮。
安然抱着两岁的女儿,“你就喜欢胡思乱想。”
我嘿嘿笑笑,“小糯米长得真好看,真乖啊,不像我那嘟嘟,整天玩飞檐走壁。”
“再生一个呀。”
我摆摆手,“不敢了,再生我身体就要变形了。”
晚上,由理哄玩嘟嘟睡觉,弄醒我,“小糯米真可爱。”
我要睡觉,“嗯”了声。
他扳过我的脸,在我耳边吹气,“小糯米真漂亮。”
我推开他的脸,“你去生嘛。”
“你知道我今天和苛钟逸说什么吗?”
“不想知道,我好累。”
“我们在说,怎么生个女儿。”由理的手开始不安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