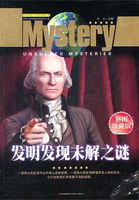天气逐渐变冷,街上行人少了,树丫上的鸟儿也不闹腾了,整座城市灰蒙蒙的。
一走出玻璃门,一阵阴冷的风扑上面颊,我把脸往围脖里缩了缩,搓了搓手低着头走出医院。
一路上我只顾低头,也不多做停留。
大概是从两年前我在房间里晕倒被房东发现开始,我每个星期都必须去一次医院。
有的时候,我会在医院里和医生呆一整天,所以我和这里给我就诊的医生还算熟,只是日子这样一天一天毫无意义过着,我还是会害怕,还是会想起以前的事。
没错,用施愿的话来说,我有忧郁症和轻微人格分裂。
用我的话来说,我就是个神经病。
我下了的士,然后朝我住的小区走去。
一路我都只看着灰色的地面,头也不抬地横冲直撞。
走着走着我停了下来,我看着脚上散开的鞋带,楞了好久才弯下腰去系。
这时,视线里出现一双蹭亮的男士皮鞋,我明显地能感觉到一个高大的影子罩在我的头顶。
我正蹲在地上,感觉到了头顶有人看着我,我便抬起头来。
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气质不凡,剑眉心目。
他微微皱着眉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虽是平静的,却还是能看出眼睛里的血丝,好像是愤怒,又好像是……不可思议?
我认出了他。
四周的冷风仿佛变成了那个夏日的风,他笔挺的西装仿佛变成了白色的衬衫。
那个夏天,那个白衣少年。
我又见到了他。
我的喉咙隐隐作痛,风吹得我眼里进了细沙,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我站了起来,想说些什么却最终无话可说。
最终,我慌乱地绕过他,落荒而逃。
我懒得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也懒得去回忆我们的当年。我只是走得很快很慌乱,很快很慌乱。
慌乱到我到了家门口连钥匙也差点插不进锁。
突然想到了余生瑶说的一句话“高傲从容的楚繁星只有遇到田野时才会手足无措。”
是啊,更何况现在卑微到尘埃的楚繁星呢?
还未从刚才的情绪里挣脱出来,我就感觉到了手机的震动音。
是施愿打来的,身为我的心理医生,他是最关心我生活的人。
“繁星,你到家了吗?”施愿问到,语气里是被他极力遮
掩的疲惫。
我踹了几口气,慌张的说:“刚……刚到。”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施愿还是听出了我的情绪不太对,毕竟他是最了解我的人。
我说“晚安!”
我总是这样,只要施愿问我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都会说晚安或者再见,说完就挂了电话。
施愿都习惯了。
挂了电话,我像往常一样,泡了澡后就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紧紧地。然后睡得轻轻地睡着。
朦胧中我感觉到有人在拉扯我的被子,我微微睁开眼睛就隐约看见了施愿的轮廓,他身上总是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
因为是我的心理医生,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房东把我的钥匙给了他。
他偶尔会来看我。
今天,他连白褂子都没来得及脱掉就赶来了。
可能是怕我一个人在家出什么事吧。
“又是不吃晚饭就睡觉嘛?”他喃喃道:“嫌自己的身体不够糟糕啊?”
我听着就睁开了眼睛。
“我困了。”我小声地说。
施愿却还是把我拉到餐桌上,狠狠地说:“先吃饭!我这么大老远急匆匆过来不是想看你饿自己的。”
他的话我明白,我不吃饭只是我多种自残方式中的一种而已,他最怕我这个样子,一声不响地就能弄死自己,甚至是那么的平静自然。
桌上是施愿用昨天的冷饭给我做的蛋炒饭。
这几年我吃得最多的就是他各种各样的蛋炒饭和只能说是实验品的小炒。
我按照他的意思平静地吃完了一碗,然后又说:“我真的困了,施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