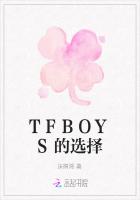当静谧的月色染上常青松,藏在暗夜里的孤魂也攀上这迷离的梦境。
阁楼上的书斋灯烛已媳,皎白之色泄在半合的宣窗上,画出幽幽疏影。房中人已然歇下,月白的底衣让主人的气息也归于宁静,松香清淡,给这一片夏夜谱起无声的曲。
悄无声息间,窗上的阴影变换了形状,立耳尖嘴,俨然一副狐狸的形容。芩恪在睫羽间看得真切,那阴影似有成年狐狸般大小,比起白日里撞上的那只显然大上不少。许是光影的缘故吧,芩恪胸中心念疾转,面上却仍是一副安宁的睡容。
窗棂微动,一阵浅香盈盈飘进房中,如尘埃落地,无声无息。
不对,这与早前的气息完全不同,想来定然不是同一只狐。这股气息妖异轻盈,带着引人迷醉的魅惑,而芩恪分明记得,那小狐狸周身几乎未携着半丝妖气,那是一种清灵澄澈到天池中的青莲都会自惭形秽的明净。晌午时分如若不是胸前坠着的灵玉指引,芩恪确信自己是发现不了那小家伙的。
夜风荡起窗前的树影,一窗之外的那狐顺势将窗缝推得更开了些。又一阵风掠过,那影子便趁着风声挤进屋内。房中除却轻缓的呼吸声再无一点动静。狐狸幽绿色的眼睛打量着雅致的书橱,茶案,桌椅,所有的陈列都呈现出一片清雅的规整,唯独……
狐狸眼中闪过明了之色,狡黠地眨了一眨,从书案跃回窗棂,发出“咔哒——”的响动。
芩恪下意识地一皱眉,又听见几声刺耳的摩擦声,心下更是诧异。微微抬起眼皮,竟看见那狐狸正蹲在窗台上,用自己尖利的前爪挠着樟木的窗框。
风声窸窣,那刺耳的摩擦声越发尖利和急促。芩恪无奈之下也只好放弃守株待兔的算盘,直截了当地睁开眼,见到自家的窗户已经被那妖孽挠出了火星子来。
窗上蹲着的那只白狐见到芩恪既然已经大大方方地睁开眼,也停下了自己装模作样磨着的指甲,在男人翻身跃起的同一瞬间挑起一枚火星。那火星在狐狸爪间忽地烧成一簇翠色的火焰,如莲花一般绽开。
就在芩恪的身影铺上窗台的同时,狐狸腾身一跃,落在院角的假山上,顺便一抖狐狸爪,将那朵火焰莲花向院中抛去。而那妖火竟真如花朵一般零落成纷纷的碎羽,点燃院中每一处角落。
一切只在瞬息之间,转眼芩恪已经看不真切那假山上狐狸的身影。眼下最为棘手的还是将院中的妖火灭去。芩恪凝结心神,念起驱邪清心咒。
约摸半盏茶的功夫,院中的火焰才渐渐媳去。妖火是冷火,因此并未伤及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但要追回始作俑者显然也再无可能。芩恪意兴阑珊地回到楼上的书房时,那原本躺在藤椅旁案几上的文房四宝连带着篮子已然没了踪影。
芩恪揉着鬓角,唇畔挑起无奈的笑意,果然,事先没有准备,临时弄来躺人的藤椅与房中的其余摆设显然是格格不入,狐真不愧是兽中灵物,承得昊天眷顾。
远郊的一处山坡上,松脂的香气镇静了夏的燥热,少年正低着头,借着细碎的月影检视篮中的物件。身畔一道窈窕的倩影靠躺在树干上,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
“我说,你小子就不能提着点心,这次要不是那人长了个榆木脑子,莫说这些家伙,连你这身狐狸皮恐怕都得保不住。”女子侧过头来,一边用幽绿色的妙目撇着少年,一边说道。
葛尘检查过砚台,又将那支墨拿到月晖下仔细瞧着,“我又怎会晓得那人竟能看出我的本体,这一趟走过这么些地界,此番还是头一遭,我这不也正愁着的么。”说罢将手中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搁回篮子,用缎子掩好。
就见着你气色一日不如一日,什么明心,什么赎罪,分毫未见得,只是为他们添了一路的香火,什么慈悲,根本就是借他人之灾谋自己的利。”
“轰——”原本晴好的夜色骤然被一阵惊雷打破,顷刻之间乌云聚汇,大雨倾盆。
葛尘将篮子护在衣襟里,缩到一块巨石之后,瞅着被吓去半条命的苓儿笑得很悠然。
翌日,天清气朗,万里无云,芩恪一直睡到巳时才被母上大人从榻上拎起来。
“瞧瞧你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德行,要不是当年让你拜了房先生学猎妖,你怕是早就把祖上的家业败完了。”芩夫人打掉儿子揉着惺忪睡眼的手,将一根红绳系上儿子修长的脖颈。
红绳之上结着一段平安结,绳结之下坠着一枚通透的翠玉。玉质细腻润泽,从窗户射入房中的日光仿佛就在玉的纹理间流动。玉坠是狐狸的形状,但细细看去竟然觉察不出雕琢的痕迹,仿佛这玉生来就长成这模样一般。
脖子上的绳子刚系好,芩恪倒头又欲躺下,硬是被母亲生生掰起来,“老娘一大早去北市给你求平安结都回来了,你还有脸窝在床上,赶紧梳洗打扮着,娘约了唐姑娘来家里吃午饭呢,快快快……”
芩恪原本还迷糊着的意识立时一片清明,“哎呦我的老母亲,您真是成天不干别的,净琢磨着怎么把自己儿子嫁出去是呗,您儿子是得有多寒碜,怎么就惹得您眼瞅着烦了,一天也看不下去了是呗。”
“嗨呀就你这德性能嫁出去都得烧高香了,何况人家姑娘知根知底,也标志,让你小子捡着宝了你还不赶紧偷着乐。”
“但您也忒积极了点儿把,之前不是才在一处过了寒食和五月五么,这才过了几日,您也不嫌累。”
“哟,替儿子张罗亲事儿哪能马虎了,娘还帮你把七月半的日子也约了,等到你这的事办妥了,娘也能入土为安了。”
“哎呦求您别瞎掺和了成不,您不知道儿子我七月都是忙得脚不沾地儿的么,哪有功夫陪姑娘菱舟泛夜。”
“那你就带着姑娘一同去嘛,让人家瞧瞧咱家儿子也有威风的时候,咱可不是成天只会打瞌睡不干活吃了饭碗也不刷的主。”
“呵,您可真能想得出来,您儿子可是成天跟魑魅魍魉一道儿混的,还把人家姑娘拉下水,人家父兄不得跟您儿子拼命啊。”
“那不正好来一出英雄救美,人家姑娘不就能以身相许了吗嘛,现在的小姑娘呀,都是看着戏本子长大的,可吃这一套了。还有我可听说,东城柳家的二公子可是对糖姑娘倾慕已久了,你小子可不能给咱们芩家丢了面子”
“得得得,您先歇着去吧,儿子我得沐浴更衣了。”说着芩恪将喋喋不休的母亲终于哄了出去。
芩恪在丫鬟催了三次之后才施施然步出闺房。等到他姗姗来迟,饭厅里已经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致。
唐家小姐是一位典范级别的大家闺秀,识大体,善琴棋,面容端秀,淑德娴静。
艾色的装束在初夏的微醺里格外清凉。姣好的面庞托起额前和两鬓垂下的碎发,盈盈之间素净而不失娇俏,温柔恬静。
“哎呦,这大姑娘可算是下了秀楼了。”芩夫人一边念叨着一边给唐姑娘添茶水。
芩夫人虽说口舌不饶人,但厨艺当真是一绝,一顿饭吃得风平浪静。
酒足饭饱,芩夫人开始催着儿子带着姑娘逛花市。
初夏时节,恰是月季最娇美的时候,花市里卖花的姑娘也是一个赛一个的动人,芩恪与唐姑娘信步其间,有些心不在焉。
唐家小姐也是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不过也并未显出多么不悦,还时不时拨弄着摊位上的花花草草。
这时唐姑娘瞥见一边的一束白月季相当别致,正想过去瞧瞧,却见到芩恪正神情肃然地望着那个方向。
松树阴下,一男一女正低头整理着花木,这时其中一人抬起头来,唐家小姐至今仍然记得,那一抹不属于人间的翠色。
谢承华正携着幼弟在午后的街市上闲逛着,忽听见不远处一片哗然。循声看去,但见地上一片残落的月季花被碾得失了风韵。
就在他正要将事态看得更详细时,却见几步之外的一位姑娘向后仰倒就要这样摔下,立时上前将她接住。
“唐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