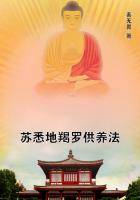暴雨倾盆。浓重的乌云笼罩着临淄城的上空。
噼啪,噼啪,噼啪。雨水冲刷着地面的血渍和污浊,血红色的雨水顺着道沿边沟汇总流下崖去。临淄城内死去之人没有得到收敛,也没时间收敛,他们颜色惨白的残破尸首接受着大雨的不断洗礼。
此刻巳时。
田和靠坐在门边,望着沿屋檐滑落的雨帘出神。今日已是距离田军将姜军赶入内城之日的第二日。
“公子,这内城难破程度实在难以想象,但若再不一举拿下内城。恐怕我军就要率先坚持不住了。”季耳忧心忡忡的对靠坐在田和旁边的田利道。
此刻的田军上下如同这古老的临淄城,异常狼狈。所有人的装束神情都狼狈。突然爆发的武变,愤然而起的反击,惊心动魄的巷战。持续摧残着所有人的意志。
“我又何尝不知道,但这临淄城本就是姜子牙所建,这内城更是他留给他子孙的最后屏障,我军攻不破也在情理之中。”披散着长发,俊美如同往昔的田利叹气,摩挲着手中田白所遗之剑,心中思索着破敌之策。
“信使已派出去了吧?”田和此刻穿着一件虽是粗布制造,但还算干净的白袍,头发同样披散着,他定定看着季耳道。
“所有能找寻到的信鸦都已放了出去,信使也派出了三波。”季耳郑重对田和道。田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武变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已深深折服了田氏上下。
田和撇撇嘴,不再言语。
田氏上下对田和态度的转变他当然能察觉到。其实这道理很直白——金钱权势固然可以赢得别人表面上的尊重,但要想赢得别人真正尊重的最好法子还是自己有真本事,毕竟这东西做不得假,别人也窃取不了。
正当这时,一名被雨水琳得湿透的兵士慌慌张张的从雨中奔入暂为田氏兄弟歇脚的楼舍。
他慌急的走过青石阶梯,啪的一声重重摔了一跤,连忙再爬起来,几步窜到屋檐下的田氏兄弟面前,单膝行礼道,“公子!二位公子!不好了!”
噌!
“别慌,气先喘匀,”田利将手中箐光剑插回鞘中,神情严肃的注视面前慢慢平静下来的兵士道,“细细道来,到底是何情况?”
“公子,所有信使都被回来了!薄姑出兵了,人数极多,已将青龙崖彻底围了起来!”兵士年纪三十左右,他的左耳没了,失去于不久前的残酷巷战中。
“何人领兵?”田利并无惊讶之色,这结果是他和田和都料到的。毕竟两人在推演战局时都是以最坏可能进行的。
“但见到一面巨大‘候’字将旗。”兵士答道。
“哼,候夸!”田利眼中闪过一丝怨毒,又是一个背叛田氏之人。
候夸是田氏支脉之人,因私生子身份,不能以田为氏,算起来是田利叔伯辈。而他能成为薄姑城军领,甚至能活下来都全靠田白提拔,毕竟田白与候夸是从小长大的。
“薄姑离临淄不足百里,算算武变开始到现在,也是时候该到了。”田和点了点头。
“薄姑有兵一万,既然是这贼带兵,那必定是倾巢而出无疑。”田利跟着道。
田氏兄弟对望一眼,一齐看向季耳,“我军现还有多少兵?”
“不足五千。”季耳答道。
腹背受敌,兵临城下!
“季师,我命你带全城兵士搜寻尚存临淄居民上城墙防守,留武士四人队于内城外屋舍中以防姜军反攻。”田利提剑而起,“和弟,你我再去看看这该死的内城墙!”
……
“国免!你不是曾在本公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田白一死剿除田氏轻而易举吗?为何现今弄成如此局面?!本公身为齐国主人,竟然被逼得龟缩于自家内城而无法动弹分毫!简直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当今齐公年方三十有五,姜姓吕氏名壬,为齐悼公吕阳生次子,生得唇红齿白宽皮大脸,一副富贵相貌。此刻他坐于齐宫青龙殿龙位之上,对垂立于殿下的国氏家主国免破口大骂。
“禀公上,臣等确实未料到田白长子区区一阉人竟有如此心机魄力,竟第一时间命季耳斩杀我方内应蜃门门镇符广,否则我军早已控制临淄城矣。不过请公上放心,臣刚接到信鸦报道,候夸已率一万薄姑军前来擒贼,剿灭田氏指日可待。”国免尚未开口,高且站出安慰道。
“哼,本公不管以后如何,就想知道如何将外城田军诛灭!”高且不说还好,说了之后齐公更加气怒。
“公上可是怕了?”国免静静看着齐公咆哮,忽然开口道。
“大胆!国免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蔑视本公威仪!”齐公仿若被戳中痛处的兔子,歇斯底里的咆哮道。
“哼!蔑视你又如何?吕壬你别忘了,当年若不是我国、高二氏死保,岂会让你一个悼公庶子以十二岁之龄登上齐公之位!”国免见齐公那副色厉内荏模样后越加失望。
“你还敢说!当年我父在位时,国氏、高氏、庆氏、栾氏、晏氏、鲍氏、崔氏、田氏等八氏辅佐我吕氏,国、高、庆、栾、崔皆是我姜姓氏族,晏氏乃名相晏婴后人、鲍氏同样是贤臣鲍叔牙后人,当时何曾让田氏坐大?然而你国、高二氏贪婪成性,为田氏歹人利用,于我父悼公病危之时,诛杀我长兄吕谷与支持吕谷之栾氏、庆氏、鲍氏,当时田氏家主为田白之父田盘,田盘仅仅一个‘二桃杀三士’之局,便让你等狗咬狗起来,继而崔、晏两家灭亡,崔、晏、鲍、栾、庆五家封土多被田氏所得,致使我姜吕齐国几成田氏之齐!”齐公凶狠望着国免,将多年苦水尽数吐出。
“吕谷若不死,栾氏、庆氏、鲍氏若不亡,你吕壬能作齐公?”国免面无表情的望着当今齐公的咆哮。
“够了!此刻内城尚被田军围困,绝非争论之时!公上,我国、高二氏过去确有种种不是,然而自始至终皆拥护吕氏之国!凭此一点,臣等问心无愧!敢请停歇争论商议对策!”高且见此情景,垂足顿首。
青龙殿陷入一片寂静,几人皆不言语。
良久,
“罢了,现今当如何解此危局?”齐公一声长叹,问询道。
“临淄内城乃圣祖太公所建,绝非一万田军可破,而内城粮草足以支持我五千姜军半年,且临淄城已被薄姑军围困,田氏根本无法传出讯息而我方却往来信息无碍,故仅需继续调动兵力来临淄,兵力足够后里外夹攻则临淄可定,而在外有十三国联军扫荡,有多年埋伏内应棋子作用,亦无须担心。我等看似危险,然而真正如坐针毡的其实应该是此刻在外城指挥的田利。”国免闭目冷静开口,“而且我有一计,可速断田氏命脉,掌定临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