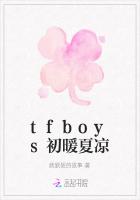在商学院上的管理学,最后有个作业,我跟一个搭档吵架,写下各自对矛盾的理解,然后交换文档。当我站在他的立场来看问题,意识到我的沟通能力好差,我说出的话导致很多歧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很愚蠢的原因吧。因为他们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或者说我的表达能力不好。只有跟我相似的人才能理解我,因此我的朋友数目很有限。
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业上,而不是卡尔。奇怪的是,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爱我,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成熟。我太忙了,没时间去想,我是否爱他,反正觉得跟他没有未来。但我不怕接受他的好意了,既然他愿意给,我就接受。世事就是这么奇妙,当你不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人们就会给你这样东西。当你照顾好你自己的时候,人们都拢来了。当你需要人们拢来照顾你的时候,人们都远离你。也许,我也长大了,对于变化能很平静地接受,学会了顺其自然,而不是力挽狂澜。现在的我,越来越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知道哪些是梦想哪些是现实。前不久还跟身在欧洲的叙霓聊天了,告诉他,我现在比以前更快乐,因为更了解自己,不再是没心没肺的快乐,有了平静和深度。
新学期开始了,我不喜欢,因为意味着我变老了。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人会成长。要成立博士答辩委员会了,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能力、跟教授的契合度、资金。于是我脑海里逐一回顾每个教授并分析跟他们合作的优缺点。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有人让你不舒服,可你又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是最可怕的,比任何明显的问题更可怕。在美国有很多体面的人,不会做不体面的事,但会让外来人满脸疑惑地被玩弄或遗弃。
没想到找委员会成员,是这么头疼的事情。首先,我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能力不足以独立做研究。不然的话,我可以跟着开明的教授,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找那种狭隘的教授,我就必须服于管制,做他的研究。而我又是有想法的人,按照别人的指示行事,往往力不从心。其次,教授们特别能装逼,似乎不忙就体现不出他成功。痛快点答应不行吗?能耽误你多少时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为了正确解读教授们各种体面的表达,我还得请教各位学长学姐以及其他同学。他们说的都在理,可是最终还是要我自己作决定。招我进来的教授都不怎么来学校,已经半退休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跟她的联系也不紧密,现在换导师似乎也找不到特别适合的。有时觉得教授们都是差不多的,都期待高回报。即使刚开始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他们的立场类似,角色一样。因此也不必想太多,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其实他们不会伪装什么,不屑于在学生们面前伪装。他们愿意或不愿意帮助你,是很明显的事。
唯一让我感到踏实的是工程学院的瑞斯教授。去年我就在计划寻找委员会成员了,想学一些跟规划相关的经济学的知识,于是找到了瑞斯教授的网页,看起来不错。就给他打电话了,说想要他加入我的委员会。他回电话说,他的研究领域其实比较狭窄,但是愿意尽力帮我,要求是我要上他的课,这样比较有点基础。我觉得这个教授很朴实,回答干脆,要求明确,对自己的定位也很谦卑。其他教授很难找到人,他们非常忙,即使找到了,仿佛也没有看我的邮件。从我们系一个教授那里了解到,跟教授约见面的正确方式是:应该是先发两次邮件,隔两天没回复再打电话,还不成功再隔两天,最后去办公室找。问题是教授们来学校的时间本来就有限,不是每天都来,更不是整天在办公室。按照这种概率趋势,一个月能见到一个教授,单是约见教授就得一个学期,还别说组成委员会了。原来我们系是全校最厉害的呢,系里的教授比工程学院的忙太多。要不然,怎么瑞斯教授就有时间及时回复,及时安排?其实我们系应该是装逼第一,学术比工程学院差远了。
我每天除了工作学习,就是跟卡尔去健身房或餐厅,与世隔绝了。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中国教授家的聚会,终于可以跟卡尔以外的人说话了。感觉吸收到不少营养,原来我错过了这么多吸收营养的机会。跟有想法的人谈话是这么有趣的事。我真应该回到现实中,过自己的生活。跟卡尔在一起像是生活在笼子里的鸟,没有危险,也没有接地气的生活。难道我真的必须伤害他,才能过自己的生活吗?
卡尔有健身的习惯,每周至少三次健身房,他甚至把器械搬到家里,因为健身房里人太多,还多汗。最近我也开始运动了,一个星期游泳三次,跑步两次,身心感觉舒服多了,不那么偏激了。有一次,卡尔来我这里说话声音沙哑,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昨天切尔斯足球队赢了。我忍住笑:这跟你嗓子哑了有什么关系?他说他喊了十分钟。我说:人家给你一分钱了吗?警察怎么没抓你?他的世界总是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