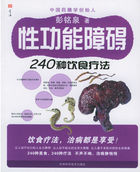就连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这样的人物也认为这个诉求有说服力。16岁起便吃素的富兰克林在一次航海旅程中发现,被剖开的鱼体内有较小的、整只被吞下肚的鱼。于是他下了结论:既然一种动物吃另一种动物是自然之道,那么人类吃动物应该也是自然的,因此,他轻信而自得地放弃了他的素食习惯。这里的论调似乎是这样的:人类在食物链中占有一自然地位,并且,既然人类也是动物,便可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吃其他物种,就像它们彼此相食一样。然而,泰尔菲(ElizabethTelfer)指出,这里有一个关系重大的语焉不详之处。在此,有关的论断若不是诉诸权利(entitlementclaim)(即人类有理由吃动物或有权利这样做),就是诉诸赏罚(desertclaim)(即动物理应被我们吃,因为它们彼此相食)。但,泰尔菲说,两种诉求都无法通过逻辑的考验。就第一个诉求而言,“我们不认为我们有权利对他人做他们对别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资格对动物这样做?”关于第二个诉求,其论证至多“提供我们吃肉食动物的正当理由”,而且,由于这些动物一般被认为“没有道德上的能力”,它们就“无法应得到、或不应得到任何待遇”。
然而,这论调持续以下面的形式存在:动物是为了人类的快乐与使用而被安置到这世上的;这看法有长远的传统与圣经的认可。抱持这观点的人,本书所谈论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打动他们的心。但是,许多学者论称,我们人类应该对其他物种承担起一种照管或照顾角色,而且他们也在圣经文字中为这个另外的立场找到基础。关于这观点我们前面已检视了一些(第七章第五节),那么,让我们看看世俗的论证:人类比动物优越,因此有资格吃它们。对许多人而言,此一所谓的“自然的优越性”已不像过去那么明显;除了这个事实以外,我们可以指出这个立场的一些主要问题。
首先,即使人类被认为完全优越于其他动物(例如,在语言、推理能力、工具使用,及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方面),这论证(依据泰尔菲的观点)作为支持我们吃它们的理由,并不比作为支持我们吃同样“劣等的”人类婴儿或有严重心智缺陷的人类成员的理由要强。其次,如果人类被认为在某些方面比动物优越,但在其他方面比它们低劣(例如,演化寿命、飞的能力及在黑暗中的视力,或控制侵略性),而仍然被声称为比其他动物优越,那么我们只是见证了一个物种主义原则(“人类一向是而且永远是优越的,只因为他们是智人[Homosapiens]这物种的成员”)的武断主张而已。而两种立场都可能面临以下这个令人不快的可能性:
一个外太空物种,有高度进化的智力与科技,但具有不同的道德信念,可能会使用这些相同的说辞来对待我们。最后,人类有能力作伦理的思考与感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是只会听从自然的命令而动作的动物;我们存在思考与抉择的责任。由于动物惯常彼此相食,因而诉诸我们在食物链里的“自然的”地位,或诉诸我们吃动物的“自然性”,正是要放弃这个思考与自主行动的责任。这是否定我们认为我们有别于,也优越于其他动物的能力之一。由于人类的确拥有关于他们可能或愿意吃什么的选择,而且由于这个选择有极其广泛的后果,所以应该谨慎而考虑周到地来执行这项抉择。
作为补充说明,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自然性”这概念本身是非常不明确的。
许多事(贪婪、战争、异性恋)仅以“自然的”为理由,就被认为有正当性,也有许多事(利他主义、和平主义、同性恋)以“自然的”同样薄弱借口而被谴责。因此吃肉被认为是自然的(或“正常的”),而素食是不自然的(或“不正常的”)。但,这除了意味吃肉是普遍的行为而素食较为少见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吗?吃肉在我们目前社会里可能(就统计上而言)是常规,但并不因为这样它就是比素食更“正确”、更“好”或更“有价值”的一种做法。事实上,就价值判断而言,根本不能做任何上述那种推论。从行为形态或个人特性的统计分布,无法合理推断出行为规范的结论。普通的音乐、艺术或科学能力,比有才华或天才更常见得多,然而我们不会说前者较好或较值得栽培。因此,自然性的论调并未解决任何事;争论(不论在特定案例中的议题为何)必须从别的方面解决。
动物是可取代的
“如果你看过一棵红杉,你便算看过了所有的红杉。”这句经常被归诸里根(RonaldReagan;译按:演员、美国前总统)的大胆之言,使1960年代的环保主义者和一般民众大为恼火。里根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仍无定论,但这类修辞背后的思想,在有关自然与自然生物的争论中倒是令人感到熟悉。例如,许多人似乎会认为,“如果你看过一只(某特定物种的)动物,你便算看过它们全部了。”用这么直截了当的方式说出来,这句话会让我们觉得很荒谬,甚至冒犯了我们的常识。但,从占多数惯于吃肉的人的行为,及其一般对于饲养与屠宰动物来作食物之议题缺乏关心的事实来判断,我们必须认定他们认为驯养的“农庄”动物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这里的“可取代性”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指动物在每个方面都彼此无法区别。它代表一种看法:就实际而言,它们是相同的,尤其是相同种类之动物的生命完全可以互换,而且缺乏称之为“道德特殊价值”的东西。换句话说,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只被杀来作为食物的动物,将会毫无损失地被多少是相同的另一只动物所填补。我们必须做的,至多只是确定它们在这过程中受到人道的待遇。
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拥有同伴动物(或宠物)的人打从内心深处知道上面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即将明白这个态度是多么无情而褊狭。人们不认为他们的特殊动物朋友是完全可取代的、没有道德特殊价值的东西;事实上他们认为它们根本无可取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待它们很特别,变得和它们非常有感情,失去它们时会哀恸,而且往往在它们死后追悼纪念它们。把一只刚死的特别受喜爱的宠物说成是可以完全取代的,那会被许多人认为轻率而且伤人。
当然,我们谈的是狗、猫、鸟、兔子、啮齿类及一些其他动物,而且我们能谈的恐怕就只是这些了。但,虽然我们很想画一条这样的界线,我们不妨思索,小规模农民及其家人也很熟知他们的动物,很容易指认它们、知道它们的个别特色、为它们取名字、有时和它们有情感联结。为了宰杀它们或将它们送到别处去宰杀,他们可能必须采取第三章里所描述的疏远或区隔化的态度。和其他种别的动物所发生的此类经验不应轻率地忽视,因为它们透露了,人们确实经常了解且本能地知道:动物是个体,因而就某个方面而言是无可取代的。有些天赋异禀的人能和驯养或自然环境里的黑猩猩、大猩猩、象、狼、海豚及其他野生动物一起生活,或和它们接近,他们也常常提到同样的发现。
尽管以上所说的这些,还是有哲学家建构了可取代论的说法:假如符合以下的条件,饲养并宰杀有知觉动物来作食物,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甚至正确的:
1.若非为了作人类食物而被饲养,有关的非人动物不会存在;2.这非人动物曾拥有舒适的生活;3.这非人动物的死亡并未带来痛苦、恐惧或其他不利状况;4.不会让这非人动物的至亲(例如其母亲、配偶)因其利用与宰杀而受苦;5.这非人动物在死亡时,会由另一头符合以上1至4之条件的动物所取代。
这个论点对那些古典效益主义快乐/痛苦说的拥护者可能有效,但很明显的,在现代工厂化农场的脉络里——看起来称得上符合的条件只有上列的第一项——它不过是个蹩脚的笑话。因此,或许它适用于饲养在开放环境中、并在3与4的条件下宰杀的动物。但,即使是效益主义最坚定的扞卫者暨动物解放运动创始人辛格(PeterSinger),也对这论点表示怀疑,他承认,“一个生物的诞生可以在某种方式上弥补另一个生物的死亡,这说法听起来很奇怪,”理由是,辛格承认有知觉动物和人类一样有偏好的事物,包括继续活下去的偏好。再者,它们累积了经验、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和动物彼此的关系与期待,可能还有其他意识面向,这些无法因为有另一生物的经验等等来取代,而不加理会。格外令人不安的是浦鲁哈尔(EvelynPluhar)所提出的论点:“可取代性论证适用于任何拥有福祉的个体,包括人类。”这里的主要观念不是人类本身是可取代的,而毋宁是:
某些为了特定目的而繁殖的人类可能是可取代的,如果他们是在符合上述五个条件的情况下被饲养并杀死的话。而这对大部分人而言,具有极度令人不安的意涵。
最后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要如何理解第一个条件的意思。这里的困难不是我们是否能有意义地思考尚未存在的未来生物,以及那些已经存在者的可能生活品质,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以及作为一个个人,在计划未来时一直是这么做的。困难在于造出我们蓄意要杀死的生物,它们可能拥有某些无关乎人类利益的价值,而且,如果可以继续存在的话,这些价值可以(就我们所知道的)更充实、更丰富,甚至更多样。
当然,所有这些复杂难题都可以消除,如果我们摒斥效益主义的探讨方式,或如前所述至少认定,它作为一个理论途径不足以处理利用与对待动物的议题,因为它并未公正对待这些议题的不容忽视的面向。例如,如果动物拥有某些基本权利,那么我们便不可以用可取代说所认可的冷漠而纯粹工具式的方式操纵其生命。但是更甚者,如果(就像越来越明显的)动物的有意识生活,比我们迄今所认为的还复杂,那么其心理、伦理与美感特性,便超越可取代说所依据的评估标准。
生态上的反对理由
柯力考特(J.BairdCollicott)主张,“吃素的人类群落……应该会造成生态上的灾难”。以及“吃肉……可能比完全吃素在生态上更负责任。”他的推论如下:
采取素食的人类将需要比目前存在的还多的植物。但是一个更大的植物性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口增加,而造成种种环境资源相对应的耗竭。接着,仰赖植物性生物的非人动物的数目将会衰减。所有这些结果都是无法承受的。此外,柯力考特还认为,素食代表“对那些仰赖人类肉食习性而存在之动物的一种诡谲的道德姿态。”
考虑到这一点,认为扩张植物性农业会使我们付出更大代价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因为这意味着,至少在北美许多地区,某些土地会开始回复白人殖民以前存在的植被覆盖(例如高原草地和森林)。虽然这样的说法可能具有争议性,很明确的是,种植人类的食用作物,是较种植供牲畜作食物的谷物有效率,且更有利于环保的土地利用方式。此外,现在用来放牧的一些牧场可以变更为食物生产用地,其余的连同低品质的土地,可以回复成野地。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柯力考特的论证着重的是:在一个素食经济体系内提高植物生产的次要或间接作用,也就是预计的人口增加所产生的作用。他并没有考虑到人类有一天可能会限制他们的人口数,他也不相信农业在整体上会变得较具有永续性。他这种信口开河的方式会导致最坏景象的结论,是毫不令人意外的。就像其他某些反素食论述,这个论述完全建立在猜测之上,以及对人类之本性、适应力、想像力与发明能力的悲观看法之上。
柯力考特暗示,逐步淘汰豢养的食用动物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的存在是我们吃肉习性的一个后果。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上文所讨论的可取代说。或许我们只需再补充:那些主要为了用作我们的食物而被我们制造的动物,如果知道等着它们的是什么命运,而且能清楚表达它们就这事的态度的话,大概不会给予我们道德赞美与感激。我们必须同意,在使食用动物产生,以及历经数千年的特殊繁殖而使其同类绵延不绝之后,我们对它们有一个重要的道德义务。但是建议我们最好继续屠宰并吃它们,借此尽到这个道德义务,而不要让它们永远免除剥削、奴役及虐待的主张,透露了人类自我中心的心态,而这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超越的。
杀生之必要
“人类为了存活必须杀戮”,有些人说。一如其他许多生物体,我们天生是杀戮机器;生命从死亡获得能量来源。这个论证接着说,要是我们关心造成活生物死亡这件事,那么,吃肉和吃素之间的差异便不再泾渭分明,因为吃素要求我们杀的活生物,会比目前的多得多。这个推理的理念不清。首先,有些素食者(食果者;)是不会为了吃饱肚子而杀生的。其次,认定生命必须从死亡获得能量来源,是过度夸张而且不正确的。许多以植物为食的人的采集方式不必然涉及杀害植物,例如摘果实与玉米;采集坚果、稻米及其他谷类;收集长在藤上的果蔬等。其他方式,诸如挖掘马铃薯、摘莴苣、拔胡萝卜,当然涉及杀害植物。但在所有的情况下,种子或插条可加以保存以作为植物再生之用,而没有被收成的植物一般而言会散播它们的种子,借而繁衍自己(当然,原则上这些情况对动物而言也成立。我们可以从活的动物拿取“插条”而借由无性复制(即克隆技术)产生新的个体;宰杀老动物时我们可以繁衍新的个体;而任其自生自灭的动物将会自行繁殖。但是我们可不能说有任何动物是我们不用宰杀就可以吃的)。第三,说在一个素食经济体系里有比目前更多的活生物会被杀,是没有多大根据的。人类会吃比现在更多的植物性物质,这是可以确定的。但只要我们仍位于食物链的“顶端”,事实上我们所摄食的(因而所“负责”的)是我们所吃之动物本身原来就吃的所有植物。因此,说我们在吃存活所需之数量的植物性物质时,会消耗比身为肉食者所消耗的还多,似乎是极为不可能的。第四,动物会受苦,而植物不会,所以,即使我们得以在杀会受苦的东西和杀不会受苦的东西之间作抉择,显然后者是较为可取的。
女性主义者对素食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