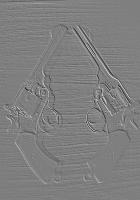人的一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哪来得一番风顺,事事顺心。永乐自从醒来后,无论是客观的身体上,还是主观的思想上都有了脱胎换骨得变化。
但无论如何改变,那颗永不服输的心是不会变化的,进到杂役房,每天跟着邢虎做事,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月余,每一天她除了准备食材,就是回到破木屋照顾生病中的小艾,因为她真怕这丫头挺不过去,哪一天变成了她手里的食材。
小艾的身体不好也不坏,脸色虽然比之前蜡黄好了许多,但是高热一直不退,猫一天狗一天,人也一直昏迷不醒。虽然永乐她们每天悉心照顾,可艾叶的身体还是一天天消瘦。
邢虎对外伤和死人研究得透彻,可对疾病就属于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放完了炎液,剩下得就看病人自己的造化了。其实说到底还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去求杂役房管事麻三儿,求他请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夫来,可永乐天真一回就不会再犯傻了,那个没有人性的东西,是不会管她们这些劳役的死活的。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连几天的春雨让木屋里充满了潮气,这阴冷的气体像一把小刀一样,割着她们身上的每一块肉,钻到她们每一个关节之中肆虐。
永乐,胖花和洛凌冻得瑟瑟发抖,真希望有个火盆可以取暖,更何况身体每况愈下的艾叶,更是被这凌厉的阴冷伤得很深。
“唉,小艾姑娘真是个苦命人,小小年纪遭此大难,希望她能吉人天相吧。”
洛凌的背伤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永乐和胖花一直问她为何如此境遇,可洛凌就是闭口不言,只有眼泪在眸子里打转。
永乐知道洛凌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想说得事一定是有她的苦衷。而且这个苦衷一定是挑战了她的底线,因此永乐也不再逼问,等时间平复一切。
“洛姐,咱们又何尝不是苦命人?不过我们要懂得苦中作乐,你看现在我们还不用干活,你看小艾姑娘的手,本应是晶莹水润,可却皮糙肉厚,一定是吃了不少的苦。”
“是啊,我们还有馒头吃,听说那些最苦的劳役,吃得比猪都差。”
“胖花,你怎么三句话不离吃啊,真是怕了你了,你一定是个饿死鬼托生的。”
“永乐,你就别取笑我了,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这小艾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这么耗下去我都不敢想了!”
胖花虽说口中贪吃一些,可心底善良得一塌糊涂,她最看不得小鸟小兔一些小动物饿死病死,更何况一个活生生的人。
“永乐,你一直主意多,你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洛凌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她们三个中就属永乐主意多,在海阎王的船上就表现出来了。
“我心里比你们都急,毕竟是个大活人,我不能眼睁睁得看着她死去,可那麻三儿就是个活阎王,上次的经历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容我再想一想。”
一切似乎走进了一个不可逆的僵局,永乐也感到无能为力,总不能逃出去偷偷去找大夫,那更是死路一条。
雨花巷每天依旧宾客盈门,夕来夙归的人们饱尝百花芬芳,个个志得意满得潇洒离去,可雨花巷就静静地立在这里,红墙绿柳得等着他们再一次光临。
“李公子,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是不是心里有了别人,就忘了我们云螺了?”
“哎呀,真是冤枉,江妈妈莫要取笑小可,我最近为了写书走遍大江南北,近日刚刚返回泉州,就马不停蹄得来拜见云姑娘。”
日上三竿,雨花楼门前行人熙熙攘攘,还没到客人最多的时刻,一位布衣公子模样的人在门口又作揖又行礼,江翠花牛气冲天得笑得花枝乱颤。
这位公子姓李名恪,应天府人士,长期居住在泉州,是个开医馆的郎中。别看他年纪轻轻,名气可不小,在泉州短短行医三年,就得了个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的称号。
不过同行是冤家,李恪本事虽大,可一些老郎中看来,他的本事不会也罢,因为李恪最擅长得是妇女之疾,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妇科医生。
云螺乃雨花楼的头牌名伶,一些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特别垂青她的琴技舞艺。云螺的美无法言表,因为她不是那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可就是骨子里透着一种淡如水的魅力。长发及腰,飘飘洒洒,一双明眸,望穿世间百态。一颗真心,等待才子相倾。
按道理云螺和李恪本应一辈子没有交集,作为一名郎中,李恪十分不耻出没于风月场所,可偏偏云螺身体受了凉气,不住得落红,到最后气血两虚,琴也弹不了,舞也舞不动,逼得江翠花没了主意。
她从一位客人那里听说,西坊长善堂有一位名医,专治妇人的阴虚之疾,就带着云螺来瞧病。哪知病还没瞧好,李公子居然瞧上了云螺姑娘。
记得那是个良辰美景奈何天,秋月的霜露滴答在桂树的红叶之上,云螺静坐在纱幔后面,一只芊芊玉手呈现在李恪面前,令他心生讶异。
“多好看得一双手,简直比那如意翡翠还光滑三分。”
忽然一阵香风吹来,纱幔被风轻轻扶起,露出一张弱水三千只饮一瓢的俊脸,李恪公子当时就傻了眼,迷了心,着了魔,丢了魂。而云螺看着对面一张英俊潇洒的面容,不由得心生悸动,她在多少男人面前也不成有过如此感受,看着李恪她心中就会有莫名的紧张。
一见倾心,两手相抵,执指之手,与子成说。从那天开始,李恪像是长在了雨花楼一样,巴不得天天和云螺在一起。在他悉心呵护下,云螺这朵百花之王恢复了往日的气息,继续耀眼夺目得在舞台上释放自己的光芒。
光芒四射时,李恪却感觉自己根本配不上云螺,暗淡得心灰意冷,逐渐退出了这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游离四方,研究医药,著书立作也算为身后留些功名。
可他的心里对云螺一直是念念不忘,世上的病只有相思最无药可救,李恪治得好别人,却医不好自己,最后还是病入膏盲,来雨花楼找云螺来了。李恪满心期待得来,却在门口被江翠花堵了个正着。
“呵呵,我说李公子,这么些日子不见你人可消瘦了,快上去吧,这会儿云姑娘正在抚琴,你可真是好福气。”
自古只有相思泪,哪见离人心上秋。李恪内心忐忑不安得步上楼梯,刚登了一阶就听见远远吹来一阵飘渺的琴音和一声熟悉的佳人。
“梨花开,梨花落,梨花带雨春不归。盼君归,盼君还,日日思君不见君。心凄凄,影依依,昨夜星辰昨夜风。黄藤下,花柳间,沦落天涯人断肠。”
李恪闻听此音,心里像被一把大铁锤重重击打了一下,整个瞬间呼吸都停止了。向上攀登的脚步停止了,明明近在咫尺的佳人就在那里,可他又突然望而却步,不敢向前一丝一毫,好像前面有万丈深渊挡在他们之间。
“哎呦,我说李大公子,怎么这么会功夫还杵在这儿呢?我还以为你进屋了呢!你这龟性子真是急死妈妈我了。”
江翠花一声不合时宜的大吼,打断了李恪心中的无限遐想和困难重重。这声大吼不仅吓了李恪一跳,它也迎着琴音与歌声一句飞上了楼,惊得风中的仙阁瞬间安静了。
“哦,江妈妈,我忽然想起还有一个病人在等着我,我,我,我改天再来看她。”
说罢,李恪公子转身就要离开,忽听见楼上却落下来略带责怪的一句话。
“这么久没来,一来就要走了吗?”
李恪猛然转身,四目相对,才子佳人难再得,一股清流爱惜间。江翠华抿嘴一笑,冲这对儿佳人摇了摇头就知趣得离开了。
“云,云姑娘您还好吗?李恪这厢有礼了!”
“李公子请上来,妾身很久没为公子抚琴一曲,今日难得一见,就让我为您助助兴。”
李恪晃晃悠悠得上了楼去,他根本不想走,此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口不对心,这分别的日日夜夜每一天都像一个火炉一样煎熬着他的心。但一想到那个舞台上光芒万丈的仙女,再一想自己的家事,李恪就觉得有一座大山压在他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云螺浑身透着淡淡的清香,温柔似水的眼神里充满了责备但未有一丝哀怨,她心里明白,自己风月之人怎么会奢望李公子垂爱,即使勉强在一起,这世俗的眼光和舆论的大棒也会把她拍打得粉身碎骨。
“公子请坐,云螺给您沏茶,云螺还留着您最喜欢的白茶。”
只有在李恪面前,云螺才会显露乖巧的一面,豆蔻年华的她已经在俗世红尘中磨炼得刀枪不入,青春中透着老气横秋,淤泥中保持着一尘不染。
“云姑娘,别忙。我坐坐就走,我。”
李恪突然有些语无伦次,因为他看见云螺那张纯白的脸上已经挂了两行热泪。李恪已经起了火的内心立刻就被焚烧一空。
他失魂落魄得走过去,用手轻轻拂去云螺脸上的泪花,云螺则更加泪如泉涌,双手紧握住李恪温暖的大手,轻轻抚摸着自己如花美眷的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