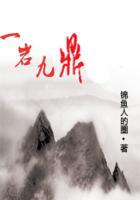东街小巷诚意堂门前,永乐正要逃跑,暂避烈火娃娃的锋芒。可刚走出一步就被旁人识出来,郭月红闻声一个激灵,风风火火地就冲向前方那道较小的背影。
“缩头乌龟你别跑,看老娘我今天怎么对付你,你!”
郭月红以为一个公子的体格怎么也应该比她高,因此她运气使力准备一道飞腿踢他娘的庸医一个人仰马翻。可一到近前才发现这公子生得比她还矮一些,体格比她家院子里那棵苦艾草还单薄,她这一脚下去恐怕对方能直接去阴间看病,因此心生犹豫。
永乐此时却感到背后生风,而且还是一道炽热的罡风,对方骂她是缩头乌龟也就罢了,可庸医可真就冤枉她了。自打接手诚意堂,虽然比不上爷爷那妙手回春,悬壶济世。可自己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替百姓排忧解难,为大明的和谐社会贡献了自己一份坚实的力量。
“庸医?这宝宝我可得问个明白,说个清楚。当着这么多人这是砸我招牌,毁我饭碗啊!我说你这个人,你!”
郭月红边冲边犹豫,腿没抬人倒是越冲越近。陈永乐忽然一个转身,挺胸抬头掐腰想质问一下这位姑娘,自己怎么就是个庸医了!
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永乐冷不防一个转身,就感觉自己眼前一黑。原来郭月红冲得实在太快,又犹犹豫豫不知该不该动粗,呼吸之间就与永乐几乎来了个零接触。
哇!围观群众各种表情,各种夸张,有的双手捂眼,有的大嘴飞张,有的痴傻呆方,有的兴高采烈。
此时此刻不能用难为情来形容这个画面,陈永乐与郭月红四目相对,两鼻相抵,烈焰红唇与雪白珍珠之间只隔一道理论上的虚妄。
“哎呦喂,今儿这热闹新鲜,刚才还破口大骂的,这会儿怎么还亲上了?”
“谁说不是呢!此情此景老夫平生也仅见,精彩,难忘,漂亮!”
在看当事双方,一个红着眼,一个红了脸。郭月红本就一身鲜红,这下连眼睛都血红如赤,整个人仿佛一块天然的红曜石,屹立不倒,一动不动。
“我这是亲上了还是没亲上?看这距离是亲上了,可我怎么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想当初和小月那可真是太美好了!”
永乐其实也脸红脖子粗的,只不过她自己看不见罢了。可此刻她的内心还算波澜不惊,毕竟大家都是女孩子,亲一下就亲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况现在这种情况并不能确定她们就亲上了。
永乐波澜不惊,郭月红可是翻江倒海了,从小到大虽然生得像个汉子,可内心深处她还是很想小鸟依人的,只不过没有遇到能把她这块钢啃了的硬角色。
不过很显然永乐并不是她内心深处渴望的类型,她中意高大威猛型,像庸医这瘦小枯干的柴火身,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
“咳咳,这位姑娘。你有事说事,恕乐失礼,不知您刚才如此气愤是所谓何事?庸医二字我乐某人可无法苟同,我。”
“啊!”
河东狮吼,河西的永乐实在是遭了殃。郭月红根本没在听永乐在那拽文词,烈火金刚一声愤怒的嚎叫,吹得永乐五官乾坤大挪移,眼白直翻。吹得众人四散飞逃,以为有妖怪吃人来了。
“竟然比我嗓门还大?”
噗通,永乐悲催地再一次晕倒,这次可真不怪她体质弱,就是一个七尺高的汉子在这也得被郭月红的一嗓子喷死,永乐就算不错了。
悠悠转醒,永乐发现自己在一个极为陌生的地方。东厅西厢,两道明窗,一张木榻,屋子里的陈设简单干净,颇有些返璞归真的味道。
而永乐显然并没有那么好运,这张仅有的木榻上空无一人,东厅内倒是隐约有三道人影,两个坐着,一个站着,好像都不约而同地看着她这个方向。直到此时永乐才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地上,坚硬冰冷的地面隔得她后背隐隐作痛。
“庸医,醒了?你这只缩头乌龟,怎么忽然变成条死鱼?在我家挺了半天尸,看你今儿怎么收场!哼!”
那团烈火金刚再一次出现在永乐眼前,愤怒的雾气,高亢的分贝震得她脑袋嗡嗡直响。听闻此言,永乐猛地起身,像一只受惊的兔子睁着比郭月红还大的眼睛迷茫地搜索着。
厅堂上坐着两个人,一位永乐认识,正是那日到诚意堂来瞧病的胖女人。另一位正襟危坐,面色肃穆,好似一尊石佛慑人心魄。不过此人也有明显的缺点,左腿僵直不能打弯,一把黑漆漆的铁拐置于身旁,明显是辅助步行之用。
厅堂上的匾额写着千秋正气四个明晃晃的大字,加上这位爷的威严模样,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
“婶,大婶?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倒是说说啊,我乐某就是有错也得做个明白人啊!”
胖女人愁容盖脸,嘴角边还挂着深深的泪痕,听闻永乐的发问,刚要开口就被一声惊雷打断。
“我来问你,前几日就是你给内子瞧的病?”
“正是在下,不知大叔你如何称呼?”
“庸医,少跟我爹套近乎,他不是你叔。告诉你,我爹是平安镖局的总镖头。”
郭月红急着抢话,面带骄傲,得意地望着永乐。可惜后者大眼瞪小眼,半天也没什么反应。
永乐知道哪个平安太平的,连琉璃坊中的医馆她都认不全呢。小得意遇到了小冷淡,郭月红眼巴巴地望着永乐,等待着对方能做出震惊的表情,最后只好以失败告终。
“庸医,你真是孤陋寡闻,怪不得你会这么缺德带冒烟的,真是气死我了!”
永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跟什么嘛。
“红儿!”
郭子阳一声喝止,示意她禁声,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要发话了。
“看你年纪轻轻,容貌也不是那奸诈之人,怎么行事如此卑劣?你算哪门子郎中,竟然挑拨别人家里的关系!”
说到这永乐突然如梦方醒,有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永乐唯一亏心的就是教唆人家中年妇女以毒攻毒,这才几天就报应不爽,人家正主找上门来质问自己,一时心中没了数。
“这位大嫂,我当时跟您只不过开个玩笑,您怎么还当真了?”
“乐公子,您可是远近闻名的和事佬,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大媒人。我可是仔细打听了,您医过的病人都是药到病除,不过您给我开得这个方子实属缺德,我一时鬼迷心窍听了你的话,现在我相公要休我,我一个人老珠黄的没人要,我,我不活了!”
“娘,您看您又来了。庸医,看你把我们家给搅和的,今儿你打算怎么办吧!”
永乐一下成了千夫所指,她突然感到有些恍惚,勿以恶小而为之,她真得打心底觉得自己错了。那天她实在是疲累至极,又感到腹中饥饿难耐。
她之所以这么努力的生活,全是为了能够撑起诚意堂,为了将来有那么一天爷爷刘基回来的时候,不至于连个熟识的门都没有。
其实永乐不知道她之所以一天到晚这么疲累,全拜那可恶的赖五所赐,黑了心的他拿永乐当成了一棵不倒的摇钱树,一劳永逸地榨取着她。
“首先,我道歉!”
永乐呆立了半天,冷不丁一个大鞠躬,吓得郭家三口人全都一愣。这还不算完,永乐连着三个深鞠躬,诚意满满,歉意多多。
“庸医,你,你光鞠躬有什么用?我们家都快被你祸害散了,呜哇!”
郭月红说话间小嘴一撇,咧开嘴哇哇大哭起来。一旁郭子阳气得头一扭不再言语,而李氏更是泣不成声,好像这一家人都委屈极了,就永乐不委屈。
“好了!够了!”
哭过三巡,泣过五味,永乐突然开口大声喝止,解铃还须系铃人,眼前纵是千难万难,小姑娘也要大无畏的迈过去,谁让这祸是她起的头呢!
“我承认我有错,可这件事归根结底你们也有错。”
一石激起千层浪,郭家三口本来表情各异,听永乐这么一说倒统一起来,三双眼睛直直瞪着永乐。
“你这是何意?难不成你拆散别人家庭还有理了?”
“郭老镖头,别误会。还请稍安勿躁,听乐某人细细道来。”
永乐似乎突然胸有成竹,那日李氏将自己心中的憋闷和盘托出,她是依稀记得真切。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我乐某人吃得就是这碗饭。我首先承认以毒攻毒这个疗法十分不妥,可依我看也确实有些效果。”
葫芦里卖药自己清楚,永乐侃侃而谈,郭家三口人闭口不言,只是安静地听着。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您二位是恩爱多年的老夫老妻。想必平时的关系也一定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庸医,这还用你说,我爹娘以前感情很好的!”
郭月红忍不住插嘴,惹得老两口又齐齐瞪她一眼。
“红儿姑娘这就对了,事出总有因,为何恩爱的夫妻会变成如此境遇?我想十有八九这里面有误会!”
永乐说得对,郭子阳夫妇心存芥蒂的最重要原因是老镖头夤夜出走,还不向妻子说明原因。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永乐听闻半天又思考左右,早就看出郭家这事根儿就在郭老镖头这,她抬头挺胸自信满满地望向郭子阳。
“郭老镖头,永乐有一事不明还请您如实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