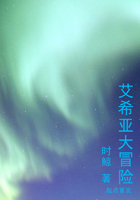这时,张家伟从柜内踱了出来,他双手抱拳,向牛二鞠了一躬说:“我早就听说二爷为人仗义,好打不平。只是我自己该死,没想到早些结识二爷。如果二爷是为了这个来问罪,那没说的,我认了;如果是有人借二爷对我不了解,想陷我于不义,那还请二爷明察。”他并不理会牛二瞪向自己的鹞眼,继续说,“他们诬我私藏了五百大洋,我到底藏没藏,建湘路的街坊邻居心里都清楚。我前妻取大洋是在火灾的头一天,我从合肥来长沙,到地时是火灾后的第二天上午。那时,我前妻已变成了一堆骨灰,她怎么还会把大洋交到我手里?”
“这么说,那五百大洋就这么凭空消失了?”牛二说着,起眼扫向刘成丰夫妇。
“的确有人惑疑,说是这笔钱被我岳父拿走了,”张家伟又把话接了过来,“可是,这儿的邻居可以证明,前妻取银之前,我岳父就已带着家人回到了这里,直到火灾发生之后,他们才赶过去的。”
“是呀,是呀,要是我们拿了这些大洋,不是让人说我们谋财害命吗?要是我们放火谋害了蒋姑娘——”刘妈说着,用手指了一下蒋奉楠,“那他大舅,还敢来我们家开布庄吗?”
“二爷呀,自家的事,自家清楚。我家姑娘行为偏激,就是因为财物被她公公婆婆拿去,这才做了傻事。”说到这里,越素贞又把蒋红梅自杀的原因讲了一遍,然后就说,“二爷请想,我家姑娘既是恨上了我姑爷家,况且已恨到了自杀的地步,她还会把大洋留给他们吗?”
“嗯,这……那这笔大洋,究竟谁拿去了呢?”
“二爷,这笔大洋,谁拿去了都不重要。那时前妻已把自己看成是个将死之人,或许用它还了个人债务——谁都知道,她是个麻将迷;也或许她随便送给了一些急需钱用的善人。”说到这里,张家伟俯下身,压低声音说,“可还有一笔钱,不知二爷感不感兴趣,这同样是五百大洋。”
“什么,还有五百大洋,这又是怎么回事?”牛二听得心里直痒痒。
“火灾之后,我在钱庄还存有三百大洋,被法院判为张声楚的房屋赔偿费。而这笔钱是不应该判给他的。”
“为什么?”
“因为那房屋是我的,不是他张声楚的。”
“既是你的,法院怎会判给他呢?”
“五年前,他还在湘潭做事,认为这房子自已无用,于是以两百大洋卖给了我,他也就不再是房主了。后来,他又拿了我三百大洋,这些加起来不是五百是什么?”
“你有证据吗?”
“问题就在这里,张声楚是算准了房契被烧,这才敢于伙同中人做假的。不过,只要二爷有心,这事不难澄清。”
“哦,说来听听!”牛二来了精神。
“我买房屋写字约那天,曾在万家楼请客,这酒楼老板和伙计可以作证。客人除了张声楚和中人外,还有代笔的戴老先生,还有那条街的街坊邻居。只要二爷向他们取证,这事保准能成。”
“难道以前法院没有取证?”
“法院?法院只怕早就被他打点好了!”说到法院,张家伟情绪又愤激起来。旋即,他又压住心中的愤怒,苦笑了一下说,“就算法院去取了证,可那时,谁愿为我这两手空空的外乡人讲话。二爷,如果是您老出面,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您说是不是?”
“你是让我替你找回那五百大洋?”
“不不!那大洋不属张声楚,同样也不是属于我的,它理应属于那些受了损失而未获赔偿的街邻,还可以作为澄清这件事的活动经费。”说到这里,张家伟又长叹一声说,“对于那些街邻,我是有愧的,等我们——大舅的生意有了起色,我向他……”
“这不用说,”蒋奉楠接过张家伟的话来,“只要小店生意有点起色,不论二爷对这事查没查清,我都一定重谢。只是张声楚为人阴损,怕只怕二爷您——”
“怕?怕个卵!他张声楚损,能损到老子头上来?老子虽然浑,但还是读过两年‘人之初’,也能讲几句‘学而’的。老子牛二不怕死,却也不会自己硬把脑袋往杨志刀口下送。”
“那是!那是!”蒋奉楠、张家伟及其家人,不住地对牛二点头赞许。
“他张声楚阴损,我牛二同样心狠手辣,只是欺善亏理之事,老子不屑去做。钱这东西,谁不想要?也要取之有道才对。”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最佩服二爷的地方!”又是一片称赞之声。
“二爷,我们家没有喝得酒的人,”越素贞说着,将几张现钞递给牛二,“无法陪伴您老喝,这点小意思,就孝敬您老拿去买点酒,同几个兄弟醉一醉。”
“不不不!”牛二站起身来表示拒绝,“无功不受禄,原来不明事情缘委,到这里打扰你们了,怎么还能收你们钱财?”
蒋奉楠从越素贞手中接过钱,又抓住牛二的手,硬把现钞塞在他手中说:“这是小意思,二爷不必见外,像我们这些远离家门在外谋生的人,还望二爷今后多多照料,怎能说无功不受禄的话呢!”
牛二拿了钱,不无尴尬地向众人抱了抱拳说:“那就不好意思了,今后有用得着我牛二的地方,尽管来找我!”
“一定,一定!”
“告辞,告辞!”
一家人送走牛二及其随从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