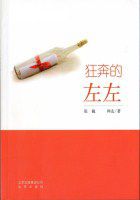陈一鸣并不介意地笑了笑:“我是慕名来看望飞贼燕子六的……如果不是我的人出手,恐怕还真让你跑掉了。说实话,你的功夫不错,可惜走的不是正道。”
“正道?什么正道?少废话!说,你到底想干什么?”燕子六说完,鄙夷地看着陈一鸣。
陈一鸣沉默了一会儿,正色道:“我今天来是和你谈一件正事,也是关系到你命运的大事儿……”
“我的命运?”燕子六不耐烦地打断了陈一鸣的话,“少在这儿给我说那些没用的,有什么屁话,你直说!”
陈一鸣没有理睬燕子六的无理,继续平静地说道:“我看你一身好功夫,想保你出来,为抗战效力。”
燕子六问:“保我出来……干什么?要我给你们军统干特务?”
陈一鸣没有正面回答他,接着说:“我知道你娘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来找你,为的就是杀鬼子。”
“哼!”燕子六不屑地瞪了陈一鸣一眼,“杀鬼子老子自己会杀,犯不着给你们这些狗特务卖命……快滚吧!”
陈一鸣没有理睬他,继续说:“我给你两个选择。”
燕子六:“哦?……给老子说来听听,看你们到底有什么牛黄狗宝?”
陈一鸣又照着以前的方法拿出一张特赦令:“这一张是你的特赦令……日期上是空白,签上就可以生效。”
“呸,老子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份儿孝心!”燕子六说罢一口唾沫,吐在陈一鸣的脸上。
冷锋气恼:“你……”
冷锋见状欲伸手,陈一鸣拦住了他:“燕子六,我这里还有一张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令,只要我签了字,即刻就能生效……”
谁知燕子六并不屈服,竟狂妄地笑了起来:“哈……狗日的,吓唬孙子哪?枪毙我吧,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放心吧,老子是不会给你们军统卖命的!”
陈一鸣脸上的表情渐渐地严肃起来,他猛地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贴着燕子六的脸皮在慢慢地滑动:“燕子六,这把匕首属于尖刀中的极品,是德国最好的刀剑工程师设计的,用最好的工人、最好的材质手工打造,它削铁如泥,锋利无比——是我的部下在德国狙击手学校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送给他的纪念品。”
陈一鸣说着,将匕首顺着燕子六的脸、脖子、前胸……向下滑去,直至停在燕子六的裤腰上。
陈一鸣缓缓地说:“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有一种痛楚叫作生不如死……”
陈一鸣说着一挑匕首,燕子六的腰带瞬间断裂了,燕子六的裤子一下子落了下来……燕子六立刻惊呆了!
燕子六惊道:“你……你要干什么?!”
陈一鸣笑了笑:“不干什么……辛亥革命以前还是封建皇朝,那时候宫里都有宦官,也就是太监——”
陈一鸣话没说完,燕子六头上的汗珠就渗了出来:“你……你别胡来!”
陈一鸣不理睬他,继续说:“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受了宫刑而做出了伟大成就,比如司马迁……”
燕子六头上的汗珠顿时像雨一样流了下来:“你……你可别胡来呀?我……我犯的是国法,你不能滥用私刑,胡作非为!”
“哼!”陈一鸣冷笑了一下,“你别忘了,军统一向都是滥用私刑,胡作非为的。”
陈一鸣说罢,手中的匕首往下动了动——
“不,不——你还不如杀了我!杀了我!”燕子六杀猪般地大喊起来。
陈一鸣没有说话,却猛地挑开了燕子六的裤衩!
“啊——别割,别割!狗日的,我干!我干!快把这该死的刀子拿开,给我拿开——”燕子六用尽全身力气大叫起来。
陈一鸣忍不住笑了:“你要是早就痛快点答应,就不用受这份儿罪了。”
“哼!”燕子六气愤地瞪了陈一鸣一眼。
9
集中营里,早晨的阳光洒满了集中营。操场上,一名叫作“书生”的囚犯正跟着囚犯们一起在操场上放风。
岗楼上,冷锋放下望远镜望着陈一鸣:“你要找的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
陈一鸣说:“就是这个书生。”
冷锋:“看上去是个文弱书生,不像是个练家子。”
陈一鸣很有兴趣地望着正在操场上散步的书生:“他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后来在日本帝国大学建筑系读的硕士,被关进来以前在国民政府建设部担任工程师。”
冷锋望着书生,不禁冷笑了一下:“还真跟他的名字一样,是个书生!哎,你挑他来做什么?”
陈一鸣吁了口气:“他懂爆破,又懂日语,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两样都具备的人才呢?走吧,我们去见见这个书生。”
几分钟以后,在集中营的审讯室里,书生被战战兢兢地带了进来。
陈一鸣和冷锋此时坐在预审桌前,凝神地看着他。
书生:“长官好,8621号奉命来到。”
“坐吧。”陈一鸣挥手示意了一下,书生小心地坐了下来。
“郑月枫。”陈一鸣突然说了一句。
书生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陈一鸣严肃地看着他:“你不叫郑月枫吗?”
书生似有些恍然大悟地站了起来:“长官,8621号罪该万死!8621号囚禁已有三年,只有一个名字,就是8621……请长官恕罪。”
冷锋有些蔑视地看着他:“行了行了,坐下吧……没出息的德行!”
陈一鸣看着书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书生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陈一鸣说:“书生,你不要害怕,我们找你来就是跟你聊聊。”
“是。”书生答应了一声,擦了擦头上的汗。
陈一鸣接着说:“书生,我看了你的资料。你本来是政府的公务员,优秀的建筑工程师,为什么被抓进来的?”
“报告。因为共党嫌疑,被军统局长官秘密关押至今。”书生说着,又站起身来。
冷锋向书生挥了挥手:“你坐,坐……你有共党嫌疑?”
书生应道:“是。我的大学同窗误入歧途,加入共党,为共党做地下工作。我因为愚昧,不知道他的叛逆身份,便与他小聚。本以为是寻常同窗聚会,不料却被军统长官早已查明,他们冲入饭店实施逮捕,共党分子意图逃逸,被乱枪击毙;我被军统长官抓住带到了这里,至今已经有三年了……”
书生说完,竟委屈地哭了起来。
陈一鸣没有说话,冷静地观察着他。
冷锋却有些不耐烦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就你这样的软蛋,我看着就不像共党……瞧你这熊样子,就不带能打仗的架儿?”
“啊?打仗?”书生听罢,吃惊地站了起来。
陈一鸣向他挥了挥手:“你坐下……我问你,你精通日语?”
书生回答:“哦,本人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文略知一二。”
陈一鸣:“你精通爆破技术?”
书生有些谦虚:“谈不上精通,只是由于专业,有所接触。”
“说你精通你就精通,瞎啰唆什么?!”冷锋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书生急忙站了起来:“是是,8621号冒失,冒失……”
陈一鸣慢慢地站起来,走了过去,拍拍书生的肩膀:“我知道你受了冤枉,我们没有恶意,你只须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陈一鸣说着踱了几步,又停了下来:“8621号,我仔细查阅了你的资料,也跟负责你专案的官员做了接触,他们也一致认为你是个倒霉蛋——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会见了错误的对象。”
书生没有回答,在思索着。
陈一鸣突然话锋一转:“但是,你在这里也待了三年,应该知道这儿的规矩。”
“是是。”书生又赶紧站了起来。
陈一鸣又拍拍他的肩,让他坐下:“我在你对面也关了四年……”
书生听罢,仿佛惊讶地抬起头来。
陈一鸣望着他笑了:“别装作不认识,每天放风……我们都能见到。”
书生的脸上现出尴尬的笑容:“长官气宇轩昂,8621……不敢想。”
“呵呵……”陈一鸣又笑了,“8621,你不用客气了,我们都是难友。既然都在这儿待过,规矩我们都不陌生。息烽集中营——只许进,不许出。这里被冤枉的人不在少数,可出去的人却寥寥无几,如果没有老天怜悯,怕都要烂死在集中营了。”
书生听着,不禁眼里流出泪来。
陈一鸣走过去,又拍拍他的肩膀:“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出去。”
书生愣了一下,立刻站起身来:“长官?!”
陈一鸣转过头来,直视着书生的眼睛:“参加我的队伍,去打日本人!”
书生呆呆地看着陈一鸣,看样子像是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你不敢?”陈一鸣追问了一句。
书生摇摇头:“不,8621只是不明白,我手无缚鸡之力,能参加军队吗?”
“不是军队,是军统。”陈一鸣更正了他一句。
书生更愣了。
陈一鸣拉过一把椅子,索性坐到书生的跟前:“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反感军统的胡作非为,但是除了参加军统的特务工作,我没有抗日的机会。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党国培养多年的军人。”
书生注意地听着,琢磨着。
陈一鸣继续说:“我想抗日,可是没有选择;你想出去,也没有选择——你说说吧,你干,还是不干?”
书生突然哆嗦一下:“长官,我……”
陈一鸣打断了书生的话:“我知道你是个胆小的工程师,这辈子就没想过会参加特务工作,所以,我不勉强你……但是,为了能拉起这支队伍,我必须逼着你跟我干!”
书生:“长官,我……我……”
陈一鸣:“8621号,你应该明白,在这个集中营里无论死了谁,都不可能有人过问。你我都去埋过被枪决的尸体,他们都没有等到法庭审判,就被作为共党嫌疑给枪杀了。如果你不抓住这次机会,谁也不能保证哪一天——”
陈一鸣话没说完,书生突然拦住了他的话:“长官,你建立这支队伍只为了打鬼子吗?”
陈一鸣:“是的,起码目前,我认为是的!”
“那……我跟你们干!”书生终于下了决心。
10
黄昏,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地处重庆郊外的日军战俘营。
战俘营内,几十名穿着没有标志的日本军装的日军战俘被圈在铁丝网里面,其中有几个是残疾人。在战俘营的另一侧,关押着近百名的日本侨民,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其中很多人是妇女和儿童。
此时,穿着破旧飞行服的被俘日本军官藤原刚正坐在草地上懒悠悠地吹着口琴……口琴吹得不连贯,却带着明显的伤感情调。
陈一鸣和冷锋健步从吉普车上走了下来……站在战俘营门口的国民党宪兵见状,赶紧迎上来敬礼并示意检查证件;陈一鸣把证件交给了宪兵。
冷锋打量里面,悄声问陈一鸣:“这儿关了多少日本鬼子?”
陈一鸣:“官方资料记载,这里关了47名日军战俘、96名日本侨民。”
“报告长官,请!”宪兵把证件还给了他们,并礼貌地请他们进去了。
冷锋一边往里走,一边恨恨地望着日本战俘:“他妈的,都应该给老子当活靶子用!”
陈一鸣苦笑了一下:“痛快痛快嘴可以,真要做可不行……根据《日内瓦公约》,放下武器的战俘生命和安全应该得到对方的保护。”
“哼,南京陷落的时候,日本鬼子杀了我们多少无辜百姓,他们怎么不跟我们讲《日内瓦公约》?!”冷锋仍然仇恨地望着眼前的日军战俘,冷冷地回了一句。
陈一鸣低声说:“因为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两个人说着走进了战俘营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又在战俘营管理人员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们去的方向是正在吹口琴的藤原刚。
“你就是藤原刚?”陈一鸣说着,站在了藤原刚面前。
藤原刚立刻站了起来,他不敢抬头,汉语说得却很流利:“报告长官,战俘藤原刚,日本陆军航空队第十五战斗机联队中尉飞行员,战俘营编号187。”
“跟我来吧,我有话对你说。”陈一鸣说完,在前头先走。
藤原刚哆哆嗦嗦地跟在后面。
此时,在四周的日军战俘不知面临藤原刚的是什么命运,也同时担心悲剧的命运不知何时会降临在自己头上,所以都心情复杂地看着陈一鸣和藤原刚。
冷锋见了不禁骂了一句:“他妈的,都看什么?被抓起来了还不老实呀!再不老实,老子拿机枪把你们一个个都突突了!”
冷锋一骂,那些转过头来的日本战俘都吓得立刻转过了脸去,冷锋这才觉得自己被怒火挤压的心稍稍松快了一点儿。
此刻,在铁丝网的另一边,站着一位身材消瘦的日本老人,正浑身哆嗦着担心地望着陈一鸣和藤原刚。
陈一鸣不禁问了藤原刚一句:“那个女人是谁?”
“我母亲。”藤原刚轻声回答。
“哦……”陈一鸣应了一声,带着藤原刚进了战俘营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