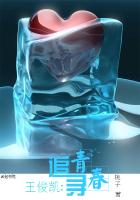山庄里近来平静地出奇.
我有些不安.
太平静了,好似暴风雨的前夕.
翎如踱进我的玲珑阁,坐在窗前兀自把玩手里的团扇.扇面上一只赤红的小鸟栩栩如生,好似活的一般.
"怎么了?看你心事重重,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
"很顺利,可太顺利了,让我不安."
"你也有这样感觉?我也是,不知为何,这几天总觉得烦躁的很,好似有种不大好的预感."
她突然回过头来,"也许我们真的不该再拖了,尽早搞定也尽早安心."
我沉吟,托起灵鹊刚刚拿进来的燕窝,"让我再想想."
"想什么?觉得不忍心?"
我没有看她,"最近我一直在想,是不是真的非要走上这一步不可."
她笑起来,"就知道你会这样,如果你现在说收手,也不是来不及,只是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再想重来,只怕不会再这么容易."
"我知道."不觉有些失笑,"不知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我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并没有想像中那般狠心."
"可是在这种地方,向来都是不是别人死,就是我们亡."
我看了眼那碗中的燕窝,腻答答的香气扑鼻而来,竟有些反胃.我求救地看向灵鹊,"可不可以不吃这东西?每天都是同样的东西我已经吃了差不多十年,换个别的成吗?"
灵鹊笑起来,"我的好小姐,这可是老爷去世的时候亲口吩咐的,不能断.你自己身子弱,再不好好保养只怕禁不起那么多事情的折腾."
翎如也笑,"你就忍了吧,看叔父多疼你,都过世了还惦记着,这心意可辜负不得."
我重重皱起眉头,扁着嘴拿起羹匙,突然一个红色的影子在眼前一闪,手一时不稳,好好一碗燕窝啪地摔在地上,只听一声脆响,白瓷的碗砸在地上,登时碎裂.
原来是翎如的那只丝丝不知何时竟从窗口飞了进来,径直落在我的肩上.我不气反笑,"瞧见没,连它都知道我讨厌那东西呢."
翎如皱眉,灵鹊却笑起来,嘴里念着这小东西,然后俯身去收拾瓷碗碎片.我让丝丝落到我手心里,怜爱地抚着它通身鲜艳的羽毛,唧唧咕咕地逗着它玩,却听见灵鹊突然啊的一声尖叫.
我和翎如同时看过去,顿时面如土色.
那被打翻的燕窝落在地上竟瞬间腐蚀了木制的地面,咝咝泛起沫来.
灵鹊蹬蹬几步退了开去,面色比我还要苍白.
这燕窝,竟是被人投了毒.
我嘴唇铁青,手心沁出汗,缓缓自椅子里站了起来.
丝丝仿佛觉出不妥,腾地飞到窗边落在窗栏上,瞪着漆黑的小眼珠不错地望着我.
这鸟,倒救了我的命.
我紧咬银牙,灵鹊瑟瑟看着我,说出的话已经不成句子,"小姐,我,我...这燕窝...."
我摇了摇手,示意她不必再说,抬起头去发现容容的祖母正站在门口,愣愣地看着我,一脸担忧.
我什么都没说,和她擦身,走了出去.
天阴沉沉的,秋风瑟瑟.我的心,却滞闷地仿佛要滴出血来.
"有人要置你于死地."
我没有回头,仰着脸注视天空,风吹在我的脸上,吹乱我一头长发,也吹乱了这山庄短暂的安宁.容容祖母的声音仿佛自天边缓缓飘来,虚无的好似梦境.
"这样大的一个家庭,让人心烦的事情也很多吧?"
我冷笑,"何止多?倘若一个不小心都要送命."
"小姐这么好的一个人,什么人会想要你的命?"
"好心?"我回头冷冷看她,"不要以为我收留了你们祖孙就可以算做是个好人,好人,在这样一个地方根本不可能存在."
"可我感激你,没有你的出手相助,我不知道剩下的这些日子和容容会是怎样度过."
她的汉语说得甚是吃力,可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她一番真诚.
"谢谢,能够被人夸奖总还是好事."我沉吟起来,"只是不知让你们住进来究竟是好是坏."
她突然一脸坚定,原本混浊的双眼也霎时清亮起来,"也许,我可以帮你."
"帮我?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我不懂得如何救人,可我知道如何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
"要人性命?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她一脸郑重,"倘若不能保证自己安全,就彻底根除那危险."
我冷冷看住她,半晌才听到自己冰冷的声音,"谢谢你的好意,可我的境地,还不至于是你所想的那样."
她却兀自说下去,"在我生活的地方有一种血咒,将九百九十九朵丁香花瓣缠住一个人的头发打成七七四十九个死结绕成花伞,用自己的中指之血将花伞养满七天,然后戴在那人头上,那戴花之人便会在三日内七孔流血而死,而灵魂也会随之禁锢.至于禁锢时间有多长,则要看你的诅咒有多久."
我看着她,她却微笑起来,"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方法,至于用或不用,则要看你.这是我能够报答你的惟一方式."
然后姗姗离去.
走出几步却又回过头来,"对了,倘若想要让那灵魂被禁锢的久一点,那花瓣就定要是千年不败的品种,听说中土有个苏州,那里的丁香寺是此种丁香惟一产地."
不知为何,有那样一刹那,我竟会觉得她的笑容竟是如此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