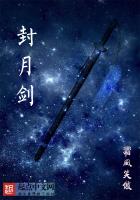这堂中弟子,其实对这段仙史早已熟知,然听牛仙教说得真切,便都倾耳细听。独莫羽非初闻此事,一时间,更觉惊心动魄,热血四涌!且一想及母亲被黑电妖重伤,自己亦背负着玉修之徒的恶名,他内心早已同黑欲王势不两立。且近来他更知仙界危机与鸿鹄弟子之重任,由此更加笃定与黑欲王对抗之心!
“牛仙教,若是炼就紫品仙力,便能跟黑欲王相抗么?”金宝忽大声道。
“紫品?”牛仙教一惊,摇头叹道:“黑欲王的魔力早已超出色品范畴了。”
“那是何意?”金宝那双小单眼直瞪着牛仙教。
“便是没有颜色么?”左机疑道。
“这……”牛仙教微一沉吟,道:“史书上对其魔力虽有记载,却也说法不一,有说其仙气看似无色,实则包含七种颜色,且每种颜色相生相助,故仙力越战越强!”
“还有说他炼就的是‘无穷紫极功’!”范庠忽接口道。
“嗯,确有此说!”牛仙教点了点头,范庠便得意一笑。
“那可远胜紫品仙力了。”严昉皱眉道。
“比掌院仙博玉玄子还厉害?”赫连涛惊道。
“那自然!”范庠忽笑道。
“你却乐什么?”赫连涛眉头一皱:“莫非正邪不辨?”
“我又不是……”范庠本欲辩解,却见赫连涛忽转脸不理。其实范庠只笑赫连涛不知那“紫极功”之厉害,然他言中之意却像是赞叹黑欲王更胜一筹了。
“罢,罢,莫作那些口舌之争了!”牛仙教挥了挥掌,道:“诸位知道,那紫品本已是我仙气修炼的最高级别,然‘紫极功’却突破紫品,再起幻变!只是仙城之中,能炼就紫品者已是凤毛麟角,若说突破,却还无人。而史上说黑欲王功成之后,其紫气之中更有七色,七色之中又生演变,如此增递,无穷匮也!此等魔力,实非我仙城之人所能及啊!”牛仙教话到此处,不禁悲从中来。
“牛仙教,那黑欲王怎就炼成了‘紫极功’?”左机忽道。四下无声,左机的话语便空荡在堂中。
牛仙教眉头一皱,半响方道:“他乃以妖邪之法……”
“是何妖邪之法?”金宝急道。
牛仙教看了看堂中弟子,见其眼神清亮,尚显稚气,不禁心道:“那方法凶残,大逆仙规,我若说与弟子们听了,实是不妥!”于是道:“那方法有背仙规,听了污耳,尔等也莫再问了。”
“黑欲王当真炼就‘紫极功’了?”金宝忽又疑道。他如今仙力刚过黄品,且还是在其母督练下勉强所得,故觉紫品高深莫测,遥不可及。
“据史书所载,他当年偷盗冰玉宝时,便是以此功与仙姑相抗的!”牛仙教道。
“可他还是败了呀!”金宝眼中流出一丝笑意。
“但他却令冰玉宝四分五裂。”牛仙教难过道。
“那就重拯冰玉宝呀!”金宝拍桌道。
“夯货,说得容易!”赫连涛鼻中一哼,嘲道。
“好,很好……”牛仙教声音低哑,却渐有笑意,道:“此路漫漫,其途艰险,却愿尔等能锲而不舍,终是将之复原啊!”
“那日后我鸿鹄弟子便可名留史册了!”范庠不觉笑道。
“哼,野史当中或能记你一笔!”赫连涛笑道。
莫羽非却眼神清冷,毫无笑意,心道:“不料黑欲王竟已魔高至此,竟连掌院仙博也逊他一筹!且他麾下之徒也自劲猛,我现与之相抗,便是蚍蜉撼树,自取灭亡,但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正邪之间势不两立,看来我也只好韬光养晦,再伺机而动了!”
“莫师弟,你又绷着脸作甚?”赫连涛见莫羽非兀自沉思,便道。
莫羽非斜了他一眼,却不说话。
“咳,别那么心忧!虽说救宝重要,却也不在这两日,再说三城联手也难敌黑欲王,更何况你我之辈?”赫连涛只摇头道。
“赫连兄,正因如此,冰玉宝才岌岌可危啊!师兄可想过,黑欲王对冰玉宝虎视眈眈,志在必得,我等若懈怠一尺,他必将更进十丈!而我辈仙力青涩,比之有如云壤,这叫人如何不急?”莫羽非压低了嗓子,却压不住急躁。
“啊呀,你两别争了,牛仙教正讲凡尘女子救电龙那段呢!”丘子语就近敲了下赫连涛。
莫羽非一听“凡尘”二字,不觉身子一震,便听牛仙教道:“……这姑娘虽是凡尘中人,却十分大胆。你想那电龙何等凶矫?便是修仙驯兽之人看了也是心惊!”
“到底何等模样?”金宝奇道。
“那《仙国春秋》上便有描述,说是:‘银蛇腾空光满天,雪涛霜浪戏作伴,金爪倒钩雨倾盆,电光忽闪雷霆唤!’”牛仙教道。
“哦!”莫羽非便想起灵禽语课本上见到的绿眼电龙。
又听牛仙教续道:“彼时那电龙因被歹人所伤,躺在岸边昏迷不醒,那姑娘便按凡尘之道,为其清洗伤口,挤出恶血,又再包扎。谁知那电龙一时醒来,竟误将姑娘当做歹人,暴怒之下,便以电爪袭之。它一招既出,忽觉不对,察己伤口,才知姑娘原是好心救它,然此时那姑娘却已受了电伤,流血不止,电龙以涎封之,却也无效,心悔之下,忙磕头三下,以示歉疚,随后便潜入湖底欲请龙父出海相救,然它父子同来时,那姑娘却已不知去向了。”
“这不是牧夫人救龙的故事么?我曾在《仙国史话》中看过!”赫连涛听罢说道。
“只是史书中却不如牛仙教讲得详尽。”严昉道。
“这到底是故事还是史实哪?”左机不觉疑道。
“这可是事实!”莫羽非忽大声道。
众弟子一惊,不觉纷纷看着莫羽非,他这才觉自己有些突兀。
“莫师弟,也竟知这段?”赫连涛笑道。他本以为莫羽非对仙史毫无知晓呢。
“这故事便是三岁小儿也听过,又有甚稀奇?”范庠不甘落后,便夸大其词道。
“可却未必知其来龙去脉,多是人云亦云罢了!”丘子语见其说得不屑,便心有不忿。
“故学史者,定要严谨,更应具备考证之态,否则仙史茫茫,浩如长河,尔等若轻率对之,不仅难以借史知兴衰、明事理,反会为其所惑,迷失方向!”牛仙教郑重道。
严昉听罢,不觉点头,忽却道:“敢问牛仙教,这牧夫人后来可是留居仙城了?”
“这……史书上却未有记载,便不得而知了。”牛仙教摇头道。
“她没有留在仙城!”莫羽非忽断然道。
“你怎得知?”牛仙教不觉愕然。
莫羽非看了眼堂中众人,心道:“我若说得多了,岂不惹人疑心?便此打住罢。”于是淡道:“我曾听人说过。”
“哎,这牧夫人也是不易,”牛仙教叹了口气,“却不愧奇女子哪!”
莫羽非听牛仙教此说,不觉心生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