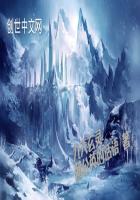用完午膳,莫羽非终于答应赫连涛去光阴湖一看。
两人按路标所指,行了有半盏茶时分,便见不远处一幽黑的湖泊。湖上有一小岛,显得有些荒凉。
越近光阴湖,赫连涛越觉不对,只皱眉问莫羽非:“你可闻到腥味儿?”
“有点儿。”莫羽非淡淡道。
“要不……咱们走罢。”赫连涛恰因刚才饱食了一顿,此刻便觉胃中不适。
“就走?你不是闹着来么?”莫羽非笑道。赫连涛不觉有些尴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
到了湖边,莫羽非放眼望去,只见那暗黑的湖面冷气森森,却不见波光,远处仅有两只小船,船上的人似正忙着打捞黑藻。近处湖面,灰绿的水上飘着细长的黑藻,散出阵阵腥臭。
见此情景,莫羽非不觉心道:“鸿鹄的惩罚还真够狠的!”
正想着,却见交缠的黑藻间冒了几个泡。
赫连涛见了,胃上又是一阵翻腾,忙捂嘴道:“走吧!受不了了!”
莫羽非不觉一笑,却忽听水泡“噗噗”声响,不禁猛然回头。
忽然间,他感到一些异样。他似乎听到一种声响……仔细听,更像一种低哑的声音。
“莫师弟,你还在那儿作甚?”赫连涛早已跑至林中,远远喊道。
然那低微而沙哑的声音却如磁石般,吸住了莫羽非。他感觉那声音像是来自湖下,但很难听清其到底说了什么。
“莫羽非,我可要走了!”赫连涛急道。
“来了!”莫羽非转身叫道。
然刚跑出几步,却听那湖底声音道:“……你别走……”
他只觉一股寒气直灌脊背。
赫连涛见他又有迟疑,索性跑了来,拉起他就跑。莫羽非却一把拽住赫连涛道:“你听!”
“到这儿来吧……”低哑的声音再次传来。
赫连涛却捂鼻道:“哎呀!我快被熏死了!有什么可听的?”
“你没听到么?”莫羽非惊道,“它说——”
“咳,快走!”赫连涛拽着莫羽非,一面走,一面想:“我看这湖是有些诡异。”
两人跑出树林,方停下喘气。
“真没料到那腥臭如此了得!”赫连涛长舒了口气道。
莫羽非的耳畔却仍回响着那低哑的声音,因想:“难道那湖下有人?”
“你在琢磨什么?”赫连涛见他若有所思,便问。
“你刚才真没听到什么?”莫羽非忍不住问道。
赫连涛心下一跳,却笑道:“我看你是被那黑藻熏昏了头吧?”
莫羽非不觉蹙眉,心想:“那声音如此真切,怎会听错?”
累了大半日两人也乏了,两人便朝寝舍走去。那寝舍隐于半山腰上,赫连涛因知道山间有个索桥,便提议走索桥,莫羽非一听快捷,随即答应。
********
原来索桥虽是快捷,却暗藏机关。弟子的见性眼若是功力不够,便难以辨别其上的“笑穴”。莫、涛二人上去后,明见警告:“恐高勿行,眼拙勿过”,却还是奇心大盛,走了上去。
谁知桥上风大,赫连涛迎风一吹,刚才的积食便难耐了;莫羽非又因不知陷阱所在,走出几步,便踩在了“笑穴”上,一时间,桥动人摇,赫连涛几欲作呕。
他俩这番顽皮之举,立时便被绿珠仙导发现了。
却说走在山路上的弟子,忽见头顶一亮,禁不住抬头仰望,原是绿珠仙导拨云显身。
几个银代弟子,因仙力高强,只用“海鹰眼”一望,立时便看到了索桥上站着三人。
“师哥你瞧,那不是绿珠仙导么?”一瘦高弟子道。
“那两个弟子好运了。”那师哥讥道。
这时恰有一面皮白净的青衣弟子走了来,见他两人正看得起劲,便也手搭凉篷,抬眼一望,这人正是范庠。他见山间悬有一桥,上面似有三个黑点,但却看不分明。
那师弟又道:“看来像是新弟子,才会冒闯索桥啊。”
“却不知‘绿仙’又要怎样罚人!”
“只要不罚光阴湖就好。”那师弟叹道。
范庠却暗想:“也不知多差劲,才会被罚守光阴湖!”转念间,又心奇那索桥,便笑着上前道:“请问两位师兄,那桥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人见他生的干净,言语又客气,便道:“那是倩影索桥,桥上有九处笑穴!”
“那‘笑穴’又是何物?”范庠追问道。
“你是新弟子罢?”
“在下正是。”范庠客气道。
那弟子便给他大略说了,他听罢别过,却边走边想:“世上怎有那样顽劣之人,好好的山路不走,却偏要寻些古怪?”
待行至山腰,终于见到林立的古朴楼殿,外面拱门匾上乃是“静怡仙园”四字。
进去后,他便直奔“敛神居”而去。
那门口立着只蓝顶仙鹤,便听鹤道:“请出示仙舍牌。”
范庠便拿出那刻字的木牌来。
“过!”鹤道。
进了敛神居,找到铁代弟子所在的画楼,他被分在第五层。
到了寝舍门前,他将仙舍牌在鱼形铜锁上一过,只见门锁顿亮,他忙推门而入。
鸿鹄弟子乃三人一间,范庠进去后,见同屋的另两人还没到。
寝舍有一间书房,三间卧房,书房中设有玉檀书架、珊瑚桌、月光烛,一进卧房,便见檀木床,鲛人幔,范庠惊喜之余,一看桌上沙漏,不觉奇道:“那两人怎还不来?”
便此时,却听门外有人大声道:“今儿算我晦气,又被减分!”
“是谁?”范庠走出卧房,惊道。
那推门之人正是赫连涛,他大喇喇进了屋,其后便是莫羽非。
“哦,咱们同寝啊?”范庠惊道。
莫羽非点头一笑,赫连涛却还在抱怨刚才被罚之事。
范庠一听,不觉暗惊:“原来索桥之上竟是他俩!”便觉他两太不安分,因问:“你两去那桥上做什么?”
“从桥上走,快得多啊。”赫连涛不耐烦道。
“铁代弟子,不易过罢。”范庠小声道。
赫连涛本就有气,不觉恼道:“还不是过来了!”
“但却被罚了呀。”范庠嗫嚅道。
“谁说的?”赫连涛怒道。
范庠一怔,“你呀,你不是抱怨么?”
“你倒听得仔细!”赫连涛气道。
范庠见了,不禁暗忧:“此人如此暴躁,与之同室,真是为难!”
莫羽非见他两人龃龉,本想一劝,却忽觉头痛,心想多半刚才桥上风大,他伤未痊愈,故觉不适。于是便在珊瑚桌边坐了下来。
范庠只管仔细整理他的书籍物事,赫连涛心中不快,便转身进了自己的卧房,猛然将门关了。
莫羽非正想倒杯茶喝,忽觉一股异香扑鼻,因想:“这不是刚才那汤味儿么?”这异香让他想起了仙馔馆的那道“学海泛舟”。
“范师哥,这是什么香?”莫羽非奇道。
“这个?”范庠晃了晃手中淡蓝的小草,“这叫天姥草。”范庠得意一笑。
莫羽非却越觉那异香令他头疼,便想避开。
“怎么?你不喜欢?”范庠奇道,“这天姥草乃仙境奇草,数十年长成,我娘百般托人方才得到,遂给我做了个香囊,佩在身上,既驱邪,又避晦。”
莫羽非听了,却愈觉头痛,忙辞了范庠,转进自己卧房,再又运气调息以镇痛。不多时,便觉头顶热气渐出,背上汗湿,痛遂稍缓。疲乏下,便合衣睡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忽被敲门声震醒,一听是赫连涛在外道:“睡了么?”
莫羽非便叫他进去。
一进屋,赫连涛见莫羽非两腮带赤,面色憔悴,不觉惊道:“你发热了?”说时便试其额头,果然滚烫。于是道:“不妙!是吹寒风坏的事么?”
“我也不知。”莫羽非摇头道。
“看来我兄弟两还要病在一处哪,我今儿吐了,你便定要发烧!”
莫羽非不觉一哂。
赫连涛见其难受,不觉皱眉:“你这样子,怎么参加明天的伞神大典?”
莫羽非摇了摇头,忽道:“怎么又有天姥草的味道?”
赫连涛一吸鼻子,“啊,是那香汤!”
莫羽非却觉头顶跳痛,因说:“定是那香囊……赫连兄,你快去看看!若是……范师哥那香囊,你且请他先收起来,我实在受不了那气味!”
赫连涛见状,只暗呼怪事,便往范庠那屋走去。越近其屋,越觉那香气浓烈,心想范庠难道在屋中暗煲香汤?
走到门前,敲了两下,却不得回应。
原来范庠为了明日迎伞之事,早用了晚膳,此时正自盆中沐浴!他为显恭敬,便特意用那天姥草点了浴汤,那仙草遇热便气味浓烈,故此时只熏得满屋皆是!
范庠锁了门在里间舒坦,哪还听得外间敲门?直到那门山响,他才惊道:“哪儿的促狭鬼,此时却来捣乱!”只听外面叫道:“你个兔崽子,再不出来,我便闯进来!”分明便是赫连涛。
“就来了!”范庠吓了跳,忙着穿衣,心里却骂:“他来做什么?”
其实赫连涛适才敲了两下,见无人应,便折身回去,然一见莫羽非因那香气头疼欲裂,才又来催着范庠开门,心想那仙草或是有毒!
“范庠,开门!你在里面倒腾什么?”赫连涛急道。
范庠一时心急,衣衫却又穿反了。他心怕赫连涛笑话,便又脱掉重穿。
赫连涛见范庠迟迟不来,便心道:“别以为你上了锁,我便开不了!”便强运仙气,将锁打开。
他奔入房内,更觉香气四溢,一见里屋热气滚滚,便径直寻了去,却见范庠只披了底衫,战兢兢地站着。
“你?”赫连涛一惊,两人都有些难堪。
“你急什么!”范庠羞恼难当,只胡乱整衣。
“这屋里这么香?”赫连涛嗅了嗅,奇道。
“别过来!”范庠见赫连涛走近了,不觉急道。
“哟,你个男子,怕什么?”说时,故意一扑,唬那范庠。
范庠一急,便将面前的浴水泼了赫连涛一脸。
“哇!”赫连涛一挡,衣袖却已尽湿,“你小子动真格啦!”赫连涛气得把脸一抹,却觉袖上满是香气。“这水有香气?”
“是啊,天姥草的味道。”范庠挥手让赫连涛退远些,便要穿外衣。
“呀!你竟拿秘制汤泡澡?”赫连涛惊道,“真是暴殄天物哪!我……今后还怎敢再喝那秘制汤?一闻那汤不就想起你的洗澡水么?”
“什么秘制汤、洗澡水的?你休得出去乱讲!”范庠脸红道。
“咳,真是!”赫连涛气得连连摇头。
范庠却也气闷,眼见赫连涛出了门,便嘀咕道:“这叫什么事儿?好好的洗浴就这么被搅了!”正想着,却听赫连涛在外叫道:“这地上怎会有血迹?莫羽非呢?”
范庠在里屋听着,只浑身一颤,心里踌躇:“我该出去看看么?”然一想明日便是“迎伞仪式”,若今日见了血污,怕是晦气,那浴汤岂不白洗了?于是便躲着未出门。
赫连涛却忙取了仙舍牌追出去了。
赫连涛赶到楼下,忙问鹤卫:“敢问鹤仙,方才可曾见得个瘦削虚弱的弟子?若见得,又可知他去了何处?”
那鹤卫一听这弟子尊他“鹤仙”,不觉暗乐,因睁了眼道:“你问他作甚?”
“那看来鹤仙是知他去哪了?还烦请告知!”赫连涛急道。
“天也晚了,你回罢!”那鹤卫受命行事,管好新弟子,夜黑不离舍,故不愿惹麻烦。
“不,鹤仙,他可是病得不轻!我得去看看!”赫连涛便有些急了。
“他已被送往仙医苑了,自有大夫照料。”鹤卫道。
赫连涛心想莫羽非既得照顾,便转身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