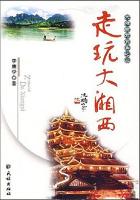倒霉的、生病的外国人
作为一个比较喜欢到处乱跑的人,我跑过的地方还是不少的,此前也并没有在旅途中碰到过生病的情况。但是在德里这次,我算是长见识了。一场奇怪的病抓住了我。
从前看关于印度的书时,一本讨论英属印度的作品曾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它这样描写外国人在印度的状况:“……他们要受一些热带传染病的威胁,包括痢疾、各种寄生虫(如肠道寄生虫)病、莫名其妙的高烧和’间歇性高热‘(生活在蚊子孽生地区而得的疟疾)等等,因疾病而死亡的人真是太多了……很多人有肝病或慢性胃病。”
威廉·希基在他的记录中回忆亡妻夏洛特时则写道:“致命疾病的种子已经潜伏在她身上了。”这名不幸的女子只在印度生存了很短的时间。从英国到加尔各答刚六个月,她就在那个圣诞节死去了。
虽然这是英属印度时期的大致状况,但是大环境应该说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印度的卫生条件比起从前有所改善,但是当地气候对外国人不能说很友好,需要某种适应过程。我成了患病的倒霉外国人之一。
头一天晚上刚从斋浦尔坐夜车到德里,一点事没有。这天上午我起床就觉得有些头晕,不过表现还不明显。出来找了个三轮,首先去火车站寄存了绝大部分行李,只在身边留了一小点东西,这样在德里观光时可以轻装上阵。
在我的日程上,德里有整整两天。但就这座(从文化角度上而言)伟大的城市来说,两天其实非常仓促,只能蜻蜓点水地简略看几处地方。因为对住的店并不满意,从车站订票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是再找住处。
这次找到的是一家金叶宾馆,标价本身不高,而且就在梦巴扎邻街,位置非常方便。这时我觉得身上更加难受,只是象征性地和前台砍了砍价,在他办理入住登记手续的时候我就站不住,赶忙跑到一边的椅子上坐下了。
该宾馆和头天住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整体环境优越不少,环形的楼梯间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天井,看起来很凉爽透气。不过此时我无精打采,已没有兴致去对它作更多的了解。被门童领到房间时,直接躺下了。
我这次的病不是一般的倒霉。不仅是那本书上说的拉肚子和莫名其妙的高烧,还多出一样:频繁的呕吐。又因为我平时很注意绝对不喝生水,基本不吃生食,觉得这病来得毫无道理,所以也感到郁闷和不平。我认为这堪称三种身体的不适和两种精神的不适。
一起旅行的同伴们对我多有照顾,但是疾病不会因此变得缓和。我自己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昏昏沉沉躺着,旁人缺乏与医生沟通这种症状的能力,大概是帮不上忙的,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睡在床上,希望身体可以硬扛过去。
这一天从接近中午一直躺到黄昏,中间就是交替地昏睡与清醒,和持续不断的发烧--时高时低,头疼自然不可避免。
这种发烧不同于感冒时的发烧。感冒造成的发烧我不算陌生,似乎是很清晰的感觉,它只影响人的某个方面,比如让你体温上升、呼吸灼热,也感到不自在,却不会让你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甚至还能干点活。在德里这个莫名其妙的高烧让人浑身发软,好像它是在以你的生命为燃料一样,越烧越软,你能感到自己在慢慢地变成某种灰烬,头脑和身体中有价值有活力的东西都被它不动声色地给消耗掉了。
从躺在床上到起床,中间的过程比较糊涂。似乎在睡醒的那些片刻,意识都很不清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是能确认自己虚弱地活着。在我写的《印度狂奔》小说版里,女主人公小鱼此时感到悲惨和凄凉,想哭,当然这是我假设一名单身旅行的女子的心理,然后施加给她的。我自己无非把这个当一段不好受的体验,只希望这体验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大致是这种心境。
到我能够起床的时候,已经是当天的黄昏。其实这场昏睡固然是疾病引发的,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这一方面应该是身体的自我修复,另一方面也补充了睡眠。之前几天一直在跑路,晚上不是坐夜车,就是在住宿的地方用电脑整理图片和作记录,休息得并不充分。这次昏睡倒是能够缓解不少疲劳感,具体效果当然必须等病好才能显示出来。
那时离我躺到床上差不多过了八个小时,身上的不适感有所缓解。这场病好像也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样,到了下班的时候了,我得到了暂时的解放。一伙人就一起出去逛街。只要下楼,推开宾馆大门就是了。
第二次邂逅
前台告诉了我本地最有名的一些书店的名字,我都记在了本子上,打算隔天精神好的时候再认真去找找,这会儿就不指望了。
这是停留在德里的第一天,时间被我的生病给浪费掉了。我们只能在梦巴扎的街头简单地闲逛,看那些吃的、穿的、用的,种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这里也卖很多尼泊尔货,比如著名的廓尔喀军刀、尼泊尔波达佛塔图案的纪念品,照样满大街都是。
在一家南印度风味餐厅里,我们吃了点饭。无论多么努力地告诉伙计,他都不能理解如何用大米做出对病人来说最适合的粥来。他只会做油腻花哨的炒饭。我对他解释了每一道工序,然后看见他还是继续做出了白米饭--接着就又习惯性地要准备往里拌各种调料配料。最后我只能吃到成功地抢救出来的一小盘白米饭。没有任何菜是想吃的,甚至也不想喝奶茶,只能要开水。
这点米饭我只吃了两口,慢慢嚼出了它的甜味,但是胃立刻开始不舒服。这个器官拒绝接受食物,就用它的方式来让我感到恶心。我本来想强迫自己吃点东西补充体力,这打算就落空了。在别人吃饭的时候,我就看看周围的人。
邻桌一个中长头发的欧洲帅哥在那里拿着个口袋版的小本写写画画,用的是半截铅笔。从侧面看起来这个人的面部轮廓很清晰,线条感清晰,偶尔瞥见正面,大概是地中海一带的长相。他写得废寝忘食,但是我忽然瞥见他指甲里的黑泥、结成绺的头发和满身的油汗时,胃里一阵翻滚,差点当场吐出来。平时绝对不会有这么怪异的反应,再脏的东西也能若无其事地看过去,这个时候大概特别经不起刺激,心里虽是无所谓,胃里却承受不起了。大概这个奇怪的病让我的胃变得神经质和矫情了。
后来接着逛街,有个黑壮矮胖的中年男人,络腮胡子,卖一种缀满亮晶晶的金属片的印度舞裙。质量比较普通,价格非常便宜,当然这种东西只是要个简单的装饰效果,穿它的人也多半就是在锻炼身体--比如跳各种健美操--这时候用起来听个动静。他为了促销,就把舞裙往身上一裹,扭了两下,还很有点印度舞的味道。
我自己在家住的房间绝无装饰,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基本不买花花绿绿的纪念品,平时看看也就罢了。这天因为不自在,只是在同伴买东西的时候充任翻译,自己就没心思多瞧了。那时候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忽然发现小高的面孔在人流中出现。
他在逛街的时候,手里永远握着一卷地图。我毫不怀疑,拿着德里地图,他可以准确地找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除非标注和实际有所出入。我这样对道路和方位不敏感的人就只能多问多打听。
小高正要过去,我忙叫住他。他扭头看见我,很高兴。这是我们在印度的第二次碰面。但是刘师傅居然没在他身边,这让我感到奇怪。
小高解释说,刘师傅待在房间里没出来。此时太阳还不算小,前两天在途中遇到刘师傅时,他看起来状况不好,多半出来晒着更难受。
两支小分队再次会合,我们一起去了小高和刘师傅的宾馆。这地方几乎就在我们住的金叶宾馆隔壁,中间只隔着几处楼房。只是房子建设得有点奇怪,门脸狭窄,有一道窄小陡峭的楼梯,让人走在上面担心摔倒,而房价并不便宜。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刘师傅脸色苍白,看起来很虚弱,说话中间不停地咳嗽。
那之后就剩下我和刘师傅在房间待着,别的人接着去逛街,反正有小高在,买什么东西都有应答和解说的人了。
刘师傅抱怨说,小高这个人属骆驼的,太皮实,一般的人都跟他耗不起。他俩一起从东印度、南印度兜着圈子旅游,小高一直在不停地走路,永不疲倦,有时候为了去看更多的景点,甚至不肯停下来浪费时间吃饭,胡乱买点水果,啃几口就算一顿。
“我多大年纪了,哪能和他比?”刘师傅说。他诉苦道:东边和南边太阳更大,比这北印度厉害多了,两个人长期顶着太阳走,有时候他实在受不了,就坚持要去商场、饭店之类的地方歇脚,蹭点冷气。可是印度这地方,要么热死,要么空调把人冻死,这冷热一激,他就招架不住了,从加尔各答开始生病,一路捱到北边来,这两天更厉害了。
这天他俩刚从阿格拉坐车来德里,找好住处,小高放下东西立刻又去逛街。刘师傅说:他精力太充沛了,山西人身体真结实,我们这些南方人不能比。刘师傅和我都是南方人,我认为他这话比较准确。别说他这把年纪和小高比,我和小高比起来都娇气了很多。
后来逛街的人们都回来了,接着聊天。小高说,他们到泰姬陵之后,拿了我给的薄大爷名片到处找,也没找到那地方究竟在哪儿,最后找了个别的什么店住下了,离泰姬陵也不远。他们在那里也待了一天两夜的样子,对当地印象很不错,果然是比我们晚一天来了德里。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模模糊糊地看着电视,感到那几种毛病又变得厉害了。似乎疾病开始上晚班,接下来会有新的一轮折磨。但是白天和刘师傅他们的见面让我精神好了一些,同时,我感到轻微的慰藉:我不是一个人在生病,而且我这才一天……相比之下,睡在不远处的刘师傅比我倒霉多了,他是我们这群来到印度的旅客当中,最倒霉的外国人。
错过红堡
第二天两支小分队的人还是各自活动,毕竟来到德里的时间有先后,大家的安排大不一样。而我们实际上只有这一天可以在德里走动了,头天上午,订的是这天下午六点去阿姆利则的火车。
当天早上,我感觉比前一天好了很多。可能由于夜里也睡得比较沉,白天也睡了足够多的觉,清晨就醒来了。走到街头时,天光还没有全亮,街道上基本看不见几个人在走动,直到走了一大段路,晨光熹微的时候,才看见活物--还是两头牛。
在下一段路上,终于发现了一家店是开着门的。大家就在这地方吃了早饭。我已经不幻想中国式白粥,只能喝一点麦片粥。就因为我自己忘记叮嘱,里面加的牛奶让我感到反胃,当然,这不是麦片的问题,是胃的问题。此时其实还有轻微的低烧和头疼,但相较于头一天的难受,已经算是减轻了大半。
这是本次到印度期间,我能在德里待的最后一天。因为我们不会走回头路,离开德里,就要一直向西去了。我很想分配好这一天的时间,把德里仔细看看。
我们先坐车去红堡。自从沙杰汗把莫卧儿王朝首都从阿格拉搬迁到德里之后,花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德里红堡就成了万众瞩目的杰出建筑作品。它被公认为是德里最壮丽的建筑,但凡写到印度或德里的书,都免不了要谈论它的庄严与奢华。这座古堡坐落于朱木纳河边,围墙长2500米,堡内的明珠清真寺和枢密殿令去过的人过目难忘。
一本书曾经这样描述德里红堡--
堡内溪水潺潺,处处是花园、清真寺,后宫林立;还有皇帝接受臣民致敬的金塔;传说中叫枢密殿的权势中心所在之处,也可说是正式觐见大厅。墙壁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砌成,银子铺就的天花板闪闪发光,奔流的溪水将地面隔开。用成千上万的珍珠、绿宝石和蓝宝石镶嵌而成的孔雀宝座也曾摆放在大厅内;环绕在大厅柱子上面的是用金子写的铭文:“若有人间天堂,那便必是这里,必是这里。”
司机在马路边停下来,说街对面就是红堡。正好路旁有一座耆那教神庙,需要光脚才能进去。我对耆那教完全不了解,除了知道它的创始人称大雄、教众分天衣派和白衣派、非常鄙视女性外,别的就不清楚了。另外恍惚记得南印度某处竖立着通身赤裸的石雕大雄巨像,香火比较旺盛,那些地方偶尔还会有人按照教义来绝食而死以求解脱轮回之苦。
在这德里的耆那教神庙里,并不能看出多少我能够理解的内容,只转了转就出来了,于是过街去红堡。但是这一天适逢周一,到了红堡边上才发现大批的军警荷枪实弹守在那里,不让游客进去。里面是无数戴着白帽的穆斯林在集会。我们沿着红色围墙走了一段路,都是同样的景象:里面是穆斯林,外面是警察。
后来看到当天的《印度时报》,果然有消息说,周一德里红堡并不对游客开放。这次也就只能过而不入了。
莫卧儿寝宫
在德里红堡周边逡巡了一阵,这时候无论找到这个古堡的德里门还是拉合尔门都没有意义,反正是进不去。接下来想去的地方是胡马雍陵,这个以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二代皇帝为主要墓主的陵墓群是德里的名胜之一。
路边有些老人闲坐,我找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问了一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最好的方式是坐一趟公交车,405路,站牌就在不远处。问路过程中,这些德里老人比较健谈,得知我是中国人,来自北京,立刻大赞北京奥运会。
印度人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对北京奥运会充满好感,很可能在至少四年之内,这届奥运会都会是让他们骄傲谈论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射击选手在北京奥运会10米气步枪比赛中,以700.5环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个结果让全印媒体疯狂,不仅报纸长篇大论地赞扬,电视台都打破常规,更改了节目表,临时围绕这话题进行大规模报道。民间的举国欢庆自不必说,官方则有女总统帕蒂尔亲发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