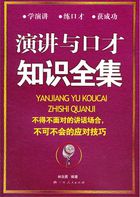“对不起,是妈不好,妈不该对你们发脾气,现在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孩子。”凌青温言道。
“好!”既然凌青已经知道了,那么上官卫国也会很快知道,那他们也无需瞒的那么辛苦了。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赶往医院,牧尘看这架势,嘴角猛地抽抽。
“上官爷爷,凌奶奶,上官叔叔,赵阿姨你们都来了。”牧尘笑迎上去,把他们带到于若云的病房。
于若云此刻像一个安静的睡美人,睡颜甜美的躺在那里,蓝白相间的被子盖在她瘦小的身上,如藻的黑发铺在枕头上,脸上白皙无暇,嘴唇泛白却不干裂,她的手上还扎着针,手背上还有几个小小的针头印,在她白皙的手上显得异常的刺目。
“这……这就是我的小孙女儿?”凌青小心翼翼的伸出手又缩回,眼眶里含着激动的泪光,哽咽道。
“妈,这就是您的小孙女!梓苒的双胞胎妹妹。”上官耀过去拍拍母亲的后背,给她顺气,不至于过于激动。
“像,真像,跟梓苒小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牧尘:“……”小美女长大后跟梓苒小时候一模一样?凌奶奶,您这也太……逗了。
牧尘给站在不远处的上官祈宇挑一挑自己的眉毛,露出一个颠倒众生的笑容。
上官卫国和凌青感慨良多,终于在牧尘的提醒下一步三回头的离开病房,一群人又浩浩荡荡的赶往牧尘的办公室。
牧尘是院长,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也够大,不然他觉得自己的办公室都要被震塌了。
在众人三堂会审般的眼神注视下问于若云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醒,大致什么时候能够醒的时候,牧尘暂时忘记跟上官耀和上官祈宇说过的话,现在还真像第一次说的一样。
“若云具体什么时候醒过来我也不知道,这一次的情况比上一次严重,大脑损伤比较严重,而且我们虽然把她救了回来,但是她没有求生的意识,只会一直躺在那儿。”
“你……你的意思是?若云没有求生的意识,她,她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一直躺在那儿?”
凌青激动的椅子坐不住,直接站起来。
在凌青威严的目光逼迫下,牧尘艰难的点头。
凌青两眼一黑,直接晕倒了,办公室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凌青被送进抢救室,最后她只是情绪太激动,需要休息而已。
闹了这么一出乌龙,几个晚辈都把神经绷紧,生怕再出什么错。
凌青一醒过来就又气场强大的去找牧尘,寻找让于若云醒过来的方法。
“凌奶奶,若云这是因为受了伤,而且这伤是在心里,只有知道她最在意的是什么,最放不下的是什么,每天跟她说说话,她才有可能不那么抵抗外界,才可能醒过来,其实对于外界的事,若云潜意识里是知道了,但她本能的抗拒外界的所有事,所以才会不愿意醒过来,能不能让她醒过来,不仅在于她,也在于我们。”
“那我这就去跟她说话,让她早点醒过来。”凌青想一出是一出,风风火火的跑出去,边跑边打电话:“老头子,你赶紧来医院,跟小孙女儿说说话。”
“耀儿,你来医院,跟你小女儿说话。”
……
等牧尘处理好手头的工作,去病房查看,病房里围着一群人,不得不说,凌青的号召力真大,几个电话,所有人都来了。
“呃……各位,你们每天陪若云说会儿话,可以每天一个人说,不用这么多的,刺激她对外界的感官就好。”牧尘说的极其轻缓,又不失礼貌,把一个晚辈对长辈的恭敬表达的淋漓尽致。
司徒兄弟也每天如期而至,不管赵雅晴对他们如何的不待见,他们还是每天都来,不过兄弟俩几乎没有碰过面,这时间差恰到好处。
“阿姨,我来看看una。”
司徒清手里抱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花,色彩鲜艳热烈,正如他对于若云的心。
赵雅晴已经无力吐槽了,每天都在说,他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有记在心上。赵雅晴眼不见心不烦,去楼下买点东西。
虽然她这样做会给司徒清和于若云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但是现在于若云还在昏迷,他们也没有机会一起说话。
“una,我来看你了。”司徒清找了一个大花瓶,把玫瑰花插好,玫瑰的香气浓郁,飘散在整个病房里,恍如恋爱中那浪漫甜蜜的气息。
司徒清坐在病房的椅子上,执起于若云没有扎针的一只手,一遍又一遍的摩挲。
“una,今天我们来讲最后一个故事好不好,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明知她没有醒,不能说话,他还是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与她交流。
“那是六年前我带你去美国的前夕。”司徒清想起那个时候的她,眼睛里又不可避免的流露了心疼。
“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和他是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抓着我的手让我带你离开,你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吗?”司徒清停住了,看于若云紧闭的双眼,手轻轻的伸出去,把她脸上的秀发拂开。
于若云:“……”
“那时候我真的被你吓坏了,我在想这个女孩胆子这么大,竟然敢让一个陌生人带她离开,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不怕我是骗子吗?”司徒清唇角勾起一个明显的弧度,笑容也变得宠溺:“不过还好啊,你遇到了我这个大好人啊,才让我有了与你这六年的快乐时光。”最后一句话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飘飘忽忽,最后化为一声重重地叹息。
站在病房外的司徒勋把司徒清的话一字不漏的都听完了,一双染上岁月沉淀深邃莫测的眸子此时此刻流露出一种叫“哀伤”的东西,拳头一点点收紧,合得更紧,手背上的肌肉紧绷,路过的人都觉得这个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气息。
他每天都来这里两次,没有人发现,第一次是听司徒清和于若云说话,第二次则是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