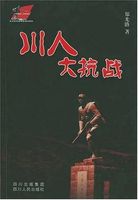她最难过的时候,她最绝望的时候,居然首先是将他推开,逃开,再也不见他。为什么会这样?他钻天打洞疯了似的找她,她却这样对他?陈释到底对她说什么了?陈释对他说,他们之间困难重重,说他和她不能天长地久,他根本不当一回事,可她离开得这样决绝,哪怕知道自己生病快要死掉了。她这样,到底把他当成了什么?
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二十多年来,生命贫瘠而卑微,可她也过来了,坚强地,隐忍地,不屈服地。她答应跟他在一起,她给过他快乐,给过他温暖,然而却从不奢望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不仅如此,她自己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居然首先是离开他。
她这样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想,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不想拖累他?还是,临死之前只想自己一个人面对?她这样,到底是对自己绝望,还是从未、从未把他放进心里?
她这样到底是伟大,还是自私?
她知道自己生了那样严重的病还能这样理智冷静、超然地离开他,到底是对自己狠心,还是太过绝情,绝情到从没想过他?因为从没有付出真情,因此她能走得这样义无反顾。
她到底有没有心?
他终于从老专家那儿知道了一切的缘由,但他能说什么?
这个女人!
他颓然地坐在床上,手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她的枕头,哀怜地,心碎地。他细细地用指头描摹着枕头的轮廓,想起她躺在身边的样子,想起她想要他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想起她那天在厨房里说,放肉之前先放点盐,那些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转眼就只剩了这冰冷的枕头?然而,到这个时候,他对她仍旧是恨不起来。
手机在床头响,他怔忡着,终于想起要去接,一起身带动身后的枕头掉在地毯上,他弯腰拾起,突然呼吸一窒,心跳好像停止了。
他枕头下面,躺着一只贵妃镯,温润的紫罗兰的颜色。他记得很清楚,这只玉镯上次被沈子橘看到,后来他便收到了保险柜里,只是今天他没有找到。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想了想,明白过来,一瞬间气血上涌,心内大恸,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挤压着他的心脏,生疼生疼,疼得人喘不过气来,疼得他没有力气去拿那只镯子。
手机在客厅里急促地响着,他好像没听见。
终于敢伸出手去拿,那只镯子早已经是透心凉,他攥紧了,那股凉意仿佛要透过手心凉到他骨子里去。
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是陈释,他终于接起来。陈释在那边焦急地问:"文晋,有没有唐瑜的消息?你还知不知道她有什么亲戚?她不是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吗?像她那样,身上也没什么钱,要走也不可能走太远,一定会找人帮忙的,她会不会去找她的舅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