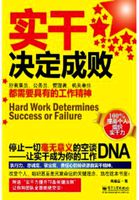不要对这样一个为求生而建立的同盟感到惊讶,这样的联盟在以前不少见,在今后也依然常见。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同盟关系的建立,其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自我获利,没有利益关系的存在,任何一个同盟都无法建立起来,不是吗?即使是在二战时期同盟国的组建不也是由于自我利益?后来危机时期国。安部和中情局的作战联盟不也是如此?只不过每个联盟的共同目标不同罢了,而此时这个联盟的共同目标就是求生。
他们不管我在说什么,他们只管那四个名额,就像美国总统不管阿富汗士兵厌战的心声,只管战争能否取胜一样。而对我来说,我是坚决不可能凑出四个登船名额的,即使可以凑出来我也不会给他们。
“你们听,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了。你们再不做决定,我们都得死!”西装男敲了敲门,丧尸的吼声便更大了,他们撞击木门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四个名额根本就不可能!”我也毫不退让地回击道。
可西装男依旧不管我怎么说,他一口咬定必须四个人都能走,否则他会将怀里的那个女孩扔出去喂丧尸。此时,其他几个端着枪的男人诧异地看了一眼西装男,似乎对他刚刚的话感到些许震惊,我当即断定这些人一定不敢杀害其他人,他们只不过是想求生,仅此而已。
人的一切欲望莫过于求生的欲望,当死亡摆在面前时,任何人都不会再去为事业、金钱、时装、房贷什么的发愁了,任何曾被称之为烦恼或目标的东西一瞬间便烟消云散,在这种情况下,烦恼也好,目标也好,欲望也好,统统都会化作为一个东西,那便是求生。
从这场大战一路走过来,我没什么梦想可言,要说希望,那便是求生的希望,正是因为有着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我才能坚持到现在。然而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却觉得自己仅剩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了,我没有梦想,没有目标,甚至连那一丝求生的希望,也被这平静的生活抹去了。我无所追求,无所欲望,我想这也是我为何屡次推辞掉新政府想要我担任的种种要职的原因吧。
一个人的夜里,总是这样,各种记忆如不断滋长的藤蔓,一点点吞噬着你的所有思绪,在我端起酒瓶的这一刻,那些曾和我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
扎克,诺玛尔,艾泽尔,还有……珍妮。
事情似乎仅在一瞬间就发生了,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哪里不对了,总之一切就是这么突然,没有原因,没有征兆。西装男拉开了门,一把将小女孩推进了尸海中,小女孩尖叫着被那群饥肠辘辘的丧尸给压在了最下面,她的父母,抓狂一般地扑进了尸群中想要救她,最后却和她一起被尸群淹没。
三个人的身体仅在一瞬间便被数十只丧尸的利爪给开膛破肚了,他们的内脏场子什么的在我们面前被一点点的扯出,然后又被塞进了那群丧尸的嘴巴里。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中,鲜血一时间淌满了路面,在那群丧尸的脚下不断汇集。
珍妮想要扑上去关门,我们知道的,所有人都知道的,她的动作就是要关门的动作,不是要攻击谁,然而那一刻子弹还是击中了珍妮,贯穿头骨,而此时她的手仅仅离门只有几厘米的距离了。
是谁给他的那把手枪?那把枪明明被扎克缴走了,为何此时它却出现在西装男的手里,而且枪口正对着那渐渐向后倒去的珍妮。
我从腿上拔出手枪,对着西装男便是两枪,“等等,别杀我!”是他临死前的最后两句话,子弹射进他的喉咙里时,他依然保持着那副表情,眼神中透露着惊恐与不安。他倒下去了,倒在了尸群中,无声地被丧尸们淹没了。他该不这么死,不该死在枪,他应该死在那群丧尸嘴里,死在自己被肢解时痛苦的惨叫声中。
诺玛尔端起枪,如一头被激怒的雄狮,疯狂地扫射着那剩下的三个男人,直到三十发子弹全部打完,直到那三个男人被打成了血筛,直到他们停止了抽搐,诺玛尔才扔下枪,跑到了珍妮身边。
扎克和艾泽尔抱着母亲余温尚存的尸体痛哭着,而珍妮却一动不动,安静地躺在扎克的怀中,圆圆的眼睛瞪着天花板,似乎在望着天堂的方向。
诺玛尔一下跪倒在了珍妮的尸体边,他就是跪着,端端正正地跪着,像是在祭拜一样,双手搭载膝盖上,不哭不嚎,只有两珠细小的泪水滑过。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振作起来,我们必须逃出去!”我拼尽全力抵挡着破开的缺口,但还是有无数双腐烂的手从门缝中钻进来,不停地在我身上抓来抓去,我甚至可以感受到门外股股寒气透过门缝钻进来,爬上我的全身,而这股寒气则是由丧尸嘶吼的声音带来的。
三个人依然无动于衷,跪在珍妮的尸体前痛哭流泪。我抬头看了看其他人,那个两鬓斑白的老妇人正靠在墙边,双眼紧闭,像是被刚刚的事情吓昏了过去,而老头则急得焦头烂额,一会听听她的呼吸,一会儿恰恰她的人中;另一个小男孩则和三个女人紧紧抱在一起,全身发抖蜷缩在角落里,显然没有从刚刚的噩梦中摆脱出来。
整个房间里除了我,简直再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了!
“诺玛尔!”我大吼一声,想要将他从失去妻子的悲痛中吼出来,因为我实在是快撑不住身后这扇木板了。
诺玛尔缓缓抬起头,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双手紧紧握拳扣在膝盖上,头上的青筋暴起,眼里的泪水也已经干涸,只剩下那压抑已久的愤怒。
“如果珍妮还在,她不会希望看到大家都丧命的!”我冲诺玛尔吼道。
诺玛尔依旧不说话,双眼直直地盯着前方,似乎想将前方的木板望穿,也许他是在回忆,也许他是在思考。我知道我本不应该打断他,他的妻子刚刚被杀害,他有理由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放任自己不管,但是实际情况不允许他这么做,在我身后的木板后有一大群疯狂的丧尸想要破门而入,也许是几十只,也许是几百只,但不管有多少只我都根本不可能撑到他们来一场祷告,那不可能!他现在必须振作起来,他还有两个孩子,所以他必须醒过来!
“诺玛尔,你该清醒了!珍妮已经走了,你还有两个孩子,难道你想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死在这里吗!”
“你闭嘴!”诺玛尔怒吼一声,犹如一头被关在铁笼里渴望被释放的野兽发出沉闷的嘶吼。
“好,”我点点头,看着诺玛尔依然一蹶不振的样子,眼神渐渐黯淡了下来。我知道一切都毁了,希望、生存、未来……一切都不存在了,结束了,今天将不会再有人能活下来了,“既然大家都没有希望了,那就一起死吧,没想到你会这么懦弱,珍妮看错人了。”
我向前跨出一步,将手松开,那一瞬间我感觉到门被推开时的风打在了我的背上,就像是死亡的钟声在为我提醒一般,那恐怖的嘶吼声也在那一瞬间如洪水般破门而入。
就在我闭上眼睛等待死亡前的最后一瞬间,我看到诺玛尔从地上一跃而起,攥紧拳头,怒火冲天地向我扑来。
这只野兽终于被释放了,在我下地狱前的最后一秒钟,你还要因为我说你懦弱而痛揍我一顿吗?
来吧,你这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