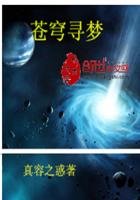第二天上午,情况依旧没有好转,电力还是没能重新供应过来。
在我刚醒来的那段时间,还经常可以听见外面有生存者的哭喊声,密集的枪声,剧烈的爆炸声,直升飞机呼啸声以及战斗机低空飞过的声音,但现在整个卡维拉却变得越来越安静了,似乎这座昔日人口繁密的大都市一瞬间被抛到了寂静的外太空里去了,逐渐向着那无力回天的黑暗边缘坠去。
早上我吃到了扎克母亲做的三明治,鸡蛋和火腿夹在两片面包之间,里面还浇盖了沙拉酱,非常可口。由于没有电,所以面包没有热,不过鸡蛋和火腿都是煎熟了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地下燃气的供应还是没有中断的,这也倒成了我们在不幸环境中的一丝安慰。
“电是没有来,恐怕是不会再来了吧。”扎克坐在我的床边说道,“我觉得有必要考虑自己发电了。”
“你真的打算去发电室?”我问道,然后悄悄拨开了窗帘看了看外面的街道,几只感染者正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动着,“这很危险,万一被他们发现了……”
“这是我们计划好了的,”扎克回答我,“如果今天不来电就去发电室。”
“我知道,但是我们不确定那条路上到底有没有危险。”
“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必须要用上电!你也说了,没有电联系不到救援。”扎克提醒我说道。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今天正午过后。在中午之前,我和我父亲会把各个窗子和前门全部封死,然后去楼顶观察一下情况,以便敲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我没有再继续阻止扎克了,因为他说的没错,我们必须要用上电,不然我们不可能一直躲在这个地方。现在的情况很明了,不发电,就只能待在这个地方等死;但是去找发电室很可能会把感染者吸引过来,然后还是一死。既然两种结局都是死,只不过一个早死一个晚死,何尝不试一下更有生存希望的那种死法呢?
我点点头,同意了扎克的想法。
扎克和他的父亲忙活了一上午,把房子一楼所有的窗户都钉上了木板,木板则是从柜子上卸下来的。扎克已经想好了如果下午发电成功,晚上必须要隔绝所有光源才行,于是他在二楼的各个窗上也钉上了木板,不过没有将窗户全部封死,在木板之间还留下了一点缝隙,以便观察使用,到晚上用布料把木板之间的缝隙塞住就好了。
扎克的全名是巴里奥·扎克,他的父亲老扎克的全名是诺玛尔·扎克(以下用诺玛尔称呼扎克父亲)。诺玛尔·扎克年轻时候也是一名赛斯维亚士兵,不过不是国名警卫队的,而是陆军。似乎扎克家族的身体基因都很棒,因为扎克那身健壮的肌肉在诺玛尔的身上也看得到,虽然诺玛尔已经退役那么多年了,但是肌肉线条依然很明显,看来扎克的身体有一部分是遗传了他的父亲。
诺玛尔的性格和扎克有很大差别,扎克是个热心,耿直,什么心情全部写在脸上的男人,而他的父亲诺玛尔则相反,他不善于表达感情,更多时候他会隐藏起自己的感情,在他的脸上最常见的表情只有严肃和冷酷,即使是一个能让全世界人都捧腹大笑的笑话,对诺玛尔讲他也顶多就是嘴巴微微一扬。
中午吃过了午饭,扎克和诺玛尔就上楼去观察情况去了。我已经把发电室的具体位置告诉了扎克,他们只能从后门出去,因为从前门的话离街道太近,很容易被发现,然后他们需要穿过我家后院的停车场,从铁丝网围成的那面隔离墙旁边的铁门穿过去,这时他们会有一段暴露的时间,因为想要从停车场到另一侧的花园必须要穿越那条连接着大门的又宽又直的道路,而这时如果有感染者往这里看一眼,那么他们就暴露了。穿越那条宽阔的马路后,他们会来到一个花园,穿过花园他们会看到一个铁门,上面写着高压危险,打开铁门进去就是发电室了。
不一会儿,扎克和诺玛尔就从楼顶上下来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看来他们已经敲定好计划了。
扎克走到我的床边,自信地说:“我们仔细看了看,院子里没什么异常,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会成功的。”
“嗯。”我拍了拍扎克的肩膀,“记住保护好自己,安全回来。另外我必须要提醒你们,发电机很久没有使用过了,如果太阳下山前还没处理好,一定不要犯傻,赶快回来。”
“嗯。”扎克用力地点点头,“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和我父亲出了意外,你一定要带着我母亲和弟弟离开这里,拜托了。”
“嗯,放心。”我用力地握住了扎克的手。
扎克的母亲珍妮紧紧地抱住自己的丈夫,一边哭着一边说着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想也知道都是些提醒和祈祷。诺玛尔抱着珍妮安慰了好半天,珍妮才舍得松手。扎克十岁的弟弟艾泽尔瞪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脸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几个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诺玛尔再次嘱咐我照顾好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后,转身蹲下来,摸着艾泽尔的小脑袋瓜说道:“我的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是时候承担起家里的责任了。我和哥哥不在的时候,这个家里你就是唯一的男人,你就是那个顶天立地的支柱,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家庭,照顾好妈妈和古风哥哥,明白吗?”
“明白。”小艾泽尔站得笔直,一脸坚毅地回答道。
交代的差不多了,两人便出发了。
我透过木板之间的间隙,向外面偷偷地观察着,那几个感染者在阳光恶毒的照射下像是脱水了一般,拖着沉重的双腿,像乌龟那般缓缓移动着,还有几个感染者则有气无力地靠坐在汽车或是电线杆旁,我知道他们这是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下午珍妮又来到我的卧室,为我的伤口更换纱布,然后清理了一下我的身子。虽然是扎克的母亲,但她毕竟也是一个女性,在她面前脱得一丝不挂确实有些难堪,不过这也是为了养病,我只能裸着身子不停地告诉自己“珍妮是医生,珍妮是医生”来缓解我的尴尬心情。
傍晚时分,太阳就快要落山了,我却依然不见扎克和诺玛尔的身影,也不见电来,于是揪着的心便更加紧张了。眼看着街道上的感染者越来越多,我真想从床上跳起来去找他们,可我一抬腿就痛得要命,只能乖乖在床上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就在我祈祷之时,楼下传来一阵动静,没过多久,扎克和诺玛尔便走进了我的房间,身上还带着一股浓浓的焦油味道。
小艾泽尔丝毫不介意父亲和哥哥那满身黏糊糊的焦油,一下子扎进了两人的怀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