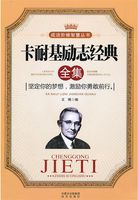天微亮,海风呼,寒冷!
我裹紧了身上的布片,然后哆嗦,很显然那破布根本不能保暖;我是滇边人,还受不了江南的寒冷天气,于是我之后紧了又紧,继续靠着水泥墩子发抖。或许是天不够亮,我的眼睛开始模糊,眼睛的东西变成了虚影晃来晃去的;眼睛黑了,我倒了!
睁眼时我已经在老叫花的馊霉被窝里,虽说残破不全,却也比我那破布好得很多;而他则忙于我的肋下,像样的查看我的伤势。
老叫花据说是学过医的,在乡下和次九流的土郎中学过看舌头,望、闻、问、切已学其三,他说前三都好学,这‘切’学问大了去,一时半会学不会。他把手搓了又搓,似乎是想搓出些温度来,不过屡试失败,最好只好鼓捣他那盒发了潮的火柴。
“我热乎了,不疼了!”我说道。
他继续捣弄着他的火柴,那是个锲而不舍的人,火柴埂子在磨擦后起了点火花,然后瞬间消失,没等老叫花滑第二次那鳞片头就掉落了,很不给脸。
“我没事啦,你的药是神药,不疼了!”我继续说。
“那是冻的,就跟冻肉一样,这天气就跟拿了块冰放了你伤口上差不多了”他继续跟他的火柴叫劲。
“大东有打火机”我提醒他。
火着了,那是‘吱’的一声,然后顺利的点燃干纸片;老叫花顺利的把手烤热了,从我腰间拿下那草药糊糊,那东西已经快干了,没什么用了!他擦了一把汗,顺利的把另外一包新的草药糊糊敷在我伤口上:“得动手术了,嗯”
老叫花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想办法,不过他能在这么冷的天擦汗,说明像我这伤对他来说是绝症。
我轻碰了一下:“你药哪来的?”
“云梨桥边到处都是这种草,在我老家是用来治肚子疼的,想你这种内外伤的不明白得不得行!”他说的倒是实话,“我去给你找吃的!”
“省省吧,我不想吃东西”我叫住他;
“那出去转悠转悠,运气好的话也许会找到一点消炎药,嗯嗯,磺胺或许能拖拖!”他走了,桥墩底下只有我一人。
我想一个人,因为我见不得别人的好,尽管是在极端的处境下;可我又想和别人一起,因为如果没有别人,比如说老叫花、大东和山强这类的,要是没有这些人我早死了;可我的想法是矛盾的,我又想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救活,死了多好??????
于是在胡思乱想之后,我又昏睡过去。梦里,我回到滇边,看见那漫无边际的山峦,看见了初晨的露水滴落和山溪水冲刷的石头。
我醒了,觉得很饿,于是颤悠的站起,忍痛的挪动脚步,跌倒后,我索性不起,慢慢的爬动;我像软体动物,又像极了爬行动物,我永远都记得的林子里的毛毛虫爬动时就像是我现在的样子;我看见了人群,他们有些异样,眼神就像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不少人驻足了,不过他们可能只好好奇我是怎么做到这么高难度的动作的,可能怀疑这人手脚健在,专业的演者,在剥求他们存在的同情;可那关我什么事?我继续向前爬去。
他们是路人甲乙丙,幸运的是他们没和我在同一世界,他们有可怜和同情,可那又有什么用,我不能拿他们的可怜和同情作为食物来解决我的饥饿,不能作为药来敷好我的伤。
我向前爬行的路被一双脚挡住了,那是一双帆布鞋,往上看是牛仔裤,我想抬起头来,只是那股香味告诉这是一女生,于是我便没了勇气,于是我只好趴在那不动;牛仔裤弯了,那是女生蹲下的动作,接着在我面前的就是一袋还冒着热气的豆浆和油条。
我终于还是抬头看了,那是一张异常清秀的脸,没有浓妆艳抹;她是一个小女孩,我说的小,因为她会让你感觉她永远都不会长大或变老;脸上的表情让你什么也看不出来,感觉像是同情我,还感觉像是可怜我,又感觉像是厌恶世间的不公。
女孩一直保持递着的动作,见我看她有些发呆给我一个笑!
好吧,我眼花了,那只是一个天使,厌倦天条而来到人间的仙女,普惠世间的美丽菩萨;我想去接,可我发现我现在连手都抬不起来;她把豆浆的吸管伸到我的嘴边,我吸了一口,那只是下意识的,我的思想还没有从她的脸上移开。
她把豆浆和油条放到我脸下,然后不耐烦地走到路边上了一辆好车,从驾驶位上下来的是一位西装革履,那是一位绅士,像是一位从来没有过穷的青瓜裂枣,他走着,方向目标是我,他把一叠钞票掏出,砸在我脸上,然后华丽的转身:“拿了钱,滚吧!”他吐了一口唾沫才上的车。
我没去拣,好吧,我傻了,或许是被这么多的钱吓傻了,又或者是被女孩的善良和美丽吓傻了,我惯性的又吸了口豆浆;有人开始捡钱了,我毫不关心,他把我头揪起,我看见了他。
捡钱的是山强,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他分分钟把钱塞进他的口袋:“死不了吧?你咋那么虎呢你?”
我不理他,不理他的东北话,我继续吸着豆浆。
我们回到了天桥底下,山强他的包打开,从里边取出来的是磺胺:“死老东西去哪了?”
“他去找吃的去了”我漫不经心的回道。
“啥玩意?有你尊菩萨在这还用去找?看回来我撑不死他!”他捣碎了磺胺,不像老叫花那般怜惜,直接扯掉我身上的破布,我大叫一声。
“吼啥玩意?扛你回来时怎么不叫?”他恶狠狠的。
我叫并不是因为疼,破布虽说不管用,一下子扯掉还是让我觉得更冷。山强把老叫花的草药扯掉,直接就把磺胺沫沫涂到伤口上:“你不是肋骨断了吗?还会有伤口?”他又把另外的两片磺胺药塞我嘴里:“吃下去,这没水你就生咽吧”,我咽了下去,然后对他宣布:“吃了你的药,我感觉好多了!”
山强:“嗯哪!”
他把钱掏出来,用东西包好丢我旁边:“去宿金身吧,好大一坨的!”
那地上的是钱,我知道的,那是食物和衣物;不过往前看,那便是一个男人的高傲、鄙视和瞧不起。
“我不要这东西!”我说。
“嗯?这不是东西,你看见了,钱在他身上掏得特别利索砸得特别准,他开的那车你这辈子摸都别想摸一下,那衣服就算把你卖了都不值一钮扣;他身边那女的,你还真会非分的想!”
我回应:“那是善良,不拜金”
山强像是气不过,像是我拿了他的至宝:“爱钱和善良不是两回事,拜金的就不善良了?善良的人就不去想钱的?”他脱下他那西装,砸在我身上:“我努力得来的,谁都别说不爱钱,你不拿这钱是觉得侮辱委屈,觉得他拿钱的时候砸给你一大堆侮辱;你是乞丐,臭要饭,你要气节还活着干嘛?”
我无言以对,那是一种教训,又像是一种叫魂,山强像极了招魂的,慢慢的把我的魂魄拉拢归位;然后我努力的让它消失,我真想魂飞魄散。
见我不说,山强继续扩大他的战果:“在这天桥底下的,你最成不得气候,掉水里都荡不起波纹的!”
我:“嗯哪,老头子和那一班乞丐呢?难道我还不如他们?”
“不如,都是群臭乞丐,除了死老头和你之外还有哪个思想神经正常的?老头六十了,活够了活一天就是一天,你才二十四岁,再活三十六年才能和他一样,可你现在就开始在这和人比烂了,而且还都不是你的对手了?
我努力不去看他,努力的给自己找借口,不过慢慢的我才发现那些能拿得出台面的借口都好像要求我杀身成仁,丝毫没有反驳山强的机会,于是我等他停了口:“你不是我爹!”
山强呵了一声:“谢天谢地你不是我儿子,我要有你这样的儿子我都回去抛祖坟好断子绝孙”
我不成气候,我不想对着山强,于是我只好翻身,老乞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边,他背着手,眼睛里透露出来的除了思考还是思考,一眨眼又多了一份黯然。
山强也看见他了:“老头你回来啦,这有磺胺、有钱,都给你了,留他在这等死吧,你不用管他,没事拿上钱回黄土高原找你儿子去!”他对着老头说的,但是说给我听的,他拿起他的衣服:“我走了,我忙,没工夫跟你们玩了”
他走了,他招了魂;留下伤残的我和目光黯然的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