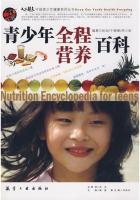我于长江之南的某个小镇,抖抖索索的抢了一个小朋友的糖吃,又因过度用力把那小子弄倒在地;结果不是我吃了糖而是被四来的人群淹没,人群离开后,我身上的脚印口痰多得数不过来了。
天很冷,小巷里几乎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类,和我穿了同样衣服的老者,鄙视的看了我一眼,抖索的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发了霉的馒头;我接过,吃的很香,然后迷迷糊糊的离开了,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我叫李牧和,单从破烂外边来看就知道我是个乞丐,或者说我是被骗的,从遥远的滇边来到遥远的江南小城。或者说我算不上活人了,活人的眼中不应该单有食物和衣物;好听点来说,我的理想就是穿上衣服吃饱肚子。
以前或许不信,但是人饿极了就会为食物付出任何代价,比如说我会趁那卖包子的不注意而顺他几个,或者说去和别人争抢那掉了地上的一块硬币;又或者说去餐厅的餐桌边上一站恶心走正在吃食的顾客然后自己狼吞虎咽之后被那有我两个头大的汉子丢出大门,摔断肋骨一根。
久而久之,在这片区域的人见了我之后都会远远的避开,有心情不爽的会找我出气,狠揍我一顿后丢下一毛钱很爽的离开,我捡起那一毛,那笑纹从心底一直泛滥到嘴角,或许我的生命就值这一毛吧?
冬天到后,天气开始放冷了,在桥墩下总会聚集那么一大群人,七八个乞丐围绕一堆用旧纸片烧起的火堆旁烤火,
可那有什么用呢,在这城市里几乎找不到半根柴火,纸片分分钟就烧灭了,还不如裹件大衣靠着桥堆好好的睡一觉。
乞丐们推嚷着,像是一团会动臭黑草,围绕着一点火光!
我在乱草之外,我算是异类吧,不喜欢把那从来不属于我的一点亮光占为己有;老头今年六十岁了,拿着儿子的照片在乱草堆中流泪,五十九岁的乞丐打击他:“你下的蛋不要你了,你还拿着蛋的照片伤感情“
老头叫什么真名我们已经记不得了,在这天桥底下的半年以来我从未听他说过他的名字,也许不当是我们,连他自己也记不起了吧?他唯一的特点就是拿着那张发了霉的照片在呼唤他儿子,什么贵儿、小金???等等乱叫,
我问他:“你到底有几个儿子?”
老头:“一个”
我:“那你叫出那么多名字?”
老头一脸无奈:“我记不得是叫贵儿还是小金了”
我:······
老头没有名字,所以我们就实事求是的叫他‘老叫花’,他并不反对,因为他喜欢这个名字。
大东是个胖子,单从他的身材上看我实在不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要着饭,他能算是我们当中最健康也是最贱的一个,他总是厚脸无耻的在和我们几个和他一样的乞丐要东西吃;就连老头捡的一把破刀他都要得去,然后躲在角落里削他那足有半尺长的头发,或者说那已经叫不得头发了,那头发脏得粘卷在一起,说是头发更不如说是长错了地方的杂草。
破刀削完头发之后,他从角落里出来,对着我们做了一个自以为很帅的表情,再看他头发,像是一觉醒来被老鼠啃完一般——七有缺八有残。
我们笑了,被这种场面雷住,山强直接就打击他:“老鼠啃了咋地?你要是每天都能整这笑料我把我的东西给你吃!”
大东好不容易修一次发被他说成笑料,面子上难免有些挂不住,他或许不在意在正常人面前的面子,但是在我们这群乞丐窝里他也是想顾全面子的。
山强是我们当中最干净的一个,或者说他已经不能算作还是一个乞丐,他已经在渐渐的脱离我们这组织;
衣服穿得人模人样,露出胸前的一大块肌肉,应了他那名字,如同山一般强壮。
我从来没有想明白过他那样的人怎么会成了要饭的?
“我要走了,我有户口有工作了,不跟你们玩了!”在笑完大东之后他开始宣布,对于这样的结果不是使我惊讶的,不得不说山强的确不是乞丐,因为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上进心,他想要强,
于是开始接一些‘生意’,比如说帮人在楼下喊某个女人的名字,喊一个小时给几十块钱。
他赚的第一笔钱,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成了有钱人。
老叫花对他的宣布也没多感冒,把他那用塑料纸包的草药糊糊拿出来对了下水沟了的水,然后裹在破布里走向我来。
“小娃,该换药了”他对我说道!
伤的是我,前些天被摔伤的肋骨断了,我只好靠着墙角不敢乱动,稍动一下就疼得要命。
他开始撩起我的衣服,说是衣服倒不如说是一大块旧破布,也许是块破床单,那只是天冷时我用来裹身的。
老叫花的动作很轻,像是以为破布掀下来我就会死一样的小心。
“你老省省吧,早烂了,不差你这一下”我说道!
老头子不理我,好容易掀开了,把手轻轻的把绑在我伤上的那破布解下,很小心的。
“你大爷的!”我骂道!
老叫花一惊呼,那手中叫草药的物件差点掉落:“弄疼你了?对不起啊!”
我用一种很疼的表情,额头上渗出汗丝来:“你知道你手有多冰吗?”
老叫花反应过来,拿着他包着草药糊糊的破布连手到那离熄灭不远的火堆上烤了烤。
他周边的几个叫花则对我这堆东西不太关心,我斜过头去:关我毛事?
老头很跨把他的手和破布烤得热乎,然后再往我断掉的肋骨上黏糊,嘴里还念念有词;包好完毕,老头擦了一把头上的虚汗。
“都烂了,得去医院动手术了!”他很关心的说;
我懒得理他:“医院是什么?”
“医院是手术”
“手术是什么?”
“手术是救命的,救你命的,拖不得了!”
我轻动了一下,其实我想转身来着,只是我发现我根本不能动了,动一下肋下就疼得厉害,只好说:“死老东西您能回你那窝去吗?看你这模样我就烦!”
老叫花对我还算是无动于衷吧,只是他好像心事重重,看我那眼光就像看见眼前摆着一百万,开始闪光。
我赶紧闭上眼睛:“死老东你干嘛?什么眼神?”
老叫花算收眼了,眼睛里模模糊糊的:“我儿子比你大几岁了,他比你大,他要是像你这样我还能安心?”
我算安慰他:“我不是他,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这只是小事,老头子思儿之情泛滥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打击他完后觉得过了,我不是个善于道歉的人,于是只好打发他走。
他那占的地方算是个窝吧,褥子被子样样俱全,那是黑褐色的,人在那数米外都能问见馊味,除了那五十九岁的老乞丐能和他滚一窝之外没人愿意和他同盖一条被子。
山强收拾完他的东西后就走了,去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是我们乞丐群里少了一个抢食吃的而已。